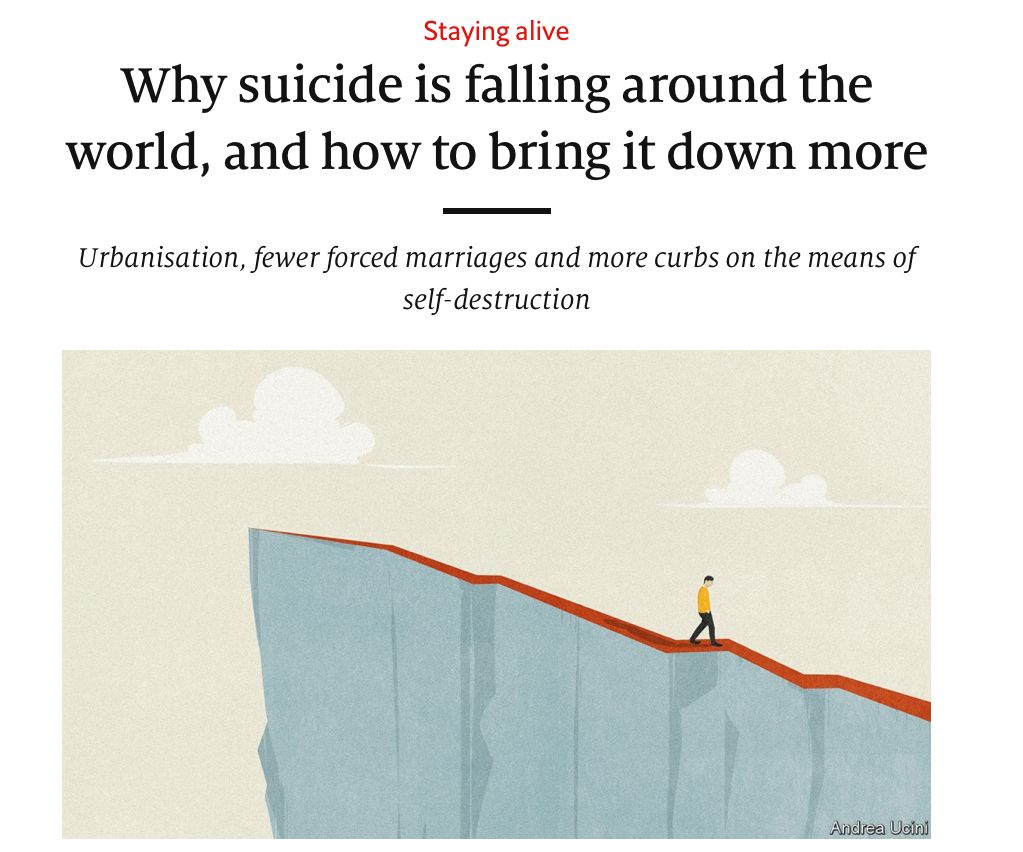来源:《诗刊》2020年6月下半月刊“发现”栏目
作者:赵琳,笔名小小贝,1995 年生于甘肃陇南,现居兰州

火车经过德令哈
有一刻,我想伸手摸一把沿途的风
星空落在沿线村庄,我和邻座大叔
聊到了拉萨,他从未远离青海大地
没有去//www.58yuanyou.com过布达拉宫
他说起家乡海西,你不知道
牛羊出栏时,草地上就飘着白云
你不知道它们眼中装满星星
在去西藏的火车上
那些漂亮的云彩就像他豢养的羊群
放牧在夜空,最亮的太阳如同一块
古老的打火石,正划亮火车进洞的黑暗
他下车时,捏着一张病例单
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今晚的星空真美
值得任何人怀念——真的值得
赶夜路
夜色摸过草地
松林间的雪厚了
静寂无限延伸,再短的路
一个人还未走,已经很长很长
整个山谷是漆黑的
河流是漆黑的,浑身的雪
有时也是漆黑的
路过一座点着蜡烛的小庙
菩萨在飘忽的烛光中
也是漆黑的,但即使
天色漆黑,视野迷茫
我只看了它一眼忽明忽暗的面容
仿佛身边多了一个做伴的人
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
第三次听琴
第三次听到琴声
让我不由想到,夜宿西海镇
星火点燃草原,词语披着
瘦弱的狼皮
在关口遥望着
有人在隔壁毡房,用口琴演奏牧羊曲
仿佛白天奔跑的马匹
一夜之间,吃完汹涌的青草
而第二次涌入生活的光亮
是移居小镇后,隔壁的琴声
像一只鹰
在雪山间飞过
有那么几次,听着惊险处
我担心,鹰坠落
在平静的草原
那些布满色彩的想象
因为风,突然退出夜晚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琴声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安静得,让我不由想起她的年少

克拉玛依来信
雨天,我收到朋友
从克拉玛依小镇寄来的石头
一块猩红色的石头,尖尖的不规则
光滑的表面磨损严重
像沉淀的沙丘
我又和他聊到乌鸦
只会在冬天出现,略带晦气的黑精灵
巢穴建在树顶,日落日出中
它们扑腾着翅膀飞过
矮矮的草原,在高耸地方
一定看到云雪
年前在藏区,他告诉我
太阳之子的乌鸦,是灾难的一面镜子
在命运中
需要带块磨难的石头
洗涤掉噩运的事物
或者日暮之际,赞美更久远的两个人
日 常
两只喜鹊在枝头盘旋
这是冬天最常见的一种鸟
寓意好运和幸福,听人说
乡村的语言中,喜鹊有两种暗示
一种是喜悦的消息
一种是悲伤的噩耗,一年之间
这座小镇打伞的女人走丢
卖肉的屠夫失手把人打成重伤
街角捡垃圾的流浪汉
他能去哪里?
放学滚铁环的孩子穿着花棉袄
在冬天,敲打着火花
他的奔跑带我又一次
回到温暖的童年
我总是这样,在悲喜间
匆匆已过二十四年
去理发店
去理发店,黑发沾着火花
剪刀夹带古老的技艺
我把时间装进镜子
借用光的一生,照亮自己
我还有灵感读完一本书
书只剩最后几页了
——“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
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①
商行已经打烊,街角路灯昏暗
我两手空空,想起了祖父
在麦子熟了的田野
赤足穿过稻草人的模样
——————
注①:出自博尔赫斯《我的一生》。
牧羊曲
我们靠着墙,院子里两棵燃烧的槐木
火焰跳跃,像祖父提着
两盏不说话的马灯在黑夜里
和一群羊对视,从未厌倦
冬雪夜晚,我围在火炉旁
在祖父赶羊的口哨声里
一次次羊群转场,草木复苏
一次次梦中打口哨
一次次火炕上,和依偎
在草料场的羊群一样温柔暖和
多年间,羊群数目不断增减
有时上百只,有时二三十只
但有时只有孤零零的一只
在偌大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山冈
我能听懂它哀嚎的每一声,正在回忆
祖父亲手擦拭过的生活
与他活着时一样清晰

西部物语、自然生活及个人体验的诗性
唐翰存
赵琳的这组诗,在题材上,大致属于比较稳当的“西部范畴”,写西部的自然地理,也写西部的生活,但诗歌描述的首先是西部的某种自然性。对自然的厚描,可以说是身在西部的诗人们的一个写作传统。自新诗诞生以来,这一传统一直在延续,即便是在全民抗战的岁月,西部也催生了“边塞新诗”那样的诗歌殊象,融地理性、时代性、文学性为一体,展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改革开放之初,“西部诗”tKeDhDfDp崛起,其中的“新边塞诗派”一脉,更看重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笔者曾在《重谈新边塞诗派》一文中对“朦胧诗”与“新边塞诗”作了一个比较,认为朦胧诗的社会意识强烈,多反思和批判社会历史,新边塞诗则借重自然环境,厚描自然环境里人的悲壮和浪漫。朦胧诗在当时总体上比新边塞诗的影响大,是因为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比对自然问题的关注来得紧迫,从而将朦胧诗推到了一个时代的话语中心,然而,“当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到达一个饱和度以后,他们发现,影响人生存的不光是社会,还有自然。很多情况下,自然的力量可能更大一些”。也因此,自然的严酷以及它长久的神奇,总是让处身西部的诗人们不能释怀,以至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题材的“自然性”贯注在自己的创作中,形成某种潜意识的“西部物语”。
赵琳的这组诗,便是“西部物语”的一个具体体现。从诗歌的题目、内容里,很容易体会到西部的地理标记。通过物象,一种自然的诗歌空间被初步建构起来。通过物语,时空中的事物被感受,或者自我感受,进而被言说。“有一刻,我想伸手摸一把沿途的风”(《火车经过德令哈》)、“夜色摸过草地/松林间的雪厚了”(《赶夜路》)、“第三次听到琴声/ 让我不由想到,夜宿西海镇/ 星火点燃草原,词语披着/ 瘦弱的狼皮/在关口遥望着”(《第三次听琴》),诗句中的感官动词,带动着写作主体对事物的身心体验以及转喻想象,实的、虚的、在场的、不在场的,都顺着某一种构思有机呈现。其中首先要肯定的,是诗人敏锐的自然感受力。唯其对自然物有心、有觉,那种体察感才能出来,借助语言,再实现某种“有意味的形式”。
对自然的体察和感受,到一定程度,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物本身的尊重,也意味着对诗的尊重,因为诗本是从自然中长出来的,自然是造物的源头,也是诗的源头。一个写诗者可以很懵懂,不去思考“自然性”的问题,然而他一旦进入创作机制,并且在文字上有所作为,他必定会用诗“触摸”到“物化自然”之状态,以符号化的方式做到对事物的贴近与尊重。像赵琳这样的青年人,还有其他人,目前或许还是“观念”的懵懂者,但这并不致命,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朴素和感性的诗者,让事物在其诗作中形成直观。事物如此具象,在西部,在路上,在生活中,召唤贴近事物的诗的出现。“我们靠着墙,院子里两棵燃烧的槐木/ 火焰跳跃,像祖父提着/ 两盏不说话的马灯在黑夜里/ 和一群羊对视,从未厌倦”(《牧羊曲》),类似这些诗句,在描写中先是维持某种相似性,然后又试图冒一点修辞上的奇险,加入作者心理体验的成分。唯此,事物就不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事物,不再仅仅是表象化的事物,而是具有了某种内在性的事物。赵琳诗歌的这种内在性特征,也是很明显的。这是一个诗者通往诗歌幽途的必备因素。观念可以懵懂,体验不能缺场。许多青年诗作者在创作中惯于物象的拼贴,以及语言的平滑,唯其体验不深,内在性的东西就在词句间无法逗留,写诗也就流于表面化。不少写西部的诗歌,也流于物象描写的表面化,并且为世人所诟病,究其原因,还是体验的问题。
说赵琳是一位比较踏实的写作者,也就包括他体验事物的那种踏实。“放学滚铁环的孩子穿着花棉袄/ 在冬天,敲打着火花/他的奔跑带我又一次/ 回到温暖的童年/我总是这样,在悲喜间/匆匆已过二十四年”(《日常》),如果说,诗的前半部分是“表象”,滚铁环是“表象”,“我”悲喜间的介入则是体验。“年前在藏区,他告诉我/ 太阳之子的乌鸦,是灾难的一面镜子/ 在命运中/ 需要带块磨难的石头/ 洗涤掉噩运的事物/ 或者日暮之际,赞美更久远的两个人”(《克拉玛依来信》),石头和乌鸦是“表象”,磨难是体验,“赞美更久远的两个人”更是体验。体验使诗具有了诗性,那种味道,那种审美上的蕴藉,那种字里行间成为诗的东西。平常我们读有些诗歌,写实方面好像比较充分,比较到位,可诗性的东西就是出不来,少了那么一两句,火候就显得不足。
体验的过程,也伴随着思考,是语言带入某种思的东西。在赵琳的诗中,语言对思的这种带入感也比较好。“去理发店,黑发沾着火花/ 剪刀夹带古老的技艺/ 我把时间装进镜子/ 借用光的一生,照亮自己//我还有灵感读完一本书/ 书只剩最后几页了/——‘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去理发店》),诗中有实有虚,有此在和彼在,通过构思,让事物成为自身的同时,也大于自身,从而扩展了诗性阐释的向度。
不过,诗性的扩展有一个尺度,即不能违背事物的情理,不能过分突兀,否则就会破坏思考的合体度,进而破坏诗性。在赵琳的诗中,这种状况也是偶尔存在的。“这是我第三次听到琴声/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安静得,让我不由想起她的年少”(《第三次听琴》),结尾一句就有些突兀,因为前句中没有任何“她”的信息,也没有一句关于“她”的铺垫。其中虽然有好句子,但表述确有些刻意了,读后觉得并不自然。

耐心而深情地注视生活
北 乔
读这组《克拉玛依来信》,如同面对一条安静的河流,正如诗中所叙述的“星空落在沿线村庄”“平静的草原”“沉淀的沙丘”那般静谧,河水缓慢流动,波纹在水面,也在天空,可以看到清水之下的一些水草和鱼儿。日常化之中,有隐喻有秘密,有些需要我们的想象力,有些需要我们用心寻找和品味。读这样的诗,感觉是湿润的,可以抵抗生活的喧嚣和灵魂的燥热。外表质朴,其里有着寓言化的内蕴和浓淡相间的隐喻质感。那些悸动和参悟,具有柔韧之力和持久之力。诗人对生活和母语进行的有意识的开拓,正在有理想地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写作经验。
诗歌读起来有意味,在于赵琳注重情节的巧妙置放。换而言之,他注重营建诗歌有意味的结构。因为情节的运用,有些诗既浓缩性地讲了一个故事,又勇敢地“留白原由网”。《火车经过德令哈》这首诗尤其如此。同在火车上,我与邻座大叔不断地交谈美好,相信气氛也是同样的美好。我自然是在去往美好的路上,旅游地点的美好,未来人生的美好。而在诗的结尾,我们才知道,邻座大叔已是患病之人。www.58yuanyou.com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今晚的星空真美”。对我而言,路过德令哈也好,经历今晚也好,前方还将有无数的美好。而对于邻座大叔而言,这样的美好,恐怕是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再回想前面“他说起家乡海西,你不知道/ 牛羊出栏时,草地上就飘着白云/ 你不知道它们眼中装满星星”,我们的感受更加复杂,诗的力量陡然加大。这样的结构,是经由赵琳有意识地设置而成,但又十分的契合生活。因为现实中,我们常常遭遇这样的“恍然大悟”或“如梦初醒”。而因这一情节,车厢里两人的交谈,便成为可供我们无限想象的画面,“邻座大叔”这样一位人物变得立体起来,诗歌的丰富性得到加强。
这组诗可谓是以细节化见长,这样的细节化是精确性的临摹呈现。作为诗人的赵琳,不是介入生活,而是就在生活中写诗。对于日常生活的敬畏,取决于生活与写作的双重态度。在这一点上,赵琳是朴素诚实且智慧的。组诗中多半都有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断或切面,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丝毫的疏离感和陌生化。我们在阅读时,可以轻易地还原并抵达现场。“我和邻座大叔/ 聊到了拉萨,他从未远离青海大地/没有去过布达拉宫”《火车经过德令哈》),这是一个极普通的生活场景。“一年之间/这座小镇打伞的女人走丢……放学滚铁环的孩子穿着花棉袄/ 在冬天,敲打着火花/ 他的奔跑带我又一次/ 回到温暖的童年”(《日常》)有人物,有故事,有岁月的情境。从容而平常的叙述中,有浓郁真实的生活气息,又散发某些不可言说的幽深。赵琳将独特的想象力和中国古典的意境之味只作用于对词语的挑拣和书写的潜动力,其他的都在不动声色里。
赵琳对于以乡村为底色的生活的叙述,基本品质是写实的,但属于经过记忆淘洗和心灵悟化后的写实。既深扎现实,又具有辽阔视野,“贴着地面飞翔”,运用了有节制且艺术化的小写意。“我们靠着墙,院子里两棵燃烧的槐木/ 火焰跳跃,像祖父提着/两盏不说话的马灯在黑夜里/ 和一群羊对视,从未厌倦”(《牧羊曲》)如此平常的画面,经由赵琳叙述,便有了难以固化的意向生发。如此可以说,赵琳的这组诗强化自己作为目击人,为我们如实提供和再现生活,好读,易读,但又有些许的隐伏。这样的隐伏看似是少量的甚至是不经意的,但内在却是巨大的。就像安静的河那样,更丰富的世界在平静的水下。
“去理发店,黑发沾着火花/ 剪刀夹带古老的技艺/ 我把时间装进镜子/ 借用光的一生,照亮自己”(《去理发店》)依然是极日常化的生活,无需过多的费心劳神,便能读出熠熠闪光的纹理,这是思绪的脉络,也是通向幽深的小径。理发店,是公共空间之下的个人生活,也是我们生活之中普通性日常性的基础节点之一。在这里,镜子以及对于镜子的描述,显然带有现代意识的语境和审美诉求。而“剪刀夹带古老的技艺”,则表明了诗人对于本土经验的回望和体验。从语言层面上,赵琳正在进行某种蜕变的尝试。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关乎语言的节奏、表情,但内核是本土的。如此,我们发现了他诗中处处显现的现代性语感之下的汉语意蕴和张力。
赵琳对于本土资源的吸收和致敬,是全方位的,我们甚至从他的诗中看到这样的创作理想,至少在这组诗中是这样的。“乡村”“祖父”“父亲”,成为他写作中常见的对象。“我能听懂它哀嚎的每一声,正在回忆祖父亲手擦拭过的生活/ 与他活着时一样清晰”(《牧羊曲》)在这里,直接表明了他对于祖父的怀念,原由网在奔跑中会经常回望故乡与亲人,这是相当智性的。而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有实力表现的90 后诗人、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敬重和之于本土经验的挖掘,远远超乎我的想象。90 后的他们在转身和后撤中直面现实,冲向未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赵琳当然也在此列,在这组诗中,表现得相当充分。从乡村到城市,从祖父、父亲到诗人自身,其实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擦拭过的生活/ 与他活着时一样清晰”,在这里,赵琳表达的不再是我们常见的“照亮”,而是“擦亮”。我们并不怀疑赵琳之于现实的对抗性写作的诗歌精神。然而这样的对抗是建立在精微的熨帖的生活写作之上,不断地擦拭自我的灵魂,寻找前行动力源。
“贴着地面的飞翔”,有大地和生活的坚实,也有天空和想象的飘逸。赵琳的这组诗清静、清醒,平易近人之中有许多我们所期望且值得细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