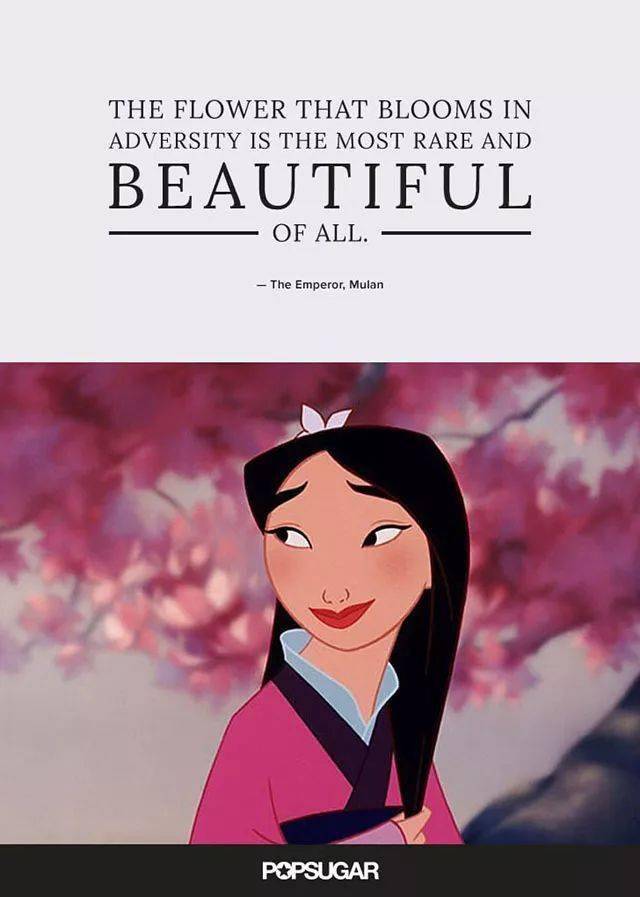↑点击收听↑ 文/刘易斯托马斯播/文月

英语没有任何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没有,但或许这只是因为我没有远见。假如我受命去掌管它,作什么会,比如全国语言改进研究会的主席,我不会去动英语一个手指头。
它适合于我能想到的所有需要:灵活,清晰,隐喻之微妙,需要模糊的地方还会模糊(这种需要比通常承认的还要频繁),最要紧的,还有可变。我喜欢语言可变。
我是一个社会向善论者,坚信过去所有的变化是越变越好;我毫不怀疑,比起伊丽莎白朝的语言或乔叟时的说话,今天的英语已经是可观的进步,比起古英语更是遥遥领先。到现在,这种语言已经达到其最终的完美之境,我会满足于让它永远这样。
但我知道这样想是错误的。英语还在改变着,在我们的眼前和耳朵前时时在变,不受任何个人,委员会,研究会和政府的控制。从前的讲话者无疑也曾这样满足于他们各自时代的说话版本。
乔叟那一代,此前所有的世代,决不会意识到有任何必要去改变或改进自己的语言。蒙田完全满意于16世纪的法语,并且显然喜欢用它做事。很久很久以前,最远最远的讲英语的原由网祖先一定曾经用古印欧语混得很好,而决然想不到,他们的语言有一天会消失殆尽。
然而,用“消失”这个词来描述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不对的。数千个印欧语词根直到今天还活着且活跃着,像共生物一样规规矩矩塞进了其他词语,塞进希腊语,拉丁语,还有所有日耳曼语言,包括英语的词汇里。
我们今天彼此用英语交谈的许多话语,都可以用带点印欧腔调的希腊语加以解释。而从今三四百年之后,很有可能,今天的英语基本会谁也不懂,除了几个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
印欧语词根的古老意义有时候扭曲甚至歪曲,真相难辨了,但它们还在那儿,从内里发着回响,作着提醒。古老词根gheue,意思不原由网过是呼叫,来到日耳曼语变成了gudam,后来成了英语的God(上帝)。
Meug这个词根本来指的是某种湿乎乎滑溜溜的东西,几千年后,变成了正规英语里的meek(温顺,柔和)和土话里的mooch(闲荡,徘徊),www.58yuanyou.com还有schmuck(可鄙的人,笨蛋)。
Bha在印欧语里意思是说话,到了希腊语成了phanai,意思一样,很后来很后来成了我们语言里的一个很基本的词,意思是不能说话:infancy(婴幼期)。Ster这个词根意思是stiffen(使僵硬),后来成了日耳曼语的sterban和古英语的steorfan,意思是死,再后来成了我们这儿的starve(饿死)。
语言的变化会永远继续,可原由网是,没有人说得准,是谁改变了它。有一个可能是儿童们要对此负责。
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德里克比克顿在他的《语言的根源》一书中对此作了探讨。1880年顷,夏威夷发生了一次语言大灾变:数千名移民工人被引进夏威夷群岛为新兴的蔗糖业工作。
这些人讲的是中国话,日本话,朝鲜话,葡萄牙话,还有各种花样的西班牙方言。他们无法彼此交流,无法跟夏威夷土著交流,也无法跟占统治地位、讲英语的种植园主交流。
他们所做的,是所有这种混杂语言群体古来就做的:讲一种洋泾浜英语,是一种退化变质的“事务英语”。洋泾浜实在并不是一种语言,倒更像是一套用来指称实物的信号,缺乏表达思想和想法所需的语法规范。
后来,仅仅一代人之后,整个混杂的人群开始讲一种全新的语言:夏威夷克里奥尔语。新语言包含从所有原有语言借来的现成语词,但用来串起语词的规则却跟那些语言前驱很少或绝无相似之处。
尽管通常被视为一种“原始”语言,夏威夷克里奥尔语却由相当精致的语法规则构建起来。比克顿教授的伟大发现是,这种崭新的话语,只有孩子们才造得出来。别的解释也许有,但就是没有这样充足的时间。
1880年工人涌入不久,语言还是夏威夷洋泾浜,而二三十年之后,通用的语言就成了克里奥尔语。最初的移民,那些说洋泾浜的父母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语言并教给孩子。当克里奥尔语出现时,他们连听都听不懂。掌管那地方的讲英语的成年人既不讲,也听不懂克里奥尔语。
根据比克顿的研究,那只能就是儿童的杰作,在他们群集在一起,亟亟于彼此讲话,一起游戏时。
比克顿引用这一在他看来无可争议的历史现象作证据,形成了一套理论,那就是,语言是生物性的,与生俱来的,由遗传决定的人类本性,由大脑里编码语法和句法的一个或多个中心所驱动。
他为这一语言天赋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作“生物程序”(bioprogram)。这一思想支持并发展了乔姆斯基大约三十年前所倡的设想,他认为,语法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而只有人拥有这样的大脑。
然而,新的研究之最为引人入胜的方面,还是它那个证据:儿童,很可能是极小的儿童,有本事构建一整个语言,靠的是大家一起做,或者更有可能,大家一起做着玩。
这件事能让你对儿童刮目相看:他们竟能做出令人生畏的事情来。我们向来知道,儿童时期能够快速而容易地学会新语言和自己的母语。在大多数人,这种能力在青春期就会消失,从此往后,学一门新语言就是艰辛的劳作。
当然,儿童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但是,他们竟有可能创造语言,改变语言,或许,从初民交流演变成20世纪话语,原来也是他们的功劳,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更高等次的尊敬了。
假如没有儿童和他们的特殊天赋,我们或许至今还在说着印欧语或者赫梯语,可是我们都在这儿,说着数千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它们的大多数,倒退回几百年,地球上没有人听得懂。
或许,我们应该严肃地注意儿童在语言起源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了。当然,我们这个物种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语言,至今还无人知道,而对于它如何发生的,也只有纯粹的猜测。
有一个流行的猜测是,在人类脑壳和里面的大脑进化的特定阶段,说话在少数几个突变型个人那儿成为可能。从此以后,这几个特别聪明的人及其基因胜出了他们所有不会说话的堂兄,自然选择导致了智人(homosapiens)的出现。
这一想法要求整个地球周围有许多彼此孤立的不同共同体出现相同的突变,不然,你就得假设,有几个幸运的讲话者能够在地球上相当灵活地旅行,到处留下他们新型的基因。
从对于儿童和语言的新观点看来,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类语言并不是随着特殊突变而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整个物种进化的某一点上,所有人的大脑全都出现一种潜在的性质。
大脑语言中心的表达所需的环境仅仅是儿童,足够数目的儿童集聚在一起,有些情况,使他们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一起玩耍。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家庭定居下来,住在紧密的区域,就像很久以前从事采集渔猎的部落那样,或者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一样,在这样一个足够稳定原由网的社会中,儿童数目就可能达到创造语言所需的临界值。
这想法够做成一个有趣的剧情说明。部落里的成年人和智慧的老者,围坐在火堆旁讲着关于日常琐事的洋泾浜,指着一样样东西嘟囔出孤立的字眼。没有句法,没有字串,没有真正的想法,没有隐喻。
近处的某个地方,达到临界数目的吵吵嚷嚷的幼小儿童团,急促不清地彼此吆喝着,因发现了什么而兴奋地提高了嗓门儿,讲着,讲着,从此往后就讲个不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