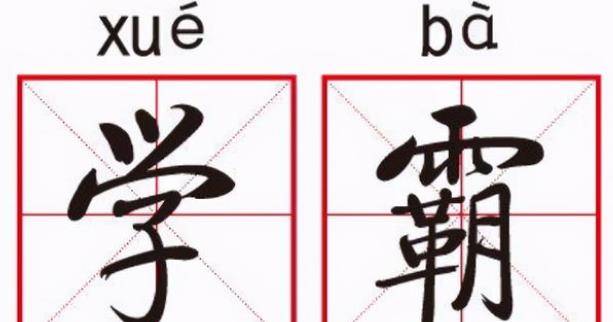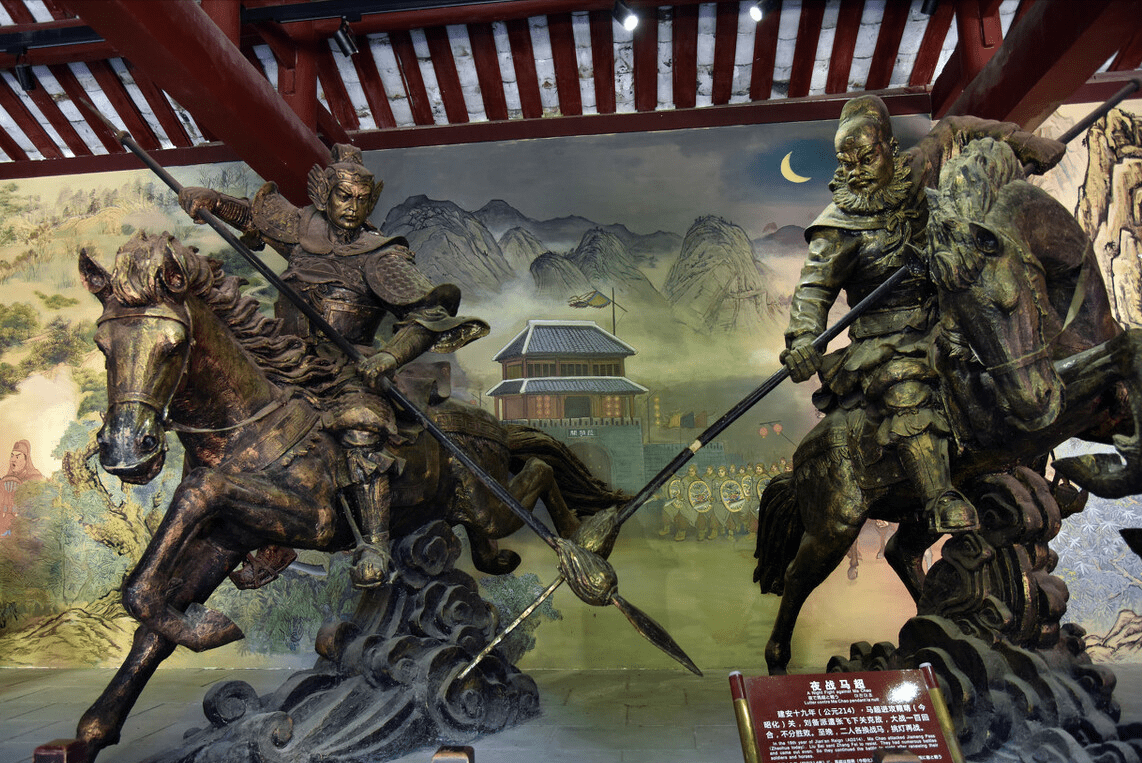王建民,1962年生于青海乐都。曾供职法院、出版社,后辞职。1984年获《飞天》大学生诗苑奖。有诗歌、小说、评论等散见于报刊。诗歌入选《青年诗选》、《当代陕西先锋诗选》等。《青海新文学史论》认为,“王建民最先提出了‘河湟文学’的概念,1989年2月,他的长文《河湟文学论》从理论上比较完整地讨论了‘河湟文学’的内洽性与实践的可能性,显示了一种青海文坛上少有的理论的自觉意识。”
本书为作者首部诗歌选集。以汉字独特的时空架构能力,追索人类文化母题中诗质的人本的部分,进行真正的现代考量。内容分为三辑,其中,“达拉积石山”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人中有良好口碑;“水缠绕在玛尼石上”为作者21世纪发布的长期潜心思索的力作,是基于宗教母题的人性还原;“雪人没有时间”是对平凡日子的多向度体验。作者以其对汉字的独特理解,在汉语新诗修辞上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干净和清醒,从而抵达形而上的自由。
序一:说几句王建民
杨争光
和王建民相识,应该是在1984年我从天津调回西安之后。
那时的建民还在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就读,他们有一个诗社,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所以两个人是因诗相识,因诗结缘,至今已三十多年。回过头想一下那时候的建民和他们的诗社,恍若隔世,又恍然如昨。
清爽自然的建民,清爽自然的诗,会让人想起青海的“花儿”与水草。
建民毕业之后回到了青海,在出版社工作,我们的联系没有中断,还会有通讯。那时候的通讯都是手写的。还有文章,也是手写的。建民写过一篇《捅破的窗户》,是说我的诗的,即使不能算是长篇大论,篇幅却也不小,在我看来已经很长了,且是认真的文字,有认真的考量。这一篇手稿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
我翻了一下八十EJKcpR年代的笔记本,其中有几页文字,是从我给王建民的一封回信中摘抄下来的,大概是要留一个记录,说的也是诗。说到“象”,抽象,象征,等等,也许幼稚,但认真,证明着那时候的我们对于诗的虔诚。
1988年之后,我不再写诗,但并没有离开诗。和诗相遇,一定会有认真的阅读,也会有一些所谓的思考,至今都是。我以为王建民和我一样也中断了诗的写作,但应该也不会与诗绝交。
果然,最近读到他的诗作,都是近十来年的新作。也因此知道了1990年代至今,他并没有完全中断诗的写作。诗一直伴随着他。
他做过出版,也做过生意,我相信,他的出版他的生意,以至于日常生活,都会有诗的或多或少的参与,所以,他至今也没有把自己倒腾到富翁的行列。但似乎也并不懊悔。这不懊悔里,应该也有诗的作用。
建民也写过小说,而且是长篇。有一本《银子家园》,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我认真读过这本小说,有价值的材料,诗意的叙述。我曾经向某大刊甚至某出版社推荐过,没有发表,我并不以为是这一本小说的遗憾,反倒以为,遗憾的应该是刊物和出版社。中国每年有几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有多少在出版之后不久又被化为纸浆?建民应该为他的《银子家园》感到庆幸。我不知道建民还有没有兴趣回望他的这一本小说,有没有兴趣对它作一些必要的修整。我相信,如果他有兴趣也愿意,这本小说会获得友谊的,而且,绝不会和化纸浆的搅拌机遭遇。
当然,也有很多珍贵的经典遭遇了被化为纸浆的命运,但这不是经典的耻辱,耻辱的是让它们变为纸浆的那个时代与国度。赫拉巴尔写过一本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写的就是这个,已经成为当代小说的经典。
关于建民的诗,他曾经的《达拉积石山》是很好的诗,不仅对他自己,对青海的诗也是,甚至对中国当代诗也是。他其后的诗,尤其是那些有骨感有质感的诗,都和他曾经的《达拉积石山》有着渊源关系,血脉相通。
建民的诗还会不会继续?在我看来,这不再重要,重要的倒是诗意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不只是天生的,还有后来的自持。而这,我对建民却是有信心的。
为建民高兴。
他所在的高原,有其相对独立的自然历史,人文历史,宗教历史,有它的“花儿”,有它的水草,有它的石头,还有,它的青稞酒。建民是不是比过去胖了一点?但胖与瘦并不必然意味着心胸的阔与窄,诗意的生命,有足够的空间拥有这一个“大块”,这大块高原的一切。
即使不能完全拥有,也可以是一支“花儿”。
我喜欢青海的“花儿”,词好,曲好,有味儿,耐听。
2017年6月28日于老家乾县
[杨争光] 诗人,一级作家,影视编剧,深圳市文联副主席。长期从事诗歌、小说、影视剧写作。十卷本《杨争光文集》的正式出版,是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
序二:大道至简
刘晓林
建民要出诗集了,这是他写诗30多年所出的第一本诗集。作为老朋友,为他高兴之余,心中也不免生出几分苍凉。建民出道甚早,曾经前程似锦,但由于坚持的诗歌立场与诗界流行风尚的抵牾,以及执拗和绝不通融的态度,与聚光灯下的诗歌现场渐行渐远,从此被人淡忘了,也被忽视了。时下,许多习诗不久的诗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诗歌履历中填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书名,而建民迟至今日才有机缘将那些飘零在漫长时光中诗篇聚拢,让那些失散已久的“孩子”团聚,这不禁让人唏嘘。
面对冷遇与漠视,建民倒是非常坦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远离喧嚣置身边缘,在灯火阑珊处保持形单影只的身姿,恰是他自己的选择。上世纪80年代后期,风华正茂的建民在青海文学界非常活跃,他的《达拉积石山》系列陆续推出,引起了广泛关注,他首倡“河湟文学”流派,显示了青海文坛少有的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当时,认识他的文友,无人怀疑他将在文学领域成就一番作为。但他厌恶呼朋引类、立门户拉山头的做派,本能地拒绝在自己的额头上粘贴某某主义的标签,坚持独立立场,撰文质疑已然蔚为大观的“西部文学”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将可能纵深到主流诗歌场域的通道切断了。
90年代初,建民去职远游,无疑也是脱身嘈杂诗界的自我放逐。此后,他杳然无踪,隐身茫茫尘世。
直到前几年,他突然现身朋友面前的时候,曾经清爽的面孔已带上了岁月沧桑的缕缕擦痕。他说,这么多年,没有与任何诗歌的团体、刊物、媒介有过联系,连早年间刊载了自己诗作的样刊都遗失了,但并未放弃写作,虽然随写随丢,却始终保持着对于诗歌的一份纯粹的热爱。容颜在变,情怀则始终如一。
我时常回忆起最初阅读建民诗作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不同城市读大学的我和建民,经朋友介绍开始了书信交流。他来信的话题都是围绕诗歌展开,他参与的西安大学生的诗歌活动,对诗坛走向的认识,当然还有自己的写作。他偶尔随信寄一两首手书的习作,字迹工整端庄,一丝不苟,不难见出他对于诗歌的那份虔诚。他的诗作大多以乡土为背景,词语朴拙近乎口语,像游吟歌者唇齿间流淌的绵绵谣曲,感情内敛,不事田园景物的描摹,也没有致敬乡土的浮泛抒情,而是以简洁的白描裸露着乡村的骨骼,直接切入乡土人物沉静甚至有些麻木的生存状态,有一种类乎黑白照片的显影效果,这在当时是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之外的“异样”的乡土诗,所以印象深刻。
此后几年间,以《达拉积石山》为总题的系列诗作陆续问世,我意识到他随信寄来的习作实际上就是这个系列的雏形,显然他为建构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西部乡村已做了长时间酝酿和准备。“达拉积石山”系列的写作与建民出身农家的乡村经验密切相关,他稔熟河湟谷地农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情态,对生长于斯人们与荒寒环境的厮磨中产生的悲苦与欣悦、无奈与希冀感同身受,因此,他勾描乡土风物和乡村生活状态可谓神情毕肖。比如《村口》一诗,黄昏时分,叼着烟卷的农人聚在村口,讲述村庄的前生今世,议论家长里短,最后,“我们扔掉烟头/望望天色/然后回家了”,这是已经苍老但世代依然在延续的一个乡村日常生活场景,不断重复显现了生活的迟滞与凝固,却自有一番安宁惬意,是辛苦劳作人们的精神小憩。建民像是在一个固定的机位安放了一台摄影机,全程记录了村民的一次傍晚闲谈,但他似乎又是村人之一参与了谈话,“他者”观察与自我表述的双重视镜,使得这种书写非常接近于格尔兹“地方性”理论所强调的通过深度描绘来展示特定地域人群“自我世界”方法。
正是对场景、细节的精微拿捏,一个地方性特征鲜明的乡村形象得以呈现,以此而论,将《达拉积石山》纳入西部诗歌的范畴也不无依据。诗人、批评家沈奇在《当代陕西先锋诗选》序中就说过,建民的诗是“至今仍不失‘前卫’或曰‘先锋’的、真正西部味的西部诗,现代意识加古歌情味,那一种返常合道、务虚于实的诡异劲道,如新开封的老酒,啥时喝来啥时为之一醉。”然而,建民并不认为行政区划和地理方位的指认对诗歌精神的建构能够产生实际的效应,西部文学在强调自身自足性和完整性之时,在广袤的地域空间寻求共性,有着遮蔽个人化经验的危险,同时强调地域特性有可能人为地制造与更广阔世界精神文化创造的不可通约性,对这些潜在的陷阱,建民是颇为警觉的。
相比削足适履去顺应某个宣言或原则,他属意于借助个体的经验从人类学的视野考索人的生存本质,《达拉积石山》虽一望而知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西部山村的景观,表达的却是精神向度的体验与认知,如生老病死的生命节律:“祖先总是丢下我们/睡在最肥沃的山坡/总会有女原由网人生下我们/让我们走远路”(《高原》);无始无终永远循环的时间:“今天累了坐石头上/用不着思量明天/但可以等待后天/后天嘛就是再过两天”(《石头》);人与大地须臾不能分离的关系:“天亮就把脚放进土里/脚下松软而温暖/蚯蚓在动/我们这样站着/没有脚印/没有谁喊我们远离”(《土地》)。
建民在诗歌中剥离着地域、时代、文化诸多因素的限定,力求穿过现象抵达本质,呈示人之本性与生命的真实状态,当然作为土地的儿子乡村的后裔,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吟唱中,也隐含着对无助挣扎在历史与现实涡旋中艰辛的农人命运的悲悯。
结束了自我放逐,重返人们视野的建民,依旧关注着乡土,然而此时的乡土已经在高速运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变得面目全非。有感于乡土的陷落,他把一份痛惜注入到组诗《达拉积石山辞典》之中。相比以往,这组诗的现实感增强了,忧患感更加浓重,那种尖锐的痛感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
《绝对的骨头》一诗,表现把祖先当作力量和慰藉的人们,总是折腾祖先,使亡灵不得安宁,“山里的坟墓/骨头的戏楼//我们缺了啥/就去翻腾祖坟”,“阴宅”古老习俗中,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部分已被弃如敝屣,而阴宅能给后代助力的部分被无限放大,人类如今的急功近利,连坟墓里的祖先都不放过。建民不是为诗意乡土的消失唱挽歌,不是将乡土视作精神的图腾而为其的坼裂而慨叹,而是关注着快速变换容颜的乡村里那些不断地被外在的力量拨弄的人的命运,袒露长期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中作为基石的农人事实上被漠视始终处于“缺席”状态的境遇。建民在《达拉积石山辞典》的写作中依然恪守诗歌的本分,作生活的呈现者而非判断者,但借用后现代批判、解构、颠覆等特性来曲折表述农人面对传统坍塌时精神挫折感,其中包含的驳难、质疑的反思品质,既可见出建民惯常穿透表象直达事物内核的锐利眼光,也可以看到一个“地之子”的情感本色,同时显示了他解读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建民说,《达拉积石山辞典》是《达拉积石山》系列的收官之作,这是否意味着不再具有完整形态的乡村已经无法唤醒他的诗情了。
《达拉积石山》系列是诗集《太阳的青盐》中写作时间跨度最长、最为人熟知的一部分,而另外两辑则显示了建民思想和生活触角的多维性。《水缠绕在玛尼石上》建构了藏地草原的背景,但依然不是对草原风物与生活的直观性描述,而是从滚滚红尘中遁逃面对宁静草原内心感悟的表达,是灵魂与草原所寓示的信仰、人性、自然深度融合之后返璞归真的纯净歌声,这些诗篇在古歌谣曲般的语式中充盈着天真稚趣,“我不用鞭子/鞭子能驱赶那些山吗/能赶我上天堂吗”(《牧》),“高山那边的人呐/没有水没有月亮/他们的月亮在木桶的水中/他们的木桶散碎了”(《土坎那儿》),“客人说帐篷后的小河/缠绕在玛尼石上”(《水缠绕在玛尼石上》),诗句拙扑自然,憨态十足,仿佛稚子脱口而出,但对于诗人而言,如果没有灵魂的长久砥砺获得的净化,没有信仰力量支撑,没有回归人性本真的一派天然,是难以道出的,简明的语言背后却意蕴深厚,不经细心咀嚼是难以品尝到其中滋味的。
《雪人没有时间》则收集了建民多年在尘世间行走,对日常生活感触的即刻性记录,有目击道存的意味,对生活的瞬间发现和领悟,使得其中的哲思、巧思俯拾即是。“一只耳朵竖起/偷听另一只耳朵的声音/声音左右为难/最后只剩下和声”(《耳朵》),“六十年代的玻璃/稀缺但是不怕破碎/完整的是一片完整的心/破碎后是好几片完整的心”(《六十年代的玻璃》),“面对叙事的嘴 对说话满怀敬畏/鹦鹉学舌时 对声音满怀敬畏/圣者的经咒令人心安么/念诵时 对发声的器官满怀敬畏”(《交易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性的诗歌,色彩斑斓芜杂,不仅因为书写的对象是现代都市生活的衍生物,充满悖谬、荒诞、失衡的意味,而且在于处理都市经验时选择的知性的冷静的审视眼光,以及冷峻的讥诮的EJKcpR反讽的语调。从“达拉积石山”走出的建民,尝试用诗歌去把握更为广泛的生活场景,触及更广阔的世界,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有更大抱负的立体的诗人。
建民在诗歌艺术上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是极简主义的语言风格。他试图摒弃形容词和修饰语,拒绝修辞,修剪了一切枝蔓,用干净爽利的短句组合构成相对整饬的诗歌节奏,这种语言方式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实现了剥离表象抵达事物内核的写作目的。这通常可以解释为,语默之间的空白包含着许多言外之意,刺激读者的创造性思维进行填补,挖掘其微言大义。而建民对此则另有解说,最近他有关于汉字的语言学文章在网络刊布,着意讨论了汉字在沿革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象形字时代的原初意义,附着了太多所谓文化的含义,变得不堪重负,面目模糊,而象形字的创造本依据中国人的时空观,是中国人独特思维方式体现,因为汉字在发展过程苔藓丛生,充满了多义性,含混性、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人丧失了以自己的时空观认识把握世界的独特思维。这些观点,在学理上大可争论,但却是建民的确信。80年代,有诗派主张现代汉诗应回到语言,便是要清理汉语所承载太多非诗因素,而建民则要回到汉字,他相信一个个汉字就是一个个事实,只有删繁就简,回归汉字的本义,就能还原一个个事实,凸显生命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诗歌的使命。大道至简,这或许就是建民诗歌语言风格生成的缘由。
行文至此,大约可以概括建民的诗歌立场了,那就是以一以贯之的悲悯、人本叙事的现代精神,切实把控汉字在时空上的自足特质,让文字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中脱身,回到生命的本真中,抽取生命本质的无奈、悲哀与欢乐,创建完全属于汉字思维的当代诗歌。诗集《太阳的青盐》就是建民实践其诗学观的结晶。
但愿我这篇思虑不周的文字不要辱没了建民的诗歌,但其中所表达的情谊则积淀长久。记得30多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某个春天,我伏在教室临窗的一张课桌,读完建民的来信以及诗歌,抬头看看窗外,阳光明丽,一株丁香满树繁花,小鸟从扶疏枝叶中飞出,那一刻,感觉真好!
[刘晓林]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专著《青海新文学史论》、《寻找意义》等。曾出任“茅盾文学奖”、“骏马奖”评委。
相信
总想让自己相信
这块地是我们的
远来的亲戚
微笑着点头
这是他们酒后
站在田埂上的姿势
城里来的大人物
把嫩粮食填进口里
说庄稼长势喜人
我们相信这话
让出远门的人
取捧土包进手帕
庙顶的喜鹊唱着歌儿
就是要让我们相信
这块地
是我们的
我们积攒下粪土
撒在地里
然后握着犁把
转圈儿
剩下的日子
到这儿很久了
给你唠叨同一样事情
你看不见
风吹来又离开
剩下我躺在坟茔里
你吵不醒
我曾经是你父亲
这种关联经常发生
更远的人
也奔涌到这儿
他们闭上的眼睛
让你知道
泪水是从眼窝里消失的
现在有许多时间
有用没用的时间
土堆摆好看了
就会给你剩下不少日子
为我干同一样事情
你还有很多力气
从我怀里
蹦到锄头上
你自己的锄头
冷落在墙角
我那个小孙子吵醒你
天也就亮了
腊月
山里是石头和雪
山里是我们
热月天的活儿都没白干
眼下去买好酒好烟
嫁出去的女儿过年要来
人老祖辈的亲戚过年要来
看看这腊月
心里稳当得要死
真想喊醒老先人们
叫他们从此安稳
孩子指着腊月奔跑
指着腊月叫唤
山里的石头和雪
又有看头了
雨水很多
出远门挣钱的人
寄来消息
天下没有大旱
工棚里日子好过
雨水也算温暖
出远门的人
捎来些消息
要去些消息
有消息心里好受些
你说雨水很多
我说雨水很多
有雨水心里总好受些
祖坟
草叶顺着熟悉的颜色扎进手心
这时手中没有工具也没有别的东西
它们都在上面在上面
后人们正在劳作
响动跟我们没缘分了
谁家的狗叫了几声
谁家的孩子从来就不认识我们
飞起的纸灰是白还是黑
草根穿越不再盛米面的腹部
抓住另一把黄土另一把
是不是年轻时候捏过的呵
活着的日子里
恨不能把天下的好物件塞进口袋
现在我们的一切挤紧了我们
挤在头发和指甲缝里
很清楚我们死了
拿自己的土堆来安排自己
健壮的身体在上面干够了一切
我们的一切这就拥紧我们
我们的一切不是水不是阳光也不是
这根骨子里伸出的草叶
干沟旱山
你以为路尽头一无所有
感到此行非常劳累
你把脸泡在一捧水里
你可以回去
你还可以说远呵
赶车的人不会瞪你
他的山在他脚下
他的脚在他腿上
有些树枝到达天空前就消失了
风出生以后就停在这儿
对面几个男人
别劝他们远离
他们要照看女人孩子
要照看坟地里的先人
那些女人太阳的女儿
眼看着她们从田埂上来了
你被抛进许多眼睛
你不知埋葬你的该是哪具棺材
你该讨一碗水
因为你听见了她们干燥的笑声
想知道早死的那几张脸
路的尽头随手可以拣到
没有力量能让他们消失
庙里有本唯一的日历
日子和木门敞开着
你会走进
你会逃出
告诉大家那是个可靠的地方
没有谁能让你替他难过
那里的小孩总有饱嗝
直到死日
而他们现在活着
往事
许多往事我们清楚
许多日子听不见往事
双手抱头蹲在山顶
这双手就是往事
吃饭的口狠命喊叫
回声就像一群吵闹的孩子
然后消失
又像受惊的壁虎
钻进了大地
这座山呵长这么高
就是要抓走我们的声音
真有那么一个冬天
我们忘记了往事
不再爬山
不再打扫房顶的积雪
眼下就是这样呵
默不做声守着火炉
风把地里的土一点点刮走
而我们想起了往事
马永波
《太阳的青盐》目录及后记
总序(马永波)
序一:说几句王建民(杨争光)
序二:大道至简(刘晓林)
辑一达拉积石山系列(1985--2018)
土地
高原
儿子
土葬
村口
长大以后
相信
剩下的日子
腊月
雨水很多
祖坟
干沟旱山
往事
干草堆
那个人
农闲
门口的树
树林
懒
石头
骏马
醉汉的天空
老铁匠谈话
老姐夫
达拉积石山辞典(组诗)
1.身体
2.播撒
3.块茎
4.视觉技术
5.踪迹
6.缺席
7.绝对的骨头
8.擦抹
辑二雪花飘飞的理由(2002--2017)
水缠绕在玛尼石上
山上
帐篷里的花
旱獭和狐晒太阳的桥上
青海湖
海北
藏羚羊
看了场电影
草的边缘
骆驼的样子
谁在我们之间
草地天气预报
月亮
《月亮》之民谣版本
高原舞
歌者
古墓那儿
牧
土坎那儿
鹰在头上旋了三圈
稀少的云
太阳和冰和石头的水
从昆仑山到湟水谷地
给一个流浪的人解释天葬
金子的河床
雪花飘飞的理由
歌唱
现场浪漫主义
烤吧喝吧
从东向西收割
速写
看巨崖上的六字真言想到流动
火烧云
黑刺
尽头的人家
茶卡盐湖(组诗)
辑三太阳的青盐(1988--2017)
自以为是
交易日
耳朵EJKcpR
中国蝴蝶
门窗
具体
有水的日//www.58yuanyou.com子
要一点风
与山说话的方式:第一种
与山说话的方式:意犹未尽的一种
与山说话的方式:静默的一种
时光天使——给孩子(组诗)
1.入侵
2.谁是跟你一样的孩子
3.时光天使
4.北方
5.南方
6.每天
7.老家青海
8.简单
9.三口之城
10.挂牌子的银杏树
11.六十年代的玻璃
12.女儿
13.儿女
14.学会用筷子
15.那年在月牙泉
年龄
自然景观
没到海边
试试把家装进夹克口袋
当月牙泉成为城市
城市密林
水仙
夜与莺
赵忆
秦砖
城市攻略
天桥上的和尚
孙散的眼疾
守时
彼岸
石头街
石头上播种
进化
衣
女鬼
雨天时空
筑巢
半个世纪的荷花
雪人没有时间
大雪这天
交通导航图
大唐芙蓉园
流沙赏花
鼠标(1)
鼠标(2)
秋季返乡
入门
阳光雨
在一条名叫瞿昙的小河边
后记
后记
“现在你看/你的空樽里/有一粒太阳的青盐/晶体光洁/构型简单”,这是我的一首小诗的最后几句。本书书名就源于此。青盐是青海地产石盐的俗称,等轴晶系,晶体呈立方体。阳光是其成型的主要外力。
在我眼中,汉字就像一粒粒青盐,坚而脆,又可融化。
几乎在迷恋上诗歌的同时,我对汉字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这几年,我写下一些关于汉字的自娱自乐的话。例如:“汉字就摆在那儿,不用拼读,不用还原,不用言说,它就在那儿,它是一粒一粒的事实。它的构型,先是设立时空架构,再添加精神投射物或时空容纳物。这让每粒汉字在时间、空间、型格、态势和质量上是自足的,使汉字这种符号,在组词造句形成文章之前,就能够罕见特殊地叙说时空故事。可以说,汉字是时空结型文字。” “探求汉字缘起和对汉字形态命名是两回事,如同不能拿猿类的本质指称人类的本质,我们不能拿象形等指称汉字的本质。否则,就会把汉字无辜送进懒人语言学诊所、或西式语言学的病房里,进而引发汉字启蒙、传承、使用、变易方面的系统性问题,造就一个坏的汉语言生态环境。”
所以,我希望汉语圈诗人首先是个敬重汉字的人。
关于字词的基本元素,我看到的不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不是一笔一划,而是人的感官给定的时空,那是约定俗成的时空,心灵的时空被排除在字词的基本元素之外。这让人们在描述诸如多维多向时空时,格外费口舌。这绝对是诗歌、宗教文本或科幻文学的藩篱。音乐、绘画甚至书法不受此规制。诗歌里,使用的字词越多,诗歌的时间就越单向、空间就越狭窄。因此,诗歌语言要尽量节制,宁缺毋滥,这是我排斥形容词的原因。汉字诗歌要想上天入地,练达简单即可。一部《道德经》,就是汉字表达宏大思想时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明证,也是诗人最好的范文。
既然如此麻烦,何必读诗写诗。有位诗人的情况最能回答这个问题。诗人毛泽东。智慧、理想、权力……他拥有太多,可是他得写诗,他的诗比他的长胜之师柔软,比他的哲学巨著坚强,比他的潇洒书法更淋漓尽致。就是说,诗歌能到达其他文本和其他艺术形式到不了的地方,这是诗歌存在的原因。
在写一首幻想月牙泉成为城市的诗时,诗歌的内在时空顺出这么几句:“月牙泉城的少女不长翅膀就能腾飞∕飞翔是她们唯一的职业∕她们飞临哲学追索不到的地方∕她们飞抵上帝梦见的地方……”此处,把诗句中的“月牙泉城”改作“诗歌城”,就是我想说的意思。顺着这个意思猜测,“哲理诗”是分行的哲学论断;“爱情诗”是分行的情书;至于“打工诗”、“学院诗”的分派法,离诗更远。我不能掉进这样的陷阱。
中华民族尽得东方智慧的精髓,成为拥有诸多特质的民族,当然也是诗歌民族。尤其是汉字,曾经摞起了那么高大的诗歌建筑群。可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不会写诗了,在诗中说话龇牙咧嘴。于是理论铺天盖地。
我喜欢诗歌理论、厚待每个诗人对他自己哪怕片言只语的诠释。我的阅读,理论读物多于文学作品,可是,一旦书写诗行,我就把“理论”忘啦,忘了别人的,也忘了自己的。这与我随意任性的人生有点相似,时而洒脱,时而尴尬;时而追逐文字却被文字抛弃,时而我背叛文字却被文字包裹。
出于同样的顾虑,在我读诗写诗的过程中,我只顾埋头看待自己、周边眼见的感知的一切、自己与这一切类似亲人或姻亲一样的关系。不论年龄增长,见识增减,以诗歌的眼睛远近探看时,永远如同一个孩子初涉人世,又是一缕年迈的游魂历经沧桑。这样,我可以在一个忘乎所以、悲天悯人的界面里,看见世界上最坚强、最柔软的存在,抚摸人群中最坚强、最柔软的根性,挥动自己最坚强、最柔软的感念。
既然有点文化知识,案头有《新华字典》,我的诗别无他途,无法向下、偏左或朝右,唯有向上。尽管我的诗说:“我是大家的水∕大家逐水草而去远上蓝天∕我,跌进了深渊”,但是,也经常“邻家笑起飞天女∕隔壁端坐来世佛”;或者,“喝酒的人/无法和自己的想法呆在一起/他见不到自己的影子/他把影子留在土里/他从村庄上空飘走”。
当下诗歌逐步回归其本性,不能养家糊口,不能博得功名利禄,但可以赚得友情,可以丰富文化宝库,这才是诗歌的福分,是诗歌永不堕落的原因。所以,诗人有的是时间写好诗歌,几年磨一首也可,社会不会催你,孩子的奶瓶也不会催你。唯一拖住你、鞭策你的,只是你诗人的良知。如果有人读诗发现“诗歌”堕落了,那么他读的绝对不是诗歌。
这也是我现在愿意出版这本诗集的原因。
当然,如果没有杨争光、马永波、刘晓林等朋友们的长期关怀,我肯定还在沉寂中。我一直心存感念。
王建民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