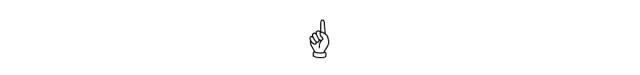普通孩子
去看火焰燃烧
我们去看火焰燃烧:它如何追逐阴影,怎样猛地膨胀、爆裂,趋近一种迷人的威胁。宁城春天总有我们这样的人,举着手电筒在天台,琢磨废纸、布料、木头和打火机的反应,仿佛今晚不想做梦,明天没有日子要过。
火焰还没熄灭,我们就开始朝楼下扬洒邹明尧的骨灰。骨灰被装在商场购物袋里,今晚我和李骏轮流抱着它,带它饱餐一顿四川火锅,在NIKE员工监督下试鞋,去了两趟书店里的洗手间,看完一场不满座的沉闷电影,最后,李骏说,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得做真正的告别。
邹明尧的离开一度不被视作真实。他总是比我们更超脱一些,或者说,更像“不在此间”。2017年他有过两次自杀,一次割腕,一次上吊。2018年他不自杀了,每周三周五放学后都骑单车去山上龙华寺,躺在大雄宝殿,侧过身面朝落叶飞旋的庭院。今年,他忽然表示要考大学,脱离了我们的三人小团体,努力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特别是化学,能考班上前几,很快二本在望。
我们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正在消失、似乎本不该存在的人,以至于死后骨灰都不能保留完全,要在空中飘飘扬扬,分散、洒落在这与他格格不入的人世间,附着在空气中每一粒尘埃上,落在河流、树梢、路灯、阳台,或是被人和动物吸入体内消化干净,不留任何痕迹。
但是邹明尧的离开无疑意味着什么,而我们得为此去寻找一个答案,或是加入成为答案的一部分。
情人的臀
春雨彻夜连绵。丁警官下车抽烟时,想的尽是不相干的事,比如妻子的乳腺癌;今早打开小区快递柜,柜里待着的那坨气质安详的狗屎;若干年前路过壮雄牛肉火锅店,响彻店内的一首《小茉莉》;甚至,他在想非洲某部落酋长吃那么多烧烤,会不会经常上火。
“老大,这都来十几次了,哪有那么多要看要想的呀?”原本坐在驾驶座的小孙探过身子,趴在副驾上,把头伸出车窗道。
丁警官漫不经心看他一眼,想起莉莉也经常在床上光着身子这副姿态,区别是她后腰凹得更深,臀部更翘,把手放在上面,能触摸到鸡皮疙瘩的细微颗粒,好像被大火烧焦、变得如同板寸发型般的原野。相较之下,小孙这臀部没有曲线可言,触感倒是不得而知。丁警官回过神来,发现烟已抽得差不多,顺手在车顶掐灭,缩身进车里,但没有关门,一只脚仍踩在外面水泥地上。
借着路灯,可以看见对面巷子空无一人,未来几个月,估计也没谁有勇气在里面走动,连巷子外边的24小时便利店都关门歇业,贴上告示:旺铺转让。这起命案发生得不是时候,上个月离这里几个街区远的一条巷子也发生命案,作案人是一名货车司机,已经逮住塞进牢里,但不到一个月,巷子杀人案再次发生,重新掀起宁城人无论是茶余饭后,还是城市论坛、微博里热火朝天的议论。大家都说,这是模仿作案,也有人认为,真实凶手还没抓到,货车司机是无辜的。反正闹得满城风雨。
说实在,干了二十年刑警,丁警官早就对杀人案件习以为常,甚至可以说,腻味,这一次如此上心,出自一他也闹不明白的原因:他感觉,自己脑袋里被塞进了怪东西。接到案子那天下午,他做完例行工作:赶往现场询问进展,问话刑事技术人员,在周边走访和调查,当天晚上,也例行前往情人莉莉家,两人例行做爱。
做完爱,他例行手一探、一抓,本该放纸巾盒的位置却空空荡荡。一切都从这一扑空开始,如果他当时手再伸长一点,在台灯背后摸到纸巾盒,不致扑空,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将例行洗完澡回家,在第二天例行查案,查不出结果,就例行推给其他同事,然后例行遗忘。
“没纸了?”当时,他问。
“床头柜下面抽屉找找。”
他仍是看也不看,手又一探,抓住门柄打开,往里边摸索,当即碰到一样四四方方的坚硬物体,抽出来看,是一本书。
“嘿,”他一字一顿念,“世,界,未,解,之,谜,修,订,版,《世界未解之谜修订版》?你不是不看书吗?还一看就看这么有知识水平的。”
莉莉嘴一撇,不以为然:“你别瞧不起人,几年前我表妹送给我的,我看了大概有一半呢。”
“你这表妹不了解你呀。”他坐起身,靠在床背,岔开双腿,示意莉莉为他口交,她照做了。他点了烟,随手翻开书本:“解密外星人,应该有点意思。”
草草阅读两个段落后,他瞅见配图,上面用极为蹩脚的电脑技术绘制了一个外星人,他想,还修订版,显然八十年代水平。配图里,外星人正走在一条通往盘子造型的飞碟的阶梯上,身子瘦骨嶙峋,支撑着偌大脑袋,后者整个转过来,眼睛足足占据半张脸,却是漆黑无神地望向前方,整副模样活像战乱国家饥饿儿童。不知为何,他竟然看出些许寂寞的神态来。
“欸,”莉莉张开嘴巴,用手指弹了弹,“怎么忽然软了?”
那个外星人的神态让丁警官很在意,并且不知不觉中,毫无根据地,他将它与案件中死去的少年联系在一起。这位少年被人持刀捅死在巷子深处,眼睛没有闭上,也是空洞地望着前方,同时很难形容是“死不瞑目”,更像自然而然的状态,似乎少年并非遭遇不幸,被人忽然捅死,而只是出了神,在呆望巷子上空停留高压线、或是直接掠过的麻雀。处理案件时,这副模样的少年和《世界未解之谜修订版》配图里的外星人总会交叠在一块,同时浮现在丁警官脑海。
“怪东西。”丁警官嘀咕道,动了再去看看巷子的原由网念头,推开车门,掏出烟盒,想抖出一支烟,结果空空如也,于是捏扁揉成一团扔到脚下。他向小孙伸出两根手指头,比了个夹烟动作,又想起他不抽烟,长叹一声。偏偏这时候烟瘾厉害。焦虑像水泥从鼻腔灌入,流经咽喉,淤积在腹部。
“我去趟便利店。”说着,丁警官撑起伞,离开警车走入雨中。
走了两条街,才找到一个营业中的便利店。结账时,他听见身后自动门打开,响起“欢迎您”的电子女声,转头看,是一位穿黑夹克,身材高胖,脸却出奇瘦削的中年男人。白炽灯下,可以看到他头发和夹克上一层水雾。
“给我来包中华。”黑衣服男子对店员说。声音有些沙哑。
“哟,烟瘾这么厉害?伞都不撑,”店员打趣道,“别把我店里东西弄湿了啊。”
丁警官结完账出来,发现雨势越来越大,干脆站门口点烟,想着抽完再回车里。刚猛抽两口,又听门打开,电子女声播报“谢谢惠顾”,黑衣男子走出店内,和他一左一右分站两边,也点了支烟。
黑衣男子悠悠抽一口,转头望向丁警官,显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但最终还是搭话:“警官,原由网大半夜还在查案呐?”
丁警官斜睨他一眼,不以为然,边从鼻孔吐出烟雾,边“嗯”一声。
男子笑眯眯地:“我没带伞,等会都不知道怎么走。”
“怎么来就怎么走。”
男子一听,识相住口。
丁警官把烟抽完后,又点着第二根,这时男子也把烟抽完了,一个抛物线将烟头丢进雨中,双手插兜,道:“你一个人跑这么远,撇下那个小警官,他不害怕么?”
丁警官仍是不想理睬他,吞吐几口烟后,忽地一琢磨他的话,不禁心下一惊,转过头去,却发现男子已经不在身旁,雨声中夹杂着远去的脚步。丁警官懊悔莫及,伞也顾不上撑开,快步追上前去,黑暗中两次脚下打滑。这时候,突如其来的闪电照亮四周,他止步在一个十字路口,狼狈环顾,却是半个人影也没有。而后,自天空深处,雷声轰然大作。
外星来客
初一那年,一档民生新闻节目连续两天播放灵异专题。她妈妈爱看这档节目,经常在给家里人盛刚煲好的汤时,叮嘱九点半要准时换台,然后时间一到,一家人边喝汤边收看电视。
她坐在背靠阳台落地窗的沙发上,门敞开缝隙,凉风吹抚后颈。爸爸“呲呲呲”地喝着汤,和洗手间下水道咕噜咕噜的声音此起彼伏。妈妈则闲不住,放下碗,从厨房拿来簸箕、粿皮、馅料、粿印,又搬出一张塑料凳坐下,包起红桃粿来,眼睛却片刻不离电视屏幕。新闻画面上,是和此刻安逸得如出一辙的夜晚。画面是用手机拍摄的,水盆里的水一样摇晃。
没多久,忽然响起电影《X档案》的配乐。突如其来的诡异曲调让她浑身一颤,雪梨炖瘦肉汤差点洒出来。这时,一抹状如飞蛾的白光出现在画面里的夜空,掠过后转瞬即逝。接着,主持人要求放慢镜头。那抹移动的神秘白光一帧一帧被呈现出来,像在分析扒手的犯罪手法。但镜头拉近,仍然看不出是什么。
之后,主持人说了些诸如疑似飞碟、引起当地居民恐慌、要请专家解析之类的话,便切进冠名广告。她没等广告进入主题便放下碗躲进房间,缩在被窝里。哪怕闭上眼睛,那抹白光也在眼前一闪而过,反反复复。
同年暑假,她去逛新华书店,相中一本《世界未解之谜修订版》,当时并没多心,回家后躺房间床上阅读,不料后边翻到外星人专题,当即就瞅见电脑制作的外星人配图:一个外星人正登上飞碟,长得头大身小,两个深陷的漆黑眼窝占据脸三分之二,没有表情,伸长的触手蚯蚓般扭曲,尾巴耷拉着,像是阳具长反了。她惊呼一声,吓得没法喘气。迅速起身,将书本塞进衣橱深处。一抹脸,手上都是泪水和鼻涕。当天,她把书送给来家里找她玩的表姐。
再后来,她发现自己开始害怕天上来的东西。太空飞碟、外星生物也好,闪电雷鸣、阳光雨露也罢,她都害怕,以至于多数时候低着头走路,不敢轻易抬头看天。她妈妈首先发现不对劲,说,这姑娘突然间怎么回事?蔫头耷脑、魂不守舍的。她爸爸则表示,青春期嘛。
发生改变是在高二。在一次每周例行的升旗仪式兼全校大会上,三个男生因为盗窃学校附近电玩吧的游戏手柄,被教导主任请上升旗台,当着全校师生面训斥。分站两边的俩男生背着双手垂头丧气,中间那个染了一红绿相间头发的,却把头高高扬起,脖子又细长又笔直,要不是穿着校服,还以为是鸵鸟。
“高二六班的这三位同学,张大滔、邹明尧、李骏,严重违反校规校纪,经过校方郑重、严肃的讨论,决定予以通报批评、留校察看处理,张大滔,”说着,教导主任把话筒伸到脑袋低垂、眼睛盯着鞋尖的其中一个男生嘴边,“下次还有再犯意愿吗?说给全校同学听听,嗯?”
“看……看情况吧。”那男生仍是低着头,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道。
台下学生笑成一片。
“担米个扑母话!”教导主任一气急败坏,蹦出几句潮汕粗口,虽然话筒没对着自己,但也足够让不少师生听见了。笑声蔓延开来。台下甚至有几个老师也在偷笑。
“毕竟可能以后要靠这个混饭吃。”男生继续嘀咕//www.58yuanyou.com道,这让台下笑声更是连绵起伏,“当然,在别的情况下,也可能再去偷东西,至于是哪种情况,现在说不上来。”
“一派胡言,恬不知耻!……你,还有你,”情况出乎教导主任意料,他想结束失控场面,迅速拿回话筒,转而冲中间那个抬着头的男生发难,“你这头发什么意思?学校明确规定不允许染发,明知故犯,罪加一等!”说着,揪起一撮头发打量,“你看你,身为中国人,头发搞得花花绿绿,你是中国人吗?哦,哪国人也不这个颜色,我看你是外星人!”
她在台下一听, 下意识浑身哆嗦。
这位一脸桀骜不驯、名叫邹明尧的男生,竟然有些羞涩地笑了一下,鸵鸟脑袋歪向教导主任面前,将话筒轻轻拨到自己嘴边,忽然变得一本正经,像在朗读课文般字正腔圆地说:“我确实是从外星来的。绝非哗众取宠,我是说,在成长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这颗蓝色星球,我或许是别的物种,在十七年前的某一天,无辜地、意外地坠落此间。我想自己应该去当宇航员,这样就有机会被发射到太空,斗胆离开飞船,回到我的家乡,科比星,波多野结衣星,刘建军星……都是乱起的名字,或者干脆流浪宇宙,蜷缩着像一个母胎中的婴儿,一光年接着一光年,哪天就被某只翼龙模样的奇怪生物叼走,我会和它搏斗,驾驭它冒险,去太阳,去黑洞,可能还会回到地球看望我奶奶,看望大滔、骏哥,看望你们……”
说到这里,教导主任仿佛才反应过来,想拿走话筒,但是男生手一拉,话筒已在自己手中,并摆手示意教导主任退到一边。教导主任不知所措地愣在那,环顾四周寻求援助。
男生继续说:“但你们都看得出来,我不是那块料,哪里可能成为宇航员,那么,全校师生能给我支个招吗?”
站在前面的同桌转过头,脸笑得通红,对她说:“搞什么呀,这几个出了名的混子,一个比一个有个性。”
但是她听得呆了。她感觉到一种冲动,后来明白这更意味着一种勇气,终于在今天,她发现自己可以直面多年来的心结,面前这个头发花绿、言行古怪的男生,对她而言有一种暖和的潮汐涌向脚掌般的温柔,他所讲述的外太空,竟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美妙可能。通过他,她或许可以找到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将告诉她,该怎样面对被神秘、未知所包裹的恐惧。
当天课间操时间,她来到高二六班后门,压根不用张望寻找,一颗红绿色脑袋趴在桌上,很是醒目。他正呼呼大睡。她快步走到他面前,两只手往桌上猛地一拍,连自己都觉得稍显粗鲁。男生惺忪双眼抬起头,下巴、右手臂弯上全是口水。
在教室闷热、不流通的空气中,她能清楚闻见那浓重的口臭味。
她说:“你好啊,外星人同学。”
飞机降临在植物王国
在这个比往年更寒冷的冬天,他接到市里植物园进行修缮工作的通知,所有员工得在家//www.58yuanyou.com办公一段时间。
“听说山上都下雪了。”同事说。
平常他周六日也会往植物园跑,现在每天,他坐在沙发上沏几壶铁观音,看看纪录片,甚至还能给刚放寒假的女儿做午饭,在妻子厂里下班时亲自开车去接驾。她们都觉得受宠若惊,妻子说,要不你辞职安心做家务活,我来养你们。
这句话让他意识到多年来,自己确实对家人有所亏欠,他想,我得有点良心。于是趁着女儿放假在家,开始尝试体贴她,比如询问用不用拿点钱买衣服,午饭想吃些什么,或者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就跟平日里关注一株植物的成长无异。他认为这是植物园工作对自己的正面影响。
在植物园的这些年里,每天,他披上不怕脏的黑色夹克,穿过花圃小门,走进砌着水泥墙的温室,独自站在玻璃顶棚下,或者走在树林间,树叶缝隙筛出阳光碎屑,泥土嵌进胶底鞋纹路时,他总会付出最大的热诚去面对花草树木——无论是需要悉心养护的特殊物种,还是稀松平常、仅供观赏的那些,通过触摸种子、花叶,他的指尖似乎能够感受到某种缓慢发育的流动,人工与天然两相结合的质感平衡得恰到好处,而当拨开剪去杂草、或是换上更优良的土壤时,他认为自己的一切干预从技术手段来说无可挑剔,从自然法则来讲正当合理。
有原由网时他想到,从皇帝沦为平民的溥仪,晚年也是在植物园里饲养花卉,给植物剪枝条,用胶皮管子往水缸里蓄水,日复一日,枯燥无味。在溥仪大起大落又回归平静的人生中,似乎无论做什么,都有种试图把一切抛到脑后的意味。而他自己则相反,在植物园,他从一介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开辟土壤、光复绿意的皇帝,一切都被装进自己脑中,无比充实。
有观察,就会有迹象。发现女儿有秘密,是在又一个看纪录片看得昏昏欲睡的午后。他斜靠沙发,半眯眼睛,即将入睡,却忽然隐约看到客厅隔壁走道里,女儿悄悄探出脑袋,正往他脸上张望。而后,女儿三步并作两步穿过客厅,打开家门又轻轻关上,离开家。
这个寒假,女儿一星期出四五趟门,问及原因,都是说去同学家里学习,他还特地确认,“女的吧?”得到肯定回答后松了口气。有几次,女儿脸上会泛起些微红晕,他也没怎么在意。但是今天这一回,女儿出门后,他倏地从沙发上坐起身,顿时疑虑重重。
他来到女儿房间,翻箱倒柜搜个遍,什么也没发现,倒是在书桌上看到一本化学笔记,详细记录着每道题的答题思路,一些基本概念也会做解释,以女儿市里化学竞赛能拿前几名的水平,似乎有些多此一举。他想,大概是给同学准备的吧。
过了两天,女儿再次出门,五分钟后他也跟着离开家。他驾车尾随女儿,保持二十来米距离。她步行到马路对面公交站,乘坐二路公车行经四个街区,在另一个公交站下车,路过银行、便利店、外贸服装店、药房,在一栋黯淡、残破的灰色居民楼面前停步,站在一棵光秃秃的木棉树下。他也熄了车子的火,压低身子,几乎是趴在方向盘上观望。
女儿今天身穿鹅黄色长裙,外套一件棕色棉服,脚下则是一双黑白配色跑步鞋。头发梳了两根小辫,显然精心打扮过。
没多久,灰色居民楼防盗大门“喀哒”一声响,有个顶着开了瓢的西瓜一样的头发、趿拉着人字拖的男孩自楼里信步走出,从背后把头伸到女儿面前,一只手搭上右肩,女儿似乎被逗笑了,转过身挽起男孩胳膊,俩人手牵手走进居民楼里。防盗门再次“喀哒”关上。
坐在车里的这位父亲愣了一下,泄了气,头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伸出左手揉前额,揉得通红。
接下来两个星期,他驾车尾随女儿四次来到此处,每次都是那个混混模样的男孩开门把女儿带进楼里。他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有何意义,或许他该向女儿询问,但这种想法只浮现过一次,很快被抛到脑后。他隐约觉得,这事跟女儿没关系,或者说,女儿处于一种被动姿态,她欺骗父母,单独来到这里,和男孩待在一块,必定不是全凭自己意志,而她本来能够乖巧成长。
他想起曾经有一回,植物园闹虫灾,当时天气逐渐转热,园内不少树上出现竹节虫,光论单棵树,数量就能从十来条达到上千条之多。只要轻轻摇动树干,竹节虫就雨点般纷纷落下。那段时间,他家也没回,一个人奔走在树林间,把老叶病果摘下,起火焚毁、深埋地底,来来回回喷洒药剂,同事们都惊叹于他的偏执。
但是用处不大,虫灾严重程度出乎意料,甚至隔壁山头的龙华寺也不能幸免,住持慧净和尚还亲自过来,向他请教驱虫方法,但最后也只能和一众僧侣跑到山下农庄避难。后来,园里向林业局申请用飞机喷洒药剂。他一个人站在附近山头观看,飞机嗡嗡声响不绝于耳,巨大的挫败感涌上心头。
这会儿,他明白了,哪里是植物园的工作塑造了他,而是他的天性选择了植物园的工作。守卫植物园,和竹节虫为敌,看着后者尽数死于手底下无疑是快乐的。而后来败下阵的挫败感,他再也不想要了。他想,自己更应该去了解这个男孩。于是某天晚上,女儿离开那栋楼后,他没有跟随她回家,而是继续在车里待着。
正犹豫要不要想方设法进楼查看时,防盗门忽然打开,男孩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现身,走进隔壁一条巷道,而后空着手出来,重新回到楼里。
总得做点什么。他想。于是下车过马路,进到巷道。巷道昏黑,是个死胡同,尽头墙壁下放置两个垃圾桶。他走上前去,看见一个是空的,另一个则只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显然是男孩刚刚手里提着的。他把塑料袋取出,盖上垃圾桶盖子,把袋子放上去,用手指按捏,如此柔软、饱满。而后,他毫不犹豫打开袋子,倒出里面的东西:烟盒、罐头、奶茶杯子、可乐罐、一双破损的帆布鞋,一大坨脏抹布,很多纸巾团。还有两个用过的避孕套。其中一个正涌泄出浓稠乳白、似乎还温热的精液。
难以置信的同时,愤怒也涌上心头。一瞬间,男孩的脸在他脑海中变成了竹节虫模样,他胳膊用力一扫,将塑料袋和所有东西拨到水泥地上,猛地把垃圾桶踢翻,转身望向狭长的巷子及其出口,心中只想:害虫必须铲除。
荷花不了情
过完正月十五,寺院少有香火,很快变得冷清。
住持慧净和尚每天都会去一次观音亭,等待荷花开放。由于请了附近植物园的员工做反季节栽培,池塘里的荷花一年四季都能开。住持站在亭子里,或者桥上,从各个角度透过温室玻璃观察荷花时,偶尔会想,这或许是他的业障,看见因,就执着于果,有时因还未发生,也有着关于因的念想。为了缓解这般心情,在处理寺院事务的空暇时间,住持会在寺里散步,像从未来过这里的游客,目光在某处停留,有所思索,又再游移到它处,试图随性些。
这天看完结苞中的荷花,他行经僧舍、大悲殿、地藏阁,经过大雄宝殿时,不禁又往里头张望,眼前依稀浮现那个男孩的身影。曾经许多个午后,他总是来到寺里,就在大雄宝殿中,四仰八叉躺在佛像面前,而后又被经过的僧侣弟子赶走。弟子们多次向住持汇报过,直到住持说,他既然执着于此,那就不管他了,也许心中有苦处,佛祖不会见怪。
去极乐堂之前,他久久地仰望钟楼。天空青灰色的光线涂抹在石壁上,他伸出手抚摸砖块,体验到真实的粗糙触感,郁结的心绪才轻松些许。如今,那个男孩已经在极乐堂中了。一个月前,住持看到男孩遗像,才知道他已离世。来看男孩的人都只是在福位前默默站着,一开始是他奶奶,然后是一个绑着两条辫子的女孩,后来有两个警察也来了,这让住持明白,男孩身上发生了不幸之事。
掐着佛珠,住持推开门,缓缓步入堂中。年少时候,来到这般地方总让他备感压抑。那时候龙华寺还没落成,他在江西一座寺庙里修行,常因悟性不足被师傅训诫。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昏暗中沿石阶而下深入地宫后,徘徊在灯火通明、由诸多福位和佛像组成的金碧辉煌的迷宫里时,他常想,那些离世的人,是否正在琢磨着他,并且有话想对他说?有时他则想,被琢磨也罢不被琢磨也罢,两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在各自世界里,人们与触手可及的他人互相扶持生活,但有时也会试图从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寻找慰藉,这也是人们来极乐堂纪念死者的原因,西天世界的人们,必定也想通过极乐堂一窥人世气息、或是与来访者交流罢。
巡查完毕后,住持离开极乐堂,准备前往斋堂交代事宜,这时,听到身后似乎发出些许动静,回头看,一棵香樟树正哗啦啦掉叶子,落叶在地上打滚,伴随凛冽冷风,由点及面迅速铺开,覆满了整个庭院。他静静地看着,不知过去多久,忽然间,眼角瞥见两个人影从极乐堂蹿出来。住持定睛一看,是两个少年,动作很快,正脚踩落叶发出嘎吱嘎吱声响,往寺院大门跑去。远处斋堂门口的弟子也发现了,连声呵斥,疾步赶来。
以住持的腿脚自然追不上少年们,他放弃这一念头,转身回到极乐堂。行进过程中,他想到,两位少年的年纪,似乎与那个平日躺在大雄宝殿里的男孩相近,当即心念一动,千回百转,找到男孩的福位。福位暗锁已被撬开,他的骨灰盒消失无踪。黑白遗像立在原处,此刻看来,男孩的表情竟透露着一股戏谑意味。
看着遗像上的男孩,住持微微一笑,说:“这里太闷了,对不对?”
住持回到落满香樟叶子的庭院,踏上通往观音亭的小桥,桥下池水中,荷花开得鲜艳。
看完了,听首歌吧。

手拉手
图片出处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