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ing 的双重含义探源
选自邓晓芒著《中西哲学三棱镜》
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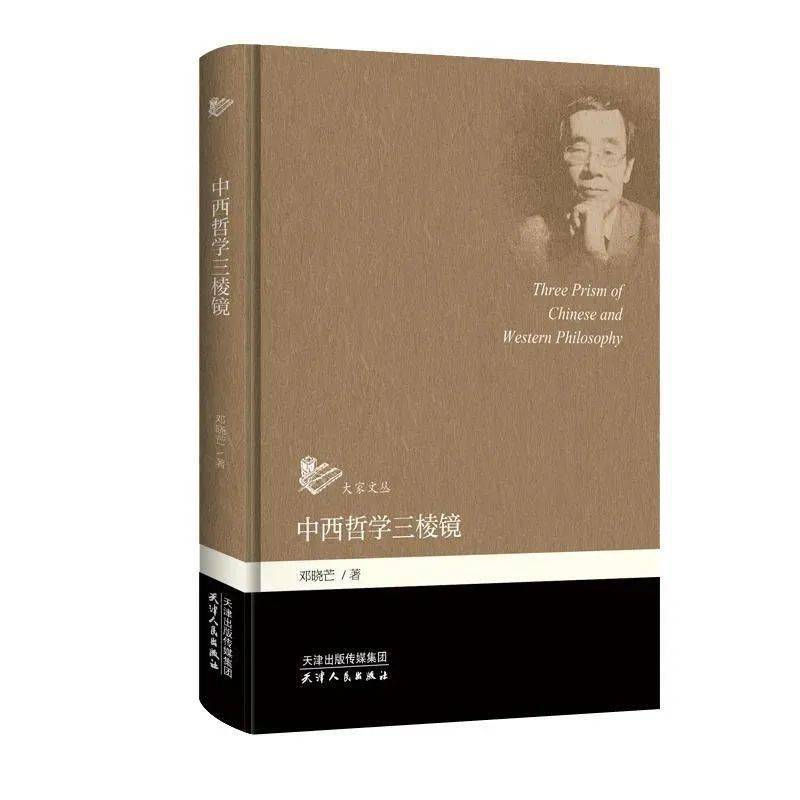
国人在引进西方哲学之初就发现,西方的 Being 一词(英文,来自希腊文 ,相应的拉丁文为 esse,德文为 Sein)是个很令人头痛的词,它本 是西方拼音文字中的文法上的系词(“是”),但也有动词的含义(“有”“存 在”),同时还有名词的含义(“本体”“实体”或“存在者”)。头痛的是,古代 汉语里没有固定的系词,因而不论我们用动词还是用名词来译这个词,它作为系词逻辑上的含义都被丢失掉了,而这正是它最根本的含义。西 方哲学正是从它的逻辑(语法)含义中,由它的逻辑动作(联系)引出其 动词含义,再将其固定化为名词含义的。现代汉语经过欧化后虽已确定 “是”的系词作用,但不像西文里那样可以和其他动词搭配来表示时态,因而可以加在任何句子中。再加上“是”的另外两个中文意思“正确”和 “此”并未废止,情况就更显复杂。现在是各种译法(哪怕在同一译者的同一本书中)杂然并存的局面。若从哲学层次上讲,中文里与 Being 层次 相当的词是“有”,但“有”的本义是“具有”“拥有”,这在西方哲学中是个 很低层次的概原由网念,只是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一。已经有不少人建议用 “是”来强行翻译 Being 一词(如三代学者中的陈康、王太庆、王路等),陈康(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和其他人(如吴寿彭等)还进行了认真的尝 试,但除了令读者殊感别扭外,也确实损失了西文中本有的一些含义。
目前比较能够兼顾各方面的译法我以为还是“存在”,这是一个动词兼名词的双声词,拆开来单用“在”,也可以表达系词的部分含义,这也是当前最通行的译法。当然仍有一部分含义表达不了,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通过一词多译加注释来解决。由此导致的西文 ontology 一词的译名也纷乱不堪,“有论”“万有论”“存在论”“存有论”“本体论”“是者论”等,不一而足。
但我认为,时至今日,到底是用中文的哪个词来译其实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倒是应当想一想,为什么汉语中就找不出一个与西文的Being 相当的词。人们大多看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的习惯,不重视语言的语法形式,这诚然是不错的;但古代中国人为什么不重视逻辑和语言?这只有通过对中西语言后面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比较才能做出说明。
其实,西方人并不是单凭逻辑思维就建立起了他们的 Ontologie 的, 要使逻辑上的系词 on 成为最高的形而上学概念,还必须逻辑本身(包括on 本身)具有一种无所不在的能动的超越力量。海德格尔所谓与“在者” 不同的“在”就是这种力量(“在起来”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一个逻辑上抽象的系词成了“存在”和“本体”。西方人之所以重视逻辑思维,根本说来是由于他们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即个体自由精神。逻辑、语言被西方人看作他们的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必原由网要手段和方式(所以海德格尔 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在古希腊是由他们的城邦民主制的社会生活状态所决定的。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在逻辑上严密的(因而有普遍效力的)法律是保障每个自由公民的权利的有力武器,而法律本身是由公民全体按照自由意志来制定的,所以按照每个人都同样使用的语言而说出来并写成文字的东西在希腊人看来是具有神圣意味的 (“神圣的逻各斯”)。在这种神圣的语言中,联系词“是”不仅仅具有联系两个词项的作用,而且代表说话主体的一种自由表达行为,它就是主体的“存在”。如陈村富先生指出的,希腊文的“是”的词根 eimi 本来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运动、生活和存在”#。换言之,说话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联系起来,“联系”是一种动作,而且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根本性的动作,因为“是”就是一切命题、表述和言说的基础,一个人想要存在就必须“说”,不说就不存在,懒得说就是懒得存在。
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不仅是语言学精神和逻辑精神(逻各斯精神),而且是个体自由精神(努斯精神)。中国自古以来的现实是只有一个人能“说”(所以黑格尔说“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说了是不算数的(“说了也白说”),甚至是不准“乱说乱动”的。而这唯一的一个人的说其实也并没有“说出来”,而是隐藏得很深的,随时可以“ 虎变”的,因而是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悉心体会、揣摩、猜测但却始终神秘莫测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伴君如伴虎”)。在专制集权的高压之下,“说”(语言)是没有普遍性的。于是当权者凭自己的任意可以口含天宪、朝令夕改,老百姓则只有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的份,只有被动地说,而没有主动地说,也就“懒得说”了,他们是一群“沉默的国民”(鲁迅语)。所以在中国,语言根本不算一回事,更重要的并不是说出来的东西,而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关键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是谁来说,其次是他为什么要说。至于一般的个人,因为从来也没有自由,时时压抑着自由意志, 也就逐渐丧失了要“说”的冲动,除非你不要命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历来没有把“是”字作为一个固定的联系词单独突出来加以研究,这是因为“是”字正和它所代表的语言本身一样,在中国人心目中本来就是无足轻重的。古希腊巴门尼德提出了西方哲学的两大原则:“一条是:它是,它不能不是”(参看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另一条是:它不是,它必定不是”(王太庆译法)。相反,在中国人日 常生活中通行的原则却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不难看出,这句话中省掉了的一个主语就是“有权者” “人主”。可见,中国人对语言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权力话语”的理解,话语是霸权的工具,而不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不是自由言说的渠道,更不 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单独的、不依赖于某个权威的语言在中国人眼 里是没有价值的,语言的逻辑(语言的前后一贯性、“一”)如果妨碍权力 的施行,则被弃之如敝屣,甚至越是逻辑上言之成理,越是被视为“巧言善辩”“妖言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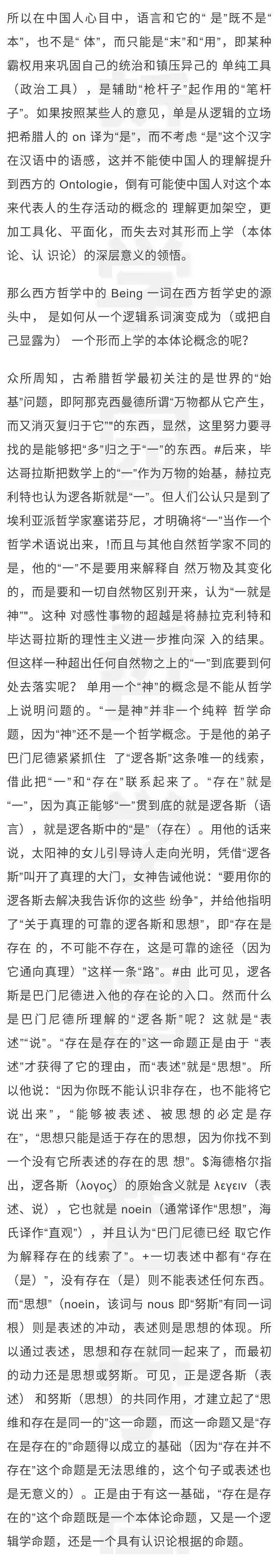
巴门尼德以后,讨论存在和非存在的话题就多了起来,各种见解五花八门。但直到柏拉图那里,都有一个致命的毛病,这就是对各个不同含义和层次的“存在”未加区分。亚里士多德对此非常不满,他说:“一般地说来,如果我们寻求存在的事物的元素,而没有把事物之被称为存在的那许多意义首先分别清楚,我们就不能找到那些元素……因此,企图寻求所有存在的事物的元素,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都是不正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存在论,即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说,首先就必须对各种各样的“存在”加以清理。但问题是,如何清理?或者说,依据什么标准来清理?显然这种清理不能仅凭内心的体验或信仰。亚里士多德追随巴门尼德的传统,从逻各斯即表述和说话的方式来着手这件麻烦的工作。他认为,我们平常说话,最常用的句子结构就是“S是P”,其中 S 是主词,它代表这个句子所表述的主体或“ 什么”,P 则是宾词,它是这个句子中用来表述主词“怎样”的。“怎样”和“什么”都是“存在”,但通常我们只有先了解了“什么”才能了解它“怎样”,“怎样”是依附 于“什么”才得到了解的,所以这个“什么”就应该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第一存在”,亚氏把它称作“实体”(ovotA,与 oU 即存在或“是”同出一字根,又译“本体”)。于是,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句子的逻辑结构的分析,给实体下了一个定义:“实体,就其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别的人或某匹马。”(对实体的这一定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这是一个纯粹逻辑上的规定,即实体必须是一个绝对的主词,而不能用作其他主词的宾词。显然,只原由网有个别事物的“专名”才是这样的“第一实体”,而种、属、类虽然也能当作实体(主词),但只能作为“第二实体”。二是“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这是对个别实体的进一步规定,如“白色”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存在于个别事物如“苏格拉底”里面(作为他的“属性”),但苏格拉底不存在于任何别的事物里面,而是独立自存的、与其他个别事物相分离的。可见,所谓“第一实体”,就是指个别的东西、“这一个”( )。 唯有个别的东西才是分离地独立存在的,也才是一个命题中一切其他成分赖以生根、得以获得 “存在”意义的基础。在对实体的上述两个规定中,虽然还是立足于语言逻辑上的分析,但实际上已经渗入了本体论上的考虑,特别是第二个规定,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第一个规定的本体论根据:为什么实体“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恰恰是因为它“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而是本身独立存在的主体。反过来,正因为实体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它的“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在保持自己的单一性前后不变的同时,实体却能够容受相反的性质”,即可以用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宾词来表述它,而无损于它的存在。所以实体就是一切逻辑表述和现实存在和变化的“基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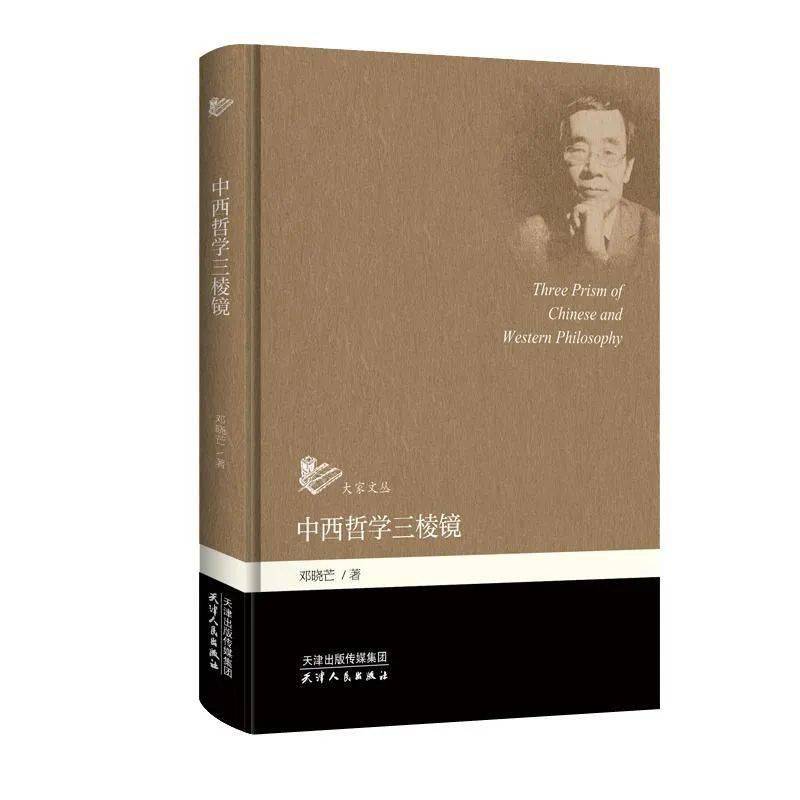
邓晓芒教授最新学术力作 《中西哲学三棱镜》
在《范畴篇》的这一定义中,亚里士多德首先展示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实体”的逻辑意义和本体论意义的不可分性。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单纯的展示,而是要进一步探讨:实体的这种性质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使实体的这种个别性成了个别的?为此,他分析了个别实体的构成。他发现,个别实体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它的“质料”,一是它的“形式”,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使前者“成形”的主动的东西。静止地来看,实体作为一切逻辑表述和现实存在的“基底”,就是指这一堆质料,所以可以把质料理解为个别实体本身;但个别实体之所以是 “个别”的,就在于它与其他个别事物的“分离”或区别,所以真正说来,是形式才使实体成为与其他事物不同的个别的东西,使这一堆质料与其他那些质料区分开来而具有了自己的个别性。如果没有形式,质料毋宁说只是普遍之物,与其他质料混沌一片,不可能有任何区别。所以与《范畴篇》中的仅仅是消极的定义不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从积极的意义上把实体规定为形式而不是质料,这是从事物得以“成形”的动态活动方面来考虑的,标志着对实体理解的一种深化。在他看来,质料只是 “潜在的”实体,形式才是实体本身的“实现”(或“现实的”实体)。如何“实现”?凭借形式的个别性。在这里,个别性就不再只是静止的与他物分离的状态,而是被理解为能动的创造性或独创性了。所以上帝作为“无质料的形式”或“形式的形式”,就是绝对的创造性、无所不在的“现实”(“实现”),就是无限的“努斯”或“对思维的思维”。
由此可见,在亚里士多德这里,逻辑学和本体论(宇宙论和神学)共同构成了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体现了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一种完美的结合。其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从来都不是后世所谓的“形式逻辑”,而是与本体论(存在和实体的学说)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而作为“系词”的“是”(存在)在他那里总是具有时间中的“存在”维度。康德曾从纯粹形式逻辑的“分析”立场出发,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解称作一种“疏忽”,如亚氏对“矛盾律”的表述:“某物同时是而又不是,这是不可能的”,康德认为,这一公式“是完全和矛盾原理的意图相违的”,因为真正的分析命题是“不需要附加上‘同时’这个条件”的,只消从主词概念中直接分析出它所包含的宾词就行了。!其实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疏忽”恰好包含着形式逻辑本身的源头,即逻辑与本体论、认识论的统一体。在亚氏那里,当 on 被理解为“作为‘是’的‘是’”即个别实体时,它就体现为时间中的能动的“此在”,只是后来随着逻辑学和本体论逐渐互相脱离(当然,这种脱离也是逻辑学本身的发展所需要的),逻辑的这种本源的能动性就被遮蔽了,直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才重新揭示出来。可见,海德格尔把“对存在的遗忘”归之于亚里士多德是有些不公平的,亚氏只是没有明确意识到“此在”对逻辑和本体论的生成作用而已,但他也没有把这种作用从他的逻辑学中排除出去。"
整个西方哲学史表明,即使在亚里士多德以后,西方哲学中对“是” 的理解仍然包含有本体论的理解,因为逻各斯、语言仍然被当作世界的本体、最高的存在。例如在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就是凭借他的“ 话”(word)而创造出了整个世界,但上帝是谁?“我是我所是。”(I am who I am.)所以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大量讨论的正是存在、“是”的含义问题。《圣经》虽然也是一种权威话语,但注经者、教父和经院哲学家们努力要把其中的话语从逻辑上理顺,使其合乎理性,以配得上“神圣的逻各斯”。在基督教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始终贯穿着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真理论”,反对迷信、盲信和宗教狂热,排除神秘主义。当然,实际的群众信仰又是另一回事,迷信和狂热曾一度支配了绝大部分信徒;但如果把基督教的历史看作一个逐渐“教化”民众的过程,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基督教使野蛮的西方人逐渐意识到了每个自由的个人对普遍语言的责任,意识到MvGLvsYH只有凭借说出来的话,个人才能够真正“是”起来,才现实地“存在”。个人的灵魂作为“圣灵”就是普遍的“道”、逻各斯,当他还没有理解普遍的逻各斯的时候,他的存在就等于虚无。逻各斯就是理性,就是“自然之光”或上帝的启示,所以灵魂的本性就在于要尽全力去追求那神圣的逻各斯。这里面已经隐含着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原则的种子了。
近代欧洲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把中世纪已经上交给上帝的逻各斯发还给了人的认识主体,要么用来把人提升到上帝的位置,以上帝的名义或代表上帝管理下面的世俗世界(唯理论);要么用来为人谋现实的利益(经验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存在”与上帝的“存在”在“存在论”(本体论)上具有同样的、平起平坐的意义,而在认识论上甚至比上帝的存在更为根本,它实际上就是“我思”这一行动。洛克试图通过“观念原由网与观念的符合”、即通过对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清理来把握三种实体(物质、灵魂、上帝)的“名义本质”,已经沿着唯名论的方向把逻各斯工具化、符号化了,导致了西方 being 一词的逻辑含义(“是”)和本体含义(“存在”)的分裂。这种情况在康德的“现象”和“物自体”的对立中达到了极致。在现象界,康德的“先验逻辑”占绝对支配地位,甚至“人为自然界立法”,但在这里,作为逻辑系词的“是”是决不能与作为世界本体的“存在” 混淆起来的;而在本体界,我可以把这个本体称之为“存在”,但这个存在不可认识,因而无法运用先验逻辑(这种运用是非法的)。不过,康德为这个不可认识的本体领域仍然保存了某种“理性”作用的可能性,这就是他所谓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也是理性,因为它表现为对逻辑的不矛盾律、同一律在行动上的遵守,表现为自由意志的前后一贯性,即“自律”,同时也表现为对知性范畴在实践意义上(而非认识意义上)的作为“ 悬设”(Postulat)的运用。这就为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 Sein(即 Being)合而为一暗示了一条出路。例如黑格尔就指出,“存在”实际上就是客观的思维,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最初阶段,同时又是一种自行存在起来、形成(werden)起来的“决心”和冲动。所以按照黑格尔辩证法,认识就是实践,不实践(行动)就不认识, 不认识也就不可能行动。认识和实践都依赖于一身兼为逻辑系词和实在动词的 Sein。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讨论的绝不只是逻辑问题,而是无所不包地容纳了整个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问题(“本体论”问题),最后归结为客观的“概念”。德国古典哲学对 Sein 一词的这种深度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他们对这个词的解释虽有相当大的不同,但他们对该词的语感却是以西方哲学史的长期发展和积淀作为前提的,不是对西方哲学史没有深厚根柢的中国学者所能够妄加臆测的。
总之,对于西方哲学中的 Being 一词,我们直接就翻译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有”或“存在”固然有失偏颇,但径直就译作“是”也还有另一方面的麻烦。前者的确是忽视了西方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但后者则同样忽视了这个词翻译过来之后在中国文化中的语境。所以我主张不必对这个词做单一的定译,而是根据不同的场合译出它的各种含义,同时在注释中说明其他的含义。这样看起来似乎增添了麻烦,但实际上可能更能切中原文的意思。当然,在当代中国,经过一段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特别是进入一个法制社会以后,中国人也许会慢慢习惯于尊重语言文字的独立性和神圣性,甚至语言本身也会发生某种结构性的变化(例如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口语中已开始使用“ 有”作为过去完成时的时态助动词,如说“我有到过旧金山”,“ 我有收到你的来信”, 这可能是受英语语法的影响),那时翻译上的这种问题也许就会自动消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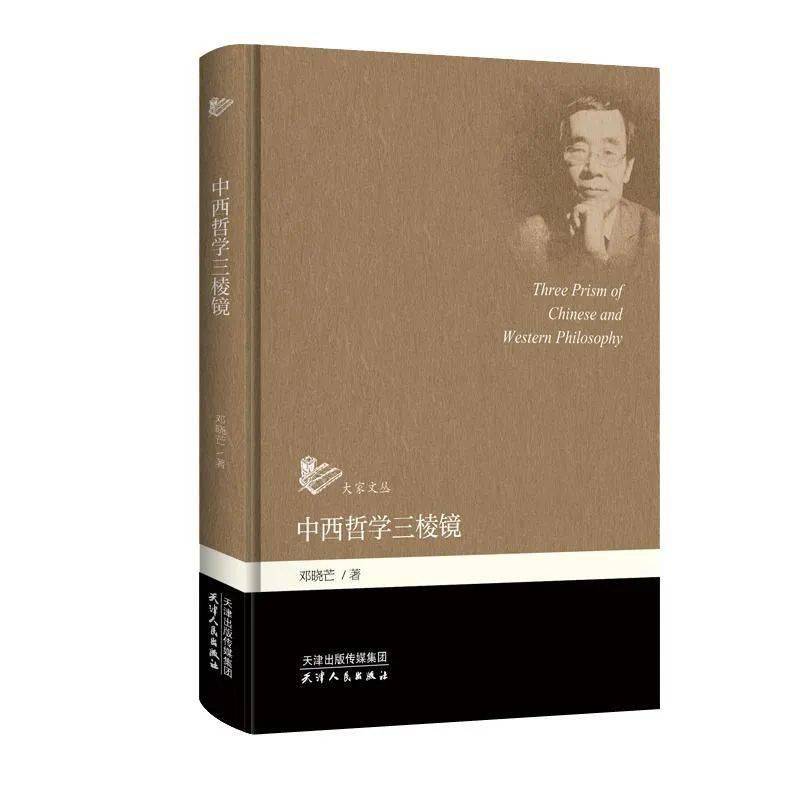
邓晓芒教授最新学术力作 《中西哲学三棱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