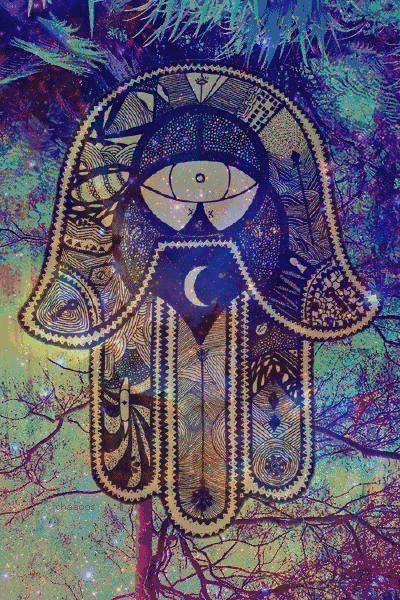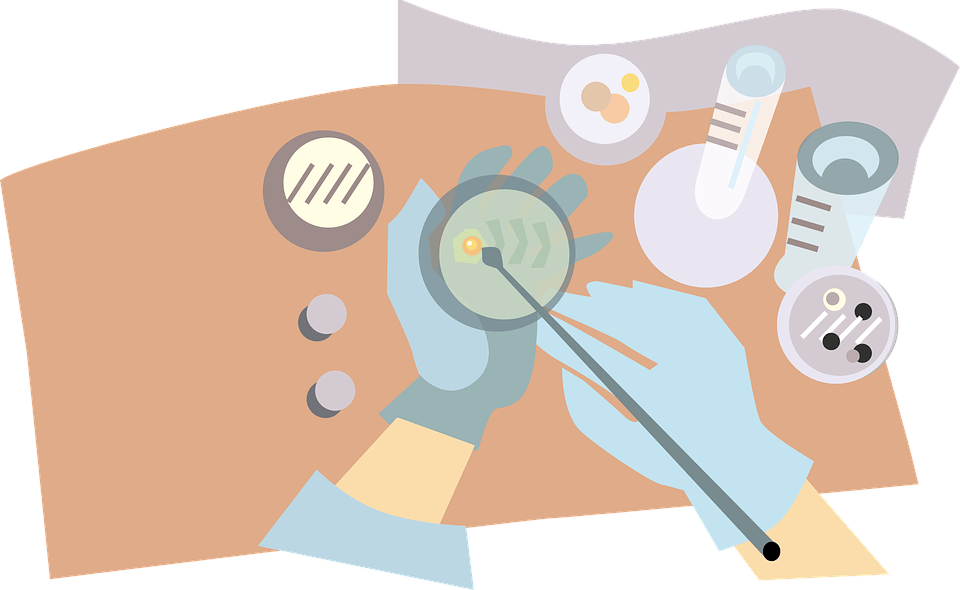今日推送《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八)》录自《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陈永玲》一书,作者南奇(1937-2013),著名京剧票友、京剧艺术评论家,南铁生先生之子,曾参与筹建「北京梅兰芳艺术研究会」,兼任副会长。南先生此书以写实的手法分别细数了王吟秋先生和陈永玲先生毕生学戏、唱戏的心路历程,以及二人在时代巨变和意识形态剧烈冲突下如何面对横逆羞辱,竭尽全力度过艰困,保存师门真传与戏曲精髓的真挚精神。本公众号将在每周六分期进行连载,敬请关注。
还将梦去
吟秋从北京京剧院退休之后,晚年独自居住在北京海淀区北三环双榆树南里二区一幢普通居民楼中。七十多岁的他,依然身体硬朗,可以自行安排有规律的起居生活。他开始回顾自己从艺之后的生涯,他有感于有知遇之恩的王瑶卿、王幼卿、程砚秋和马连良诸位,这些回忆,也使他心中时时激起层层的微澜。
记得那是一九四八年春节,清华大学举行春节团拜联欢晚会。王吟秋应邀陪经济学家刘大中先生演出《打渔杀家》和《奇双会》[写状] 一折,刘大中先生于老生戏、小生戏无一不精,校方还特别邀请程砚秋先生登台清唱。
二月十四日下午,程师、师母带着王吟秋来到了清华大学吴景超教授府上。车一到吴府,吴氏夫妇、刘大中夫妇已在门口恭候程师三人,下车后,大家在吴府门前合影留念。傍晚,吴景超夫妇设宴招待,刘大中伉俪坐陪。饭毕,刘大中先生和王吟秋即去礼堂化妆,程师、师母则在吴府吃茶说谈。程砚秋早向刘大中说道:「我这个徒弟没念过多少书,您在台上多指点指点。」
晚上七点多,联谊会开始。梅贻琦校长、朱自清先生、吴景超夫妇、刘大中夫人、程师、师母与众位校内师生观看演出。当刘大中先生上场后唱「父女打渔在河下,家贫哪怕人笑咱,桂英儿掌舵父把网撒……」,一个拖腔,赢得了满堂的掌声。稍作休息,接演《奇双会》[写状]一折,刘大中上场后一句[引子]念得清脆响亮,又博得掌声无数。刘大中扮相儒雅,表情动作出于自然,充满书卷气,程师盛赞刘大中是很难得的「多才多艺」。
唱完,台下闻听得程砚秋先生来唱《锁麟囊》,早沸腾开了。程师身穿青布长衫,清唱《锁麟囊》一段[二六]「春秋亭外风雨暴……」台下掌声雷动,久久不停;还要程师加唱,复又加唱两段,每段唱完,掌声不断。这也是程砚秋先生多年来破例唯一的一次不化妆穿便服登台清唱。

程砚秋之《锁麟囊》剧照
当晚,台下观剧的朱自清先生,随即赋诗两首,分赠程砚秋、王吟秋师徒二人。诗题为《赠程砚秋君及高徒王吟秋君》,首赞程师:韩娥歌哭入云深,老幼悲欢不自禁,今夕琳琅闻一曲,千人忘味各沉吟。复赞吟秋:盛年头角已峥嵘,雏凤清声满座倾,不负苦心传妙绪,程门此子最能鸣。
程师的观众群多为知识分子,与书家交往多了,王吟秋对念书上大学充满了憧景,然而,他自己哪敢有进清华园上学的奢望呢!
已是暮年的他,毅然掏出自己菲薄的退休金的一大部分,无偿地捐献给家境贫苦的大学生。十年之间,竟也捐出了好几万,而自己依旧省吃俭用,只订阅了多份报刊来了解世间动态。他回想,自从一九四五年进入程师家,到一九五八年程师去世,这一十三年之中,不曾见过师父添置过什么新家具。唯有一次,一九四七年,秋草渐黄的时节,一个清风飒爽的午后,师父带着吟秋去逛天桥,在天桥一家旧货店里,无意间相中了一面约一米五高的红木大镜子,便买回家中放在堂屋内,师父每天对着镜子练身段。一九八五年,师父已经走了多年,还听得师母凄凄长叹道:「你师父,累了这一辈子,没有享什么福就走了!」想起这话,王吟秋没有一次不硬咽难鸣。
与程师朝夕相处的六年,程师生活上的俭朴风度,点点滴滴,恰如镌刻在王吟秋的心坎上一般。
程师家,中午惯吃面食,晚上吃点炒菜。中午面食花样倒也不少,面条、烙饼、馒头、饺子、还有小米面窝头一应俱全。仅面条花样就有几种,打卤面、炸酱面、羊肉烩汆面、猪肉丁黄花木耳汆面。王吟秋是江南人,哪里能习惯那羊肉的膻味,最怕吃的就是羊肉烩汆面。炒菜则再也普通不过,有时炒个葱爆羊肉,一般做点蔬菜,切碟儿咸菜,熬点粥就窝头或贴饼子吃。
程师家有三位帮佣,雷三元、赵升和女佣辛妈。程师演出时,雷三元帮穿戏衣,赵升在一旁沏茶倒水打点些杂事。平日里雷三元、赵升就住在程家,雷三元管做面食,赵升买菜做饭,辛妈管打扫、卫生、浆洗诸事。
雷三元能抻出很细的面丝儿,赵升善做羊肚汤,拌上芝麻酱、撒些香菜,惹得吟秋之后也不拒羊膻味了。程师最爱吃这羊肚汤,每次先就一大碗下肚。赵升看程先生吃得有味,就附和说:「四爷,您再来一碗?」程师毫不犹豫:「好,再来一碗。」赵升接过碗,去厨房再盛上端来,程砚秋先生便轻拍一下肚子,笑说道:「我的肚子是橡皮做的。」师母听了哈哈大笑,永源、永江、慧贞三兄妹和吟秋也都掩不住仰笑。
程师虽简朴,但倘若是青龙桥附近有农民家里揭不开锅,来求助于他,他总客客气气地打发些钱米给他们。所以青龙桥附近没人不知「四大名旦」,更无人不知「四大名旦」中的程大老板是个大善人。
对希望工程、救助贫困地区、灾区的捐款捐物活动,总能见王吟秋的身影儿。逢年过节,居委会组织慰问附近的武警、部队,王吟秋一准也要拿出许多东西,要不就出钱让居委会的同志帮着采购些东西送去。
吟秋陪师父一起逛大栅栏,吟秋看见一件大衣,觉得款式不错,便悄悄多瞄了几眼;却早已被一旁的师父察觉到,出父问他:「喜欢吗?」王吟秋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随即便忘了此事。不料第二天,那件大衣已挂在了吟秋的床头,师父为他买了回来。王吟秋自忖道:「连师父的亲生儿子也没给买,就给我买了呀!」吟秋脑海中一时间回闪起这段记忆,幸福洋溢之余反又平添了天人永隔空悲凉的意味。
程师走得太早,在吟秋看来,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程师的艺术创作能力,在那时已登峰造极,游刃有余。倘若程师不走,京剧艺术宝库中又当增添多少珍品呢?然而,程师最后那几年,已倍感暴风雨之来袭,不走,他又能争取到多少艺术独创的空间呢?
谈到那时被迫跑龙套的经历,王吟秋后来曾对我笑说道:「唱不情愿的角色,何尝只是我。以前在宁夏京剧团时,鸣盛演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中的农民武装起义者乌豆,那么一个优秀的杨派老生演员,演一个草莽英雄,唱老生不老生、花睑不花脸的角色,人家问他唱的那是什么派,他自个儿说‘我是马列派’。鸣盛病卧在床上之后,我去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死活不放,我们一直是难兄难弟!」
王吟秋居住的双榆树南里二区比较幽静,外来人口并不多,治安一向抓得也紧。但王吟秋住的二号楼却紧挨小区东院墙,院墙和楼房之间又搭建些平房,平房不足两米高,房顶离二楼王吟秋家的窗台不过一米之距。院墙之外是一片旷地,则聚居了许多外来人员。居委会曾经劝王吟秋先生将窗户和阳台装上防盗网,但王吟秋只是笑说:「家里也没什么值钱东西,装防盗网没必要。」恰因这程大意,才酿成了日后的祸端。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午后,独居家中的王吟秋遭一个外来人员入室砍死。杀人者不过为寻些邪财,此人正是翻过院墙踏过平房从阳台进入的。因王吟秋的女儿远在日本,警方一周之后方启出现场。一个月之后,凶手在原籍被捕。
王吟秋死后,警察也向王吟秋生前的同事走访调查情况,看死者生前是否有什么仇家。当问到温如华时,温如华想了一回,说道:「说起来,有个叫李世济的和他仇恨最大。」警察一边记下这条重要线索,一边问李世济是干什么的,温如华如实答道:「中国京剧院退休演员。」警察忙持着卷宗到中国京剧院调查李世济为何许人也?被问及之人莫不忍俊不住,拊掌大笑。
在京剧各流派之中,程派的魅力弥久不衰,私淑者众多。只是程砚秋先生一生不愿收女弟子,女性由于气血方面的原因会导致发声位置游移不定,很多女演员一生都在调整发声位置,这是原因之一。
程砚秋大约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之后,程派弟子和私淑程派者的分歧会如此之大,分化为两个阵营,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守望与革新,针锋相对。守望程派者,有王吟秋、赵荣琛、李丹林等座前弟子;恣意革新程派者,主要是李世济与其众门生。
一九八三年,为纪念程砚秋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为正名分,台下勾心斗角之戏先已上演。
李世济一直要拜程砚秋先生为师,程先生只收她做了干闺女。李世济的唱腔、身段历来激情澎湃,程先生并无收之为徒的意思,李世济走上层路线,即使在周恩来总理的询问下,程砚秋先生也一直婉拒。
这次纪念演出,李世济想一手把持,尤其对于新艳秋,李世济坚决要将之逐出去。
新艳秋,应当是第一位程派艺术追随者。为了学习程派艺术,什么偷「梁」换「柱」的法子也都使过。她是程派艺术的忠实拥戴者,也是坤伶中程派第一人,可惜没有文化,对人物内涵的理解流于肤表。她因曾投奔川岛芳子,陷于这些历史重诟,解放之后极不如意。
赵荣琛先生对于李世济的做法颇为义愤,他用「君王驾崩,贼子乱朝」来比喻此等局面。他劝解李世济以和气为上,李世济大吵大闹,赵荣琛先生招架不住,只得向师母程夫人果素瑛女士倾诉。
程夫人慨然出面,对李世济说道:「你也别吵吵,成何体统?我还没死呢,这件事我说了算。新艳秋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你干爹都原谅她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必把人都往死里逼。我告诉你,这次演出,新艳秋要参加,他们都要参加纪念。如果你不愿意和他们同台,你可以走。」李世济被帅印一压,也就偃旗息鼓。
于是新艳秋、王吟秋、赵荣琛、李蔷华、李世济五人合演《锁麟囊》。李蔷华演出[选妆奁]一场,李世济演出[春秋亭避雨]一场,赵荣琛演出[归宁遇水]一场,王吟秋演出[花园]、[三让椅]两折,新艳秋演出[团圆]终场。这其中,王吟秋在戏里的沉稳,无人能过之;李世济在台上的挥洒,亦无人能过之。

姚慕楚、王吟秋、果素瑛、林天池、钟世章在1983年纪念程砚秋//www.58yuanyou.com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活动中留影
一九八六年,程夫人也离开了人世。去世之后,李世济逢人便说:「她死之前,作揖冲我拜了一拜!」一个缠绵病榻之人,弥留睡卧中不过善意地双掌合十而已,原本是对送别之人礼貌的告别,倘若非强说这里面有什么深意,大约也就是:大局为重,以和为贵!果素瑛女士严以持家、爱憎分明的作风是众所周知的。
王吟秋曾戏谑道:「我们这些程派门人,瘦的瘦,胖的胖,老的老,丑的丑,还是免不了争斗,乱乱哄哄的!」
李世济从一九七八年调入「中国京剧院」之后,就大力修改程门本戏。《英台抗婚》、《文姬归汉》、《碧玉簪》、《梅妃》无一幸免。
单以《文姬归汉》为例。故事的背景是:东汉末年,董卓死后,军阀混战,南匈奴乘机掠掳中原,纵猎围城,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文姬与许多妇女,被北掠朔漠,年仅二十三岁,忍辱嫁与左贤王,生二子;十二年之后,建安十三年,曹操感念旧友蔡邕之才,知其唯有一女文姬流落番邦,遂派人携黄金干两、白壁一双将之赎回。也就是这一年,爆发了「赤壁之战」。
程派的《文姬归汉》以史为据,以家国离乱为场景,以蔡文姬流落异邦对中原大地的思念为主调,「伤心竟把胡人嫁,忍耻偷生计已差。月明孤影毡庐下,何处云飞是妾家?」是也!文姬归汉,经过大黑河南岸的昭君墓前,赋诗自比昭君。这两个相去两百多年的女性,运数大不相同,昭君是汉元帝和番的牺牲品,和亲之后,边塞狼烟熄灭五十年,她终落得死葬朔北,能归故里。文姬哭昭君,是对汉武帝之后软弱无能的政府以女性作为交易条件以求安定的痛斥,叹其「可怜你留青塚独向黄昏」,也是对照自己哭诉战乱之苦。
李世济改编版的《文姬归汉》,与郭抹若一九五九年写就的《蔡文姬》一脉相承。
一九二八年,因受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郭抹若流亡东瀛十载,一九三七年偷偷别妇弃雏返国,人生逐步得意。郭沫若曾对曹禺说道:「我就是蔡文姬,我要为曹操翻案。」的确,在一九五九年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运动日益频繁,郭沫若颇识时务,以他的才情,在《蔡文姬》中高歌了曹操统治下的太平盛世、安康人和,蔡文姬「我生不辰逢离乱」之恨被无端弱化了。明眼之人,定能体味到郭老夫子创作时的心绪。
李世济改编版的《文姬归汉》,其基调是民族大团结,因此最末一场增加左贤王追上文姬送还儿女一幕。如此改编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却将民族大团结的情绪推到了极致,让历史再度扭曲,「深悔恨误把恩爱当恶辱,难宽宥错认壮志为骄狂」,将十二载的忧思翻做了无限的自责,「深深拜,深深拜」,倘若情真如此,何须归汉?
待看过此等演绎的《文姬归汉》,王吟秋怒道:「从头到底就没有一点是对的!师父的唱,以气托声,以音包着字眼儿,字字如珠玑,师父最讲究字韵四声。她可好,自编自唱的「送儿女」三个字,一开口就是上海口音,都成了「松耳语」了,不守程派戏的根本,为后人留下一笔糊涂帐,真是罪过!」
《文姬归汉》、《红拂传》和《梅妃》,皆为程砚秋早期剧目,演出之累,尤以《文姬归汉》为最。《文姬归汉》,唱做并重,程砚秋弗过一年一演,作为年终封箱之戏。每演《文姬归汉》,票价倍增。程砚秋早年曾随武术名家高紫云习太极拳,一生不辍,他将太极拳中用劲运气的原则融化到京剧的台步、身段中,圆润和谐。程砚秋曾说过:「我个子太高,通过练太极拳来调整自己的身形和步伐,沉肩坠肘、源动腰脊、劲贯四梢,可以藏拙。」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家父曾托林秋雯先生的徒弟李紫楣带我去看程砚秋先生在「新新戏院」演出《文姬归汉》,以祝贺程先生重登舞台。临近后台,见林秋雯叔叔早已站在台口迎接,牵过我的手说,「小琪,你来,我带你去看程先生。」我们一同进去,在角儿独立的化妆间里,程先生正在上妆。林叔叔将我扶在胸前,对程先生说:「四爷,南大爷派他的小少爷来祝贺您重登舞台了。」程先生含笑转过头来,柔声道:「来啦!」我还没来得及行礼,程先生已扭过头去,对旁边站着的管事儿轻声吩咐道:「客座!」我被领到第三排中间位置坐下,两旁都是些衣冠楚楚的绅士派头人物,我乖乖地不敢任意四顾,心想:这是我有生以来看戏的最高礼遇啦!管事儿的低声说:「南少爷,回头儿完了戏,您别动,还让接您的人送您回去。」「新新戏院」位于六部口,我家在新平路,相隔不过数百米的步程。
圆弧形的台口,高高地垂落下来猩红色缎子的大幕,上面绣满了五彩的花鸟,在剧场稍显噪杂的氛围中,却仿佛置身于鸟语花香的密林,我开始细数起那林中飞鸟的只数,好似无有穷尽。
随着幕布徐徐分启,程先生一袭黑帔出场,黯淡的光线一点点炫亮起来,寡居中的蔡文姬,高贵端庄,眉宇间愁绪萦绕……
在接下来的[逃难]一场,林秋雯叔叔扮演的侍琴与程先生一道跑s型的圆场,又快又稳,衣带飘然,却听旁边之人悄悄议论道:「林秋雯的圆场那么好,在程砚秋老板面前,还是有些颠了!」
「整归鞭」归汉途中,一大段优美的唱段,程先生内着改良蟒、外披斗篷、头顶风帽、坠狐尾,风帽、斗篷的边上都附缀着一条条毛茸茸的银鼠尾,在灯光下油亮光润。全剧中,走「马趟子」最为吃功。黄沙漫天,草色低迷,朔风如铁,马啸啸,在人与马、黄沙、朔风的逆抗中,归途艰涩。程先生身体忽而前倾、忽而仰面勒马;先生的马鞭、水袖就犹如长在他手腕上一般,在太极的劲道带动下,银鼠尾无不舞动起来;真如塞外健马,气度非凡。在《昭君出塞》一戏中,尚小云先生也是走「马趟子」。一去一回,跨越了两百年的时空,一条是不归之路,一条是返国之途。文姬哭于青塚之前,似乎想要携昭君的一缕香魂回归故里;那[反二黄]幽怨的倾诉声,也确实深深打动了我这个八岁的孩子。当日后读到「胡笳十八拍」时,眼前横现出的却是昔日程先生在「新新戏院」舞台上的身姿:悲//www.58yuanyou.com凉且悲壮。不免感叹:唱程派戏,没有扎实的功底、没有厚重的文化内涵,怎能体现出程先生所塑造的舞台人物的神韵?
数年后,当我提到会看了程砚秋先生那一场演出时,王吟秋兴奋地抓住我的手说,「我也去看了,我是站在场面后面看的。完了戏,白登云先生还说呢:吟秋呀,你一边儿看,一边儿就直着眼睛往前小碎步地挪,都快欺到我背jyPzJdjEe上了,你要是跑起圆场来,嘿,可不把我们都给撞翻啦!我看得太入神了,我可是怹的超级戏迷,那时候儿我就认准了要拜怹。」

程砚秋之《文姬归汉》
然而,《文姬归汉》经由李世济易手,身段繁难的走「马趟子」改为「行车坐辇」,魅力顿时锐灭。
王吟秋说:「塞外漠北,南面横贯着大漠戈壁,她还敢以车代马,也不怕陷在黄沙里面去?文姬坐着车辇,再花十二年恐怕也归不了汉。师父在台上,舞动的马鞭伴随着他的身姿,能让观众体会到在无垠的沙漠中孤绝奔越的艰辛,一人演满全台。现在的舞台上,蔡文姬在众多龙套簇拥下显贵地乘辇而归,无点滴精彩可言。功力不到就糟改,用人海战术代替个人艺术。师父严守太极,太极遵循的是守静而不妄动,她是‘太急’!」
赵荣琛也曾戏道:「她那水袖哪儿叫水袖呀,也就俩面口袋。」
王吟秋说:「怎么样胡诌都算改革创新!反正啊,再怎么糟改艺术,警察也不会来抓她。」
口齿之辩,乃是源于徒弟对师父十万分的虔诚。为了对得起师父在天之灵,不忍看到师父遗世的精品被篡改,不免耿直批判。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趁着京剧观众群体尚未大量流失,出版部门想召集梅葆玖、杨荣环、王吟秋与宋长荣合作一次全部《四五花洞》,以完成一桩「四大名旦」传人重现辉煌的夙愿。终因资金不足未尝实现,王吟秋颇感惋惜,他对我诉说:「其实,为了能给后人留下些可以借鉴的资料,我们这些老艺人是不会计较出场费的,怎么就半途而废了呢?!」逆流行之,道阻且长,正是京剧艺人多年来的真切感受。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以田汉、马彦祥等为首的「戏改局」在改戏、改制、改人的进程中,步步彻底浇灭了艺人们期盼的热情。传统戏曲被迫接受西方话剧的洗礼,在这场洗礼的仪式上,正面冲突时时触发。如「四大名旦」这样成熟的老艺人,只是采取心中有「戏」、对尔等「敬而远之」的战略。他们固守传统戏曲的创作原则,以所见、所知、所感为素材,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过百出老戏的唱念做舞为基础,信手拈来俱是戏。梅兰芳此生最后一出新戏是《穆桂英挂帅》,首演于一九五九年,该戏移植于豫剧。几乎同时,尚小云先生在西安与林金培先生编写了他最后一出新戏《双阳公主》,此戏借鉴于王瑶卿先生《珍珠烈火旗》和《反延安》两出剧本。荀慧生一九五九年的新戏《金玉奴》是对老戏《红鸾喜》的重新梳理。程砚秋先生创编出《英台抗婚》,多少有些与马彦祥改编导演的《柳荫记》打对台的意思;这内中有两层缘故:一是,他不想用改革派的大作,二是,王瑶卿先生为《柳荫记》设计了唱腔,沿用了传统的[二黄]悲情路线,程砚秋先生有自己的想法,他要用激越的[西皮]板式演绎这个反叛意识异常浓烈的祝英台。取名《英台抗婚》,这其中的「抗」字,则直接抒发了性子刚烈的程先生对戏的愤懑。深谙时局的陈叔通老先生,闻此剧名,吃惊至极,连忙找程的好友胡天石去劝说程,这属于「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希望程先生莫逾雷池。岂料胡天石的想法与程砚秋如出一辙,「封建家长包办婚姻是不合法的,用「抗」字恰当,能突出女主人公的性格,并无不妥。」「四大名旦」以艺人的良心,抵制着传统京戏与西方话剧这桩畸形的婚姻。
在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中,比较有成效的是「中国京剧院」的编剧翁偶虹、范钧宏、马少波等诸位,这几位先生不仅仅会演唱京戏,且很地道。他们是有相当国学造诣的文化人,他们也了解广大观众的审美追求,他们的作品也能充分发挥京剧演员的专长和个性特点。
剧作家田汉和导演郑亦秋合作的《白蛇传》,也必须要仰仗王瑶卿先生来安排唱腔,也必须由名角儿来演出,才使得剧本有存世价值。即便如此,《白蛇传》在艺术上也无法超越《金山寺断桥祭塔》。老艺人与新派编剧对新时期下的戏曲创作各有心得,在泛政治化的巨网面前,前者有能力创排却不能获得太多机遇,后者随心所欲却力有不逮;二者心照不宣,各有各的痛苦。然而在人格上得不到尊重的情形下,老艺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妥协,用传统手法和话剧手法新编剧目的共生现象,表现了当时的戏改稍许温和的一面,那时艺人的脊梁尚未折断。
政治环境进一步严峻,戏改之势扫荡全国各大剧种,漫厉呼啸。「四大名旦」后一辈的演员,焉能有老艺术家那样抗争的本钱?因此上,就如张君秋、杜近芳也只能在田汉面前唯唯地恳切道:「田老,您写吧,您怎么写,甭管句子有多长,甭管押不押韵,我们都能唱!」为了争取演出的机会,本子通常是这样淘换来的。口语化的话剧台词、字数参差不顾句读、既不洗练、也难合辙上口。如欧阳予倩先生的京剧剧本《桃花扇》,剧中李香君的几段独唱,除却杜近芳这样优秀的演员,旁人恐难胜任,真可谓「高处不胜寒」,学者寥寥,更谈不上推广与吸引群众琅琅上口地吟咏传唱了。即使买票去看戏的观众,亦是冲着主演而决非冲着剧作者而去,这是艺术鉴赏的惯性思维。哪一个演员不希望在艺术中争取独创的自由?但是这种畅怀的自由在政体的约束下是不存在的。纵使那有限的演出自由,也是配给式的,就如杨荣环、梁小鸾这些优秀的演员,甚至都没有演出的机会,唯有愀然独立。没有名角儿的维系,戏曲必亡,没有戏曲的传承,就没有名角儿诞生的本源,在思想意识上认为「话剧加唱」可以替代传统戏曲的传承,则从骨子里加速了戏曲的死亡。

杜近芳之《桃花扇》
在江青众人的眼中,作为国剧的京剧艺术俨然可以被利用为政治呐喊的工具,随后,传统艺术被鞭笞倒悬。「革命样板戏」披上了伟岸的道袍,八亿人民耳际反反复复地充斥着八出样板戏,这出轰轰烈烈的闹剧持续原由网了十年之久。京剧团逐个萧条,演出场次锐减。以江青原籍山东为例,文革之前京剧团有三百余个,文革中纷纷遽散。在这层道袍终遭撕裂之后,传统艺术已破碎殆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文革「造反有理」的思潮,仍一直在挤压着传统京剧的生存空间。表面看来,新时代的京戏艺人在舞台上塑造出先进的工农兵形象,好似扩展了京剧表现手法;实则,艺人为了争取到演出的权利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舞台演出多半是违心的迎合,任由导演的指派,完全背离了戏曲的创作规律。以演员为中心的戏曲艺术被彻底颠覆,演员边缘化,导演中心化,舞台上演出的哪里还是京戏,不过是一出出历史傀儡戏。
几十年来,始终未曾改变的是,艺人从未获得过自由的话语权;在风高浪急的政治运动中没有获得,在天下承平的「盛世」中也不可能获取。国营剧院中,唱戏的是艺人,决定艺人境遇的却是剧院的领导。领导不见得懂戏,甚至沿袭了抵制传统的一贯作风。领导要政绩,自然就得力推新编戏,有无艺术内涵不是第一要则,重要的是能从中勾取功名利禄。三十年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并未扣响京剧的门环。顺之者昌,此言中的。对于那些「抱残守阙」不肯依附的老朽们,就让他们清高去吧!摆在青年演员面前的,有名利与艺术两条路,不可兼取。名利之路唾手可得,艺术之路荆棘遍布,有谁会选择后者呢?在名利的诱惑下,青年演员悉投名师,而非明师,选择前者虽无可厚非,然而却加速了京剧的急剧陨落,直至跌入死亡之谷,不可逆转。
艺人的脊梁在血色的烈焰中被融化了。
李世济顺应时局的变通,是其生存之道。毛泽东曾问李世济:唱程派戏有多少年?李世济铿锵地回答道:「我要做革命派,不要流派!」嗜好传统京戏的毛泽东很是惊讶,严肃地告诉她:「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
李世济一步步爬上了程砚秋先生当年也不曾企及的政治高位。她完全可以在剧本、声腔、身段上保留住程砚秋先生的程派原貌,毕竟,她看过那么多程砚秋先生的明场演出。她的丈夫唐在炘,作为一位程派琴师,对程派戏的了解又岂是等闲。然而,他们对程派戏大幅修斫,这其中融入了他们的艺术见解、他们的历史观、世界观,甚至可以用当代的情绪穿越千百年的尘雾去改写历史。在个别戏的个别情节上,他们的确也有进取之处,比如对《梅妃》最后唐明皇梦梅妃的一场剧情的改编。然而,纵观起来,的确不敢恭维,尤其在艺术修为上,她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李世济所谓的「新程派」,占领了京剧程派艺术专业领域的大半壁江山;而王吟秋、赵荣琛、李丹林几位,谨惯经营,一攻一守,攻守之势立判。
从一九五八年程砚秋先生仙去,年年三月九日,只要王吟秋在北京,顶风、冒雨、裹雪,他准一大早去八宝山公墓为恩师扫墓。他说:「每逢师父忌日,头一宿都睡不好。去墓地看师父就似赶赴一个最重要的约会,师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好象还活着一般。第二天醒得很早,倒不是想抢着第一个去给师父扫墓,只是怕堵车,走的早反倒顺畅。」王吟秋独自手捧鲜花,带上专门为程师扫墓的小笤帚,去至墓前。正是春色渐起的光景,草展花伸,墓园中,因清明,上墓人稀少,显得如许清穆。王吟秋静静地先打扫师父墓上的落尘,再回首清扫斜对面师母之墓,随后向两位老人家献花鞠躬,就痴站在师父墓前,合上双眼默哀;千思万绪,一任往事从心尖上唏嘘淌过。
王吟秋是程派最忠实的信徒,他恪守师训,不逾半步,在他的身上,你能不经意间就捕捉到程砚秋的影子。程师已去,他回想起那些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人,匆匆然皆成了亡灵。他的半个生命都沉浸在了对往事的追忆里,除去这种精神上凭空的慰藉,剩下的就是一条逐渐老去的孤独的身躯。
王吟秋在心头为自己悬上了一副「挽救程派」的重担,以程师的光芒尚且无力穿越历史的阴云,四十年过去了,格局又改变了多少?王吟秋被搁在了死局当中必输一方的位置上,自强、冥想、挣扎、遍觅奇才皆不能逆抗败局。愈是冥想、愈是挣扎,痛苦弥增。他自然也能卸去负担、散淡若闲云。但是,他分明能感受到程师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在冷清的居室中,孤灯照彻长夜,投影出他瘦弱的身影;他分明与程师促膝而谈,谈经年往事、谈别后之际遇。的确,他的耳际满是使命的召唤,就是要将对程派的所知、所解传达给下一代。但在自说自话式的讲授中,倏忽间睁开眼来,才发觉四座皆空;空旷如置巨野,夜风来袭,举目唯有一派惆怅相伴。倾耳听来,隔壁车马杂遝,竟是一片觥筹交错的喧闹,醉话连篇、胡话连篇、错话连篇,不忍稍闻!故顿足痛惜程门大义惨遭曲解。
一墙之隔,实相去霄壤。
与赵荣琛大哥一样,王吟秋这些程派弟子耿介不群,选择了抱艺绝尘的孤高姿态。其实,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寂寞的宿命!
二千年的一个傍晚,我约同一位记者去北京大学看学生京昆社团的演出。我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正细心观剧,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我右侧移动了过去,我偏首一看,原来是王吟秋大哥,他也来了。吟秋大哥也同时发现了我,于是轻步移身过来,我们俩会心地笑了一下,未交半语,继续看戏。台上正演出《贺后骂殿》,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告诉他,饰演贺后唱程派的是博士生,演赵匡义的是硕士生,他听后十分高兴,说道:「没有文化内涵是唱不好京戏的,青年学生回归传统文化,他们是传统艺术生存的根基。学生们演得可真好,真没想到。」我顺口说道:「等完了戏,咱们给他们道个辛苦吧!」
待戏唱完,我引领他来到小礼堂右侧一间教室,学生们在此处卸妆。我将同学们一一介绍给了王吟秋大哥,也许是出于腼腆、又或许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位清瘦的老者在传统京戏艺术中的份量,学生们对他的到来反映平常之极,更无人提出向他学艺。
我陪同他一起走出校门时,他说:「专业的演员已很少来找我学戏,我没有名利的号召,有次在天津,参加传统戏音配像的会议,李瑞环同志指定说要为我配学生的,空等了半年,也没人来找我,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我喟叹他的执着。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扶送他上去,抱歉道:「王大哥,不送了,我还要送小吴记者。」他含笑俯身上车、关上车门、挥手而去,我一直目送着街头的灯火淹没了缓缓离去的车影。孰料此去之后,不过一年,就传来了惊人的噩讯!这一年之间,虽时有会面,但那晚从校园出来的路上,他无限的落寞,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作者南奇先生与王吟秋先生之合影
在朝夕万变的政治风潮中,体会了程师病榻前的无奈,目睹了马连良先生//www.58yuanyou.com的最后岁月,他开始谨小慎微,言辞闪避,因此陷入落寞。程师的艺术在他看来,足可一览众山小,作为程师跟前受益最多的弟子,他有责任不辱师父门楣,他有一种神圣的高傲,他步履深沉,脊背削直。程师不希望他给人跨刀唱二牌旦角,只是时代又不同了,他再没有这样好的际遇。虽也有些创排,但剧场内外演员观众的心气儿已不复向日光景,因此终其一生并未大红大紫过,因此愈发的落寞。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肆意篡改程师的一个唱腔、一个字句、一个身段、一件行头,然而,但凡演员都希整能突破旧有的樊篱,唱程派戏的人多了,在王吟秋看来,「造魔」的也多了,却又无力收拾这个局面,因此更是落寞。王吟秋看着自己逐渐老去,他自是希望将师父的艺术尽量传承下去,却见认真学戏之人已寥若晨星,又都心绪躁急,发声归韵都成问题,身段手势也不在地方,台上满台一飞,台下观众却也附和着叫好儿,听过这些后辈,再聆听程砚秋的唱片,反说程砚秋唱的不是程派的听众也是有的,王吟秋何等痛心,又有口难辩,转而落寞终老。
对王吟秋先生的艺术品格,正如《中国京剧史》第二千五百二十七页所写道的:「他的表演严谨有法,恪守规矩;身段舞做分寸准确,举止有谱;唱念吞吐考究,行腔刚寓于柔;四功五法头头是道。特别着意于保持程派所独具的风范,准确展现程派艺术特有的意韵。他成为程派艺术的最佳传人之一 。」
而台湾传媒界资深京剧评论家「周郎」则说道:「王吟秋,是程派唯一正宗继承人。」
王吟秋,悄然而来,衔恨而去。京剧的繁盛,他目睹过,也曾经历过。他这一走,带走了太多,留下的遗憾也太多。囿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秉性,他无力与梅、尚、程、荀这样的大艺术家比肩。但「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他能够竭尽全力捍卫优秀的传统文化且独守清操,已堪比此花!
京剧一个时代的重门,似乎也随着这样的老艺人的离弃而缓缓掩上了;再想推启,只怕不能。后人能在浮躁不堪的体制和风气下维系住京剧的生命并保持住京剧艺人该有的尊严,也许就是为重门后的那些先灵献上的最虔诚的一瓣心香吧!
完
(《声远长天:怀念王吟秋、陈永玲》)
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