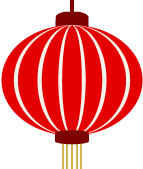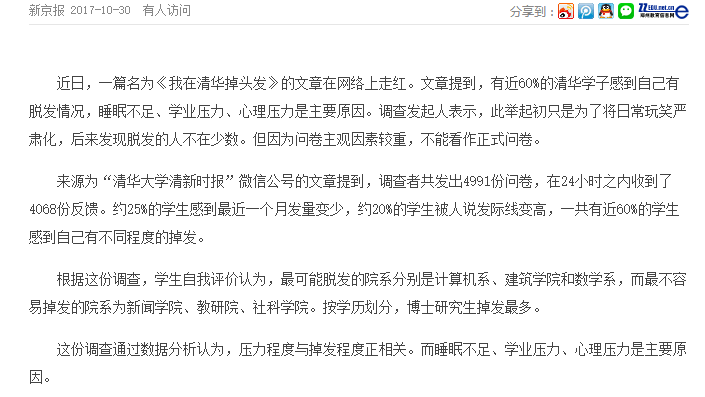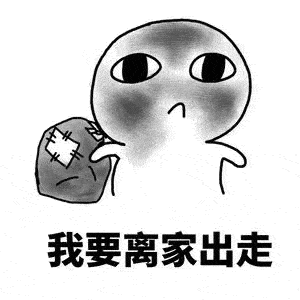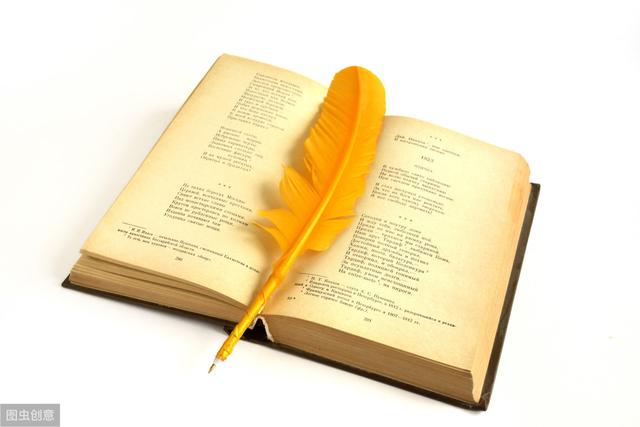
诗歌是一种无限接近于创作者心底最隐秘欲望的文学体裁,所以它才能够用短小的篇幅,精炼的语言中带来深刻的共鸣。有时候诗歌抒发的是所有人都高声吟唱的情感,有时候抒发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情感,有时候抒发所有人都在压抑,都不敢直视的情感。
诗人在写诗时笔端流泻出他的欲望,读者在阅读时感受欲望,无论是欲望的表现还是对欲望的追寻,都免不了一段永恒的距离。费歇尔曾说:“我们只有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到美,距离本身能美化一切。”这里的距离并不是空间时间上的距离,而是心理距离,在诗歌中也就是审美距离。
审美距离因诗歌的欲望而存在,不仅存在于创作者、读者与诗歌之间,更内化在诗歌之中,成为其魅力的一种。中西诗歌的表现、意境、思想都有不同,但在审美距离这一问题上,却又有许多如出一辙的地方。下面将会从“诗歌中的距离”,“上帝视角的创作者”、“读者与诗歌之间的距离”三个方面来分析中西诗歌的审美距离。
一、诗歌中的距离
中西诗歌中时时都能看见距离,尤其是诗人与被歌咏之事之间的距离。宇文所安的《迷楼》中有这样一句话:“这场革命从来不允许获得成功——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就要被迫放弃我们的欲望自由。”诗人因为达不成自己的欲望,所以创造诗歌聊以慰藉,而诗歌正好成为了我们求不得的明证,成为那一段永恒的距离的写实。如果没有距离了,也就无从谈诗了。距离因欲望而保持,同时赋予欲望诱惑的香气。

在中国诗歌里,《蒹葭》很能体现诗歌中的距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伊人是可望不可求的,那追求者用诗句一遍遍的描述伊人的美,同时也描述距离的阻隔。原由网在诗歌中,伊人“在水一方”,保留了追求者与所咏之物之间永恒的距离,所以全诗弥漫着美丽的哀伤。这哀伤不是蒹葭的,不是伊人的,而是因为追求者正望着那段永远不能逾越的距离。这段距离内化在诗歌里,成为这首诗的美的核心。
再来看一首西方诗歌: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之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他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里尔克《秋日》 北岛译
里尔克的这首诗相信会让许多熟读中国诗歌的人感到熟悉,因为“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描写了一个漂泊者内心的孤独。中国有许多羁旅诗歌描写了同样的孤独,诗人也是在路上,或者背离了家乡,或者与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可以与苏轼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对读,场景切换的画面感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形影相吊的背影。他们是一个人,缩成一个小小的点,与家乡存在距离,与理想存在距离,与人的心灵存在距离。这样的距离是在人生路途上的困惑,保持一个孤独的点的状态则是对人生困境的勇敢直视。西方不止有里尔克书写距离,还有马拉美,还有贺拉斯等,中国也不止有一首《蒹葭》,还有李白,还有杜甫,还有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诗人。

距离是一样的,但诗歌中对于距离的态度在中西方却大不相同。西方诗歌书写距离,在欲望即将达成,距离即将消弭的时候戛然而止;而中国的诗歌则多会想方设法的弥补距离。
首先看西方诗原由网歌。贺拉斯的《颂诗》结尾处写道:
“那么来吧
我最后的爱人,
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一个女人
激起我心中的暖流;来吧,学着唱这些歌
以召唤爱情的声音;歌唱能消去
我们黑色的忧伤。”
在本该描写欲望的达成,即得到“最后的爱人”之时,诗人却用歌声代替了追求的结果,然后终结全诗。马拉美直接在《海风》开篇写道:“肉体是忧伤的,可惜”,肉体的忧伤,令人联想到那句“一切生物在性交之后感到悲哀”。
为什么会悲哀呢?因为欲望的达成等于欲望的终结,距离的消弭。燃烧过后就什么都不剩了。所以贺拉斯用歌声代替肉体的遇合,马拉美也在这首诗的结尾写道:“倾听水手的歌谣”,于是诗歌得以保持与欲望的距离,同时又将欲望的目的用华丽的语言包装的闪闪发亮,诱惑人们无限靠近。但我们知道,在美丽的表象下,是空洞无物。没有欲望达成的那一天,这只是诗歌的引诱;肉体也不是甜美的,而是忧伤的。所以当我们无限逼近欲望的时候,诗歌戛然而止,只有歌声在回响。
中国的诗歌又是另一种意境。下面看一首词。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晏几道《鹧鸪天》
这首词的最末两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为人所乐道。这正是对距离的一种弥补。整首词描写对昔日恋人的思念之情,但苦于“碧云天共楚宫遥”,两个相爱的人之间隔着非常遥远的距离。为了弥补这一距离,词人写道自己的梦魂又回到了恋人所在的地方。这样的写法在中国诗歌里很常见,姜夔也有句云:“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杜甫《梦李白》中也写道:“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至于“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此类,更是数不胜数。
中西方诗歌对待距离的不同,我想是来自于两种文化体系中对待悲剧的态度。西方有希腊式悲剧作为文化基础,而中国则追求圆满的大团圆结局,所以西方诗歌在欲望达成前终止诗行,而中国诗歌则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消弭距离。但是诗歌中的距离是不可消弭的,这种徒劳无功的尝试更为诗歌增加了一层哀伤情调,成为中国诗歌中的独特意境。
二、上帝视角的创作者
米开朗琪罗认为:“最好的艺术家没有任何意图”。这句话我并不完全认同,所以我将它修改了一下——“最好的艺术家没有表达欲之外的任何意图”。
米开朗琪罗的《诗》中写道:
“你把毁灭和优美一起藏着
内心,低能的我已被燃着,
却只知道从中撰取一死。”
当他在雕刻那块“把毁灭和优美一起藏着”的大理石块时,他必须是冷静的,用上帝一般全面的视角观察他的艺术胚胎。一旦他被自己所雕刻的艺术品的美所点燃,妄想与其融为一体,他就会失去对艺术的控制,欲望(或爱)则如洪水将他的艺术品冲的七零八落。所以,艺术创造者必须与自己的作品保持距离,诗歌也是一样。当诗人失去对欲望的控制时,距离消失,让人们看见“肉体是忧伤的”这一毫无美感的苍白真相。
诗人只能是旁观者,执笔的他像是上帝,冷眼看着自己的痛苦,欲望的折磨,所咏之物的魅力。无论笔下有多少痛苦,激情,都是回忆痛苦的痛苦,幻想激情的激情。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一段话为诗人要在创作过程中保持距离给出了非常合适的理由:“然而,当人亡物非,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久,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忍不拔的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和你的欲望保持距离,不要去触碰那些情感,你只需要回忆这欲望给你带来的一切感受,独善其身,然后诉诸笔端即可。就像死去后看着镜子里自己的鬼魂。
在中国诗歌中也有足够多的例子来佐证创作者需要与自己的艺术品保持距离这一观点。比如贾岛对自己的诗中究竟用“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拿不定主意。用“推”还是用“敲”就是怎么还原诗人脑中意境或者回忆的争论。这只有在诗人冷静创作,与自己的艺术品保持距离,用上帝视角审视自己的作品时才会发生。如果他被欲望吞噬,不能既融入诗歌中又保持创作的意识在外,就不会有“推敲”的思索了。
但是,在中国诗歌的观点中还透露出“入乎其内”的思想。这是与西方思想不同的地方。从龙沙《玛莉的爱》可以看出,“入乎其内”是一种会到达歧途的幻想,会使诗歌走向预期效果的反面。要达成艺术,就只能从诗歌所言之物中出来,成为保持距离的那个人。距离是不能在创作途中被消弭的。艺术的诞生过程是欲望和距离的拉扯制衡,如同刀尖上的舞蹈。只有当审美距离最终依然存在时,艺术才是艺术,诗歌才能称为诗歌。
在中国,对“入乎其内”有不同的认识。王静安有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保持距离,让艺术不必流俗,消弭距离,让艺术拥有灵魂。
而顾随是这样解释创作者之于作品的审美距离的:“身临其境者难有高致,以其有得失之念在,如弈棋然。”同时又对“出乎其外”作了如下解释:“一者,为与此事全不相干,如皮衣拥炉而赏雪,此高不足道;二者,若能著薄衣行雪中而尚能‘出乎其外’,方为真正高致。”恰当的审美距离是能够深入自己的欲望摸索其形状,却又不被其迷惑导致迷狂。
西方诗歌观念认为,诗歌是距离的投射,相当于一块顽石,而诗人只能雕琢,却不能使之软化成为肉体。中国诗歌观念则认为,你可以用自己的幻想来使这顽石软化成为肉体,却依然要将这鲜美的肉体目为顽石。
三、读者与诗歌之间的距离
当我们在阅读某首诗歌时,常常能够感受到时间上与空间上的距离。我们知道,单纯的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不是审美距离,但是当这种距离面对诗歌时,情况却有所不同了。因为诗歌像是一种古董,一年一年的流传下来,时间距离最终会是一层层累加上去的故事,而空间距离则会导致更多的想象和幻想。诗歌有自己的命运,比古董幸运的是,它不会因为保存不当而锈迹斑斑或者千疮百孔。不过,某些诗歌的命运轨迹一点也不会比古董的神秘性要小。于是这些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就被转化为读者的心理距离,也就是审美距离。

元稹,是白居易十分亲密的朋友,在他被贬到通州后,在某堵墙上见到了一首诗,他觉得写的十分好,就寄给了白居易,而白居易发现这是自己十五年前写的诗,并为它为何会在多年后被提上千里之外的一堵破墙而疑惑。他为此事写了一首诗:
十五年前似梦游,
曾将诗句结风流。
偶助笑歌嘲阿软,
可知传诵到通州。
昔教红袖佳人唱,
今遣青衫司马愁。
惆怅又闻提处所,
雨淋江馆破墙头。
——《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
白居易在十五年后,成为了自己创作的诗歌的读者,并感受到了一种心理距离——他触摸不到这首诗的时间轨迹,无法确定它经历了什么才被刻在墙头成为一首特殊的诗歌,他对诗中所描述的情景也有距离感,那是他十五年前的事情,是千里之外的长安。这审美距离终于化为又一首诗歌,既《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他能够感受到,那首宴会上随性而作赠与歌妓的诗已经不再有它诞生时最初的意义。
他被从一原由网张口传诵到另一张口,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最后被提在墙上,慢慢的被雨打风吹去。现在白居易自己成为了阅读者,他的阅读给这首诗带来了新的意义:“今遣青衫司马愁”。这首诗让他想起轻狂的年少,想起自己凄凉的境遇,勾起一阵惆怅。他与这首诗有距离了,这首诗比十五年前更有魅力了。白居易就像是突然意识到孩子长大的父母,无措至极,也认识不到孩子的思想,父母对这个长大的孩子失去了控制权。
诗歌自诞生以后的第一次传唱就在赋予新的含义,因为诗歌是情感的载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同样的情感映像会勾起截然不同的情感。李煜的恋情词,“刬袜步香阶, 手提金缕鞋”,多么香艳甜蜜。但是当南唐灭亡之后,人们再读这首词,恐怕也要在微笑过后长叹一声。再比如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当南宋灭亡,为夷狄统治时,读来又是一番滋味,刘克庄为此写道:“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林景熙也写道:“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这时,陆游的沉痛又因为时间和时代的变迁而加深了,变得更加痛苦,触目惊心。
这类审美距离并非诗歌本身直接带来的,而是时间和空间的加持作用。而另一种读者与诗歌之间的审美距离,则是诗歌本身一手促成的。
西班牙作家洛尔迦写道:
“我用呻吟之词歌唱他的优雅,
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橄榄树之于西班牙,就像白桦之于俄罗斯,樱花之于日本,郁金香之于荷兰。橄榄树林在西班牙乡下的土壤中抽根发芽拔节,一年又一年,与它们一起的是西班牙人的出生,嫁娶,死亡;是西班牙人的生活,革命,流血与宁静;是西www.58yuanyou.com班牙人的悲欢苦乐。这些悲欢苦乐太过平常,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就像鱼不会注意到水。但是,//www.58yuanyou.com当诗歌将这些平实的情感变成“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时,却成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诗句。因为当一切浓缩成一阵风,成为另一种陌生的形态时,我们感觉到了距离,当这阵风吹过熟悉如自己血肉的橄榄树林时,又激起一阵阵共鸣。这共鸣正是因为有了距离感,才能产生波动。
当读者读洛尔迦的诗时,他们退出了生活的舞台,成为一个观众,欣赏悲风是怎样吹过橄榄树林,生活就在那阵风里,触摸不到它,只能远远看着,从而想起自己的生活。记忆中的生活片段,就像这阵橄榄树林的风一样美丽,一样悲伤,一样发出欢乐的摩擦枝叶的碎响。
诗歌将我们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了,为内里相互关联的东西塑造了互不相关的造型。读者在阅读时,陌生化的诗歌语言产生了审美距离,从而达到读者与诗歌的共鸣。这是西方诗歌在被阅读时常常出现的,美好的距离。

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西方诗歌,读者阅读时都是在体验诗歌隐含的欲望,体验自己欲望的共鸣。读者可以看见诗歌中的审美距离,明确这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带来多大的诱惑和魔力,而阅读本身,也因为审美距离而将文本变得充满生命的香气。审美距离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要求,是创作者恪守的原则,也是读者享受阅读和思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