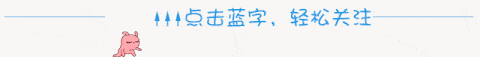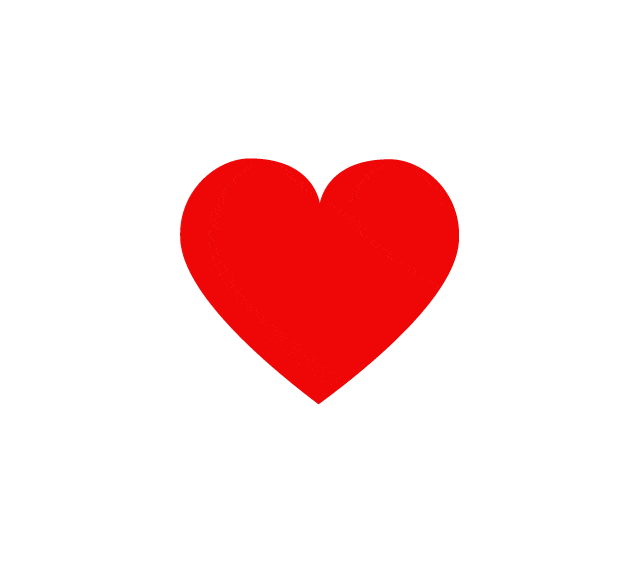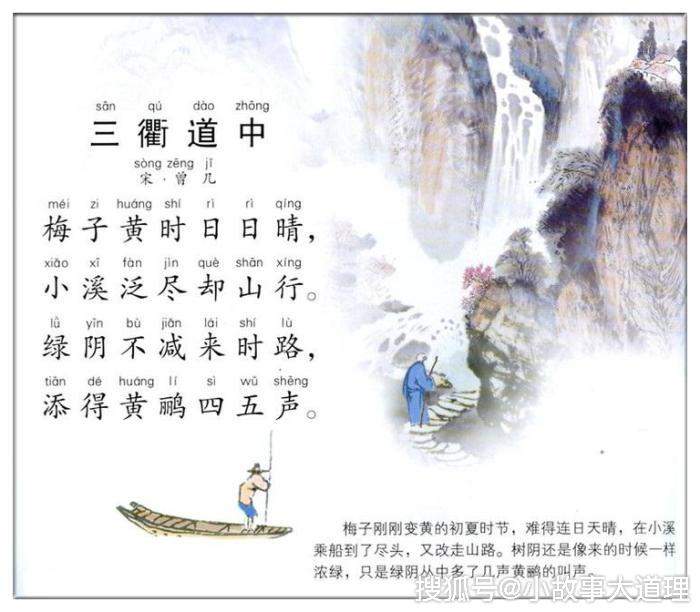▲点击上方“泉城时光”订阅▲
泉城时光 只跟影迷和有意思的人在一起
入微信群 联系微信 qqxietian
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属于小说原作者肖江虹,仅供学习交流之用。
《百鸟朝凤》正在上映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票
15
老马的葬礼新鲜而奇特。
乡村的葬礼不一定非得沉痛,但起码是严肃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去了那头,这叫喜丧,气氛是可以鼓噪些的。老马六十不到,他的葬礼是没有资格欢欣鼓舞的。可就在他入土的头一个晚上,马家大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气洋洋,那些奔丧迟到的人走进马家大院都一头雾水,以为走错了门,这里怎么看都像是老马家在娶媳妇,说在办丧事打死人家都不相信。
让老马由死而生的,是那支乐队。
先是几个人叮叮咚咚的乱敲一通,然后就唱开了。
鼓捣吉他的边弹边唱,唱的过程中还摇头晃脑的。他唱的是什么我听不懂,我的师弟蓝玉在一旁跟着哼哼,我问蓝玉他唱的是什么,蓝玉说是时下正流行的,只能跟着哼哼几句,整个儿的记不住,曲子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了。
开始,木庄的乡亲们站在院子里,脸上都有了怒气。每个人都不很适应,脸上都有矜持的不满,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婆把手里的一棵白菜狠狠的摔在地上,眼神离奇的愤怒,嘴里还咕咕囔囔,最后很沉痛的看了看灵堂。我知道他是在为死去的老马打抱不平呢!
渐渐的,大家的神色开始舒展开了,有一些年轻人还饶有兴致的围在乐队的周围,环抱双手,唱到自己熟悉的曲子时还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哼。
游家班站在马家大院的屋檐下,局促得像一群刚进门的小媳妇。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唢呐,才忽然想起来我们也是有活干的。
雨停了,空气清爽得不行,干干净净的。院子里为游家班准备的呈扇形排开的凳子还在。我们过去坐好。我看了看几个师兄。
“还吹啊?”一个师兄问。
“怎么不吹?又不是来舔死人干鸡巴的!”我对他的怯懦出离的愤怒。
我还拿起脚边的酒瓶子灌了一大口烧酒,悲壮得像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
呜呜啦啦!呜呜啦啦!
平日嘹亮的唢呐声此刻却细弱游丝,我使劲瞪了几个师兄两大眼,大家会意,腮帮子高鼓,眼睛瞪得斗大。还是脆弱,那边的声响骄傲而高亢,这边的声音像临死之人哀婉的残音。一曲完毕,几个师兄都一脸的沮丧,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吹,往死里吹,吹死那群狗日的。师弟蓝玉在一边给大家打气。
我们吹得很卖力,在那边气势较弱的当口,就会有高亢的唢呐声从杂乱的声音缝隙里飚出去,那是被埋在泥土中的生命扒开生命出口时的激动人心,那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划燃一根火柴后的欣喜若狂。
我们都很快意,那边的几只眼睛不停的往这边看,看得出,眼神里尽是鄙夷和不屑,甚至还有厌恶。
说实话,我对这群不速之客眼神里的内容是能够接受的,甚至他们就应该对我手里的这支唢呐感到厌恶才对。只是我没有想到,对我手里这支唢呐感到厌恶的不光是他们。
一个围在乐队边唱得最欢的一个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的面前。他斜着脑袋看着我,表情怪怪的,像是在瞻仰一具刚出土的千年干尸。我把唢呐从嘴里拔出来,吞了一口唾沫问:干什么?
你们吹一次能得多少钱?他说。
和你有关系吗?我答。
我付你双倍的钱,条件是你们不要再吹了。
我摇头说那不行。
没人喜欢听你们几根长鸡巴吹出来的声音。
那我也要吹。
这时候我的师弟站出来了,他过来推了年轻人一把。说柳三你干啥?叫柳三的说关你啥事?蓝玉说就他妈关我的事,咋了?
两个人就你来我往的开始推搡。本来已经有人过来劝住了的,柳三这个时候像想起了什么来,然后他说:“哦!我差点忘记了,你原来也是个吹破唢呐的!”说完还嘿嘿的干笑两声。
我看见蓝玉的拳头越过三个人的脑袋,奔着柳三的脑袋呼啸去了。一声闷响后,殷红的鲜血从柳三的鼻孔里奔涌而出。场面一下子就乱了,呼喊声,叫骂声,拳头打中某个部位后的空响,夹杂在癫狂的乐曲声中,活像一锅滚热的辣油。www.58yuanyou.com
第二天是蓝玉送我们离开的。我的师弟脑袋上缠着一块纱布,左边眼圈像块圆形的晒煤场。在我们身后远处的山梁上,送葬的队伍爬行在蜿蜒的山道上,那利箭一样的乐器声响充斥着木庄的每一个角落。
16
水庄最近变化很多,有些是那种轮回式的变化,比如蒜薹又到了采摘的时候;有些变化则是新鲜的,让人鼓舞的,比如水庄通往县城的水泥路完工了,孩子们在新修完的水泥路上撒欢,大大小小的车辆赶趟儿似的往水庄跑,仿佛一夜之间,水庄就和县城抱成一团了。要知道,以前水庄人要去趟县城可不是那样容易的,不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五六个小时,你是看不见县城的。现在好了,去趟县城就像到邻居家串个门儿。
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游本盛站在自家大蒜地里,满脸堆笑。在他眼里,像水庄有了水泥路这些新鲜事儿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更关心的是他的大蒜地。今年的大蒜地倒是争气得紧,从冒芽儿开始就顺风顺水的,该采摘了,一根根在和风里炫耀着粗壮的身躯。父亲每天都要到大蒜地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啜着纸烟蹲在土坎上,没有比这让他更满足的事情了。
父亲弓着腰在剥蒜薹,一阵风过去,我看见了他两扇瘦窄的屁股。我说歇歇吧。他直起腰,回过头,一脸的怒气:“歇歇?歇歇都能有饭吃老子早歇了!”我不说话了,还后悔刚才说出来的话。我想我最好是闭嘴,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我的父亲都能找出让我难堪的理由。
可我发现,我不说话也不行,我不说话父亲也会把他的不满通过诸如眼神和动作传递给我。这一年来,父亲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了疑问和警惕,我就像一只潜入他们家偷食的野猫,不幸正好被他发现了。我这只偷食的野猫只好把尾巴藏着掖着,生怕主人那天不高兴了一脚把你踹出门去。
初夏是水庄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个时候的水庄可有生机了,天空清澈碧透,水面也清澈碧透,一庄子待收割的蒜薹也清澈碧透。最打动人的不管你走到哪里,每一个水庄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水庄人真的没有野心,一次理所当然的丰收就能把一个村庄变得天宽地阔。父亲不和我说话,埋下头继续采摘蒜薹。我直起腰,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一望无际的蒜地在阳光下像一幅油画。远远的,族中的三叔对着我远远的招手。三叔是我请去通知几个师兄弟出活的人。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无双镇的唢呐班子省掉了接师礼,连运送出活工具这些规矩都一并没了。我三步两跳的跑过去,先递给三叔一支烟,他撩起衣角擦了擦满脸的汗水,把烟点燃后对我说。
“都通知了,只有你大师兄同意来。”
“其他人呢?他们怎么说?”
“还能说啥?不是说忙就是这里那里不利索咯。”
三叔说完走了,走出老远了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回头大声喊:
“对了,你二师兄说以后不要去叫他了。”
“为什么?”我问。
“说下个月要出门了。”
“去哪里?”
“不知道,大城市咯!”
我悻悻的回过头,就看见了父亲那张铁青的脸,他两手叉在腰际,眼睛直直的看着我。我低着头从他旁边走过去,他在后面冷冷的笑,笑完了说:
“都快孤家寡人了吧?看你以后还怎么吹?吹牛X还差不多。”
晚上我没有吃饭,躺在床上,定定的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蜘蛛倒悬着垂下来,一直垂到我的鼻尖处,我伸出手,让蜘蛛降落在我的手心里,它就顺着我的手臂往上爬,时左时右,我不知道哪里是它想去的地方,或者它压根就没有目的地,只是这样一直往前爬,再往前爬,什么时候爬累了,织个网,就算安家落户了;又抑或被天敌给吃掉了,无声无息的,谁又会去关心一只蜘蛛的未来呢!
仿佛一眨眼时间,我身边这个世界一下就变得陌生了,眼里的一切都没变,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可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却不一样了,像水庄的那条河,看上去风平浪静的,可事实不是这样的,小时候下河游泳,一个猛子下去,才发现河底下暗潮汹涌。
直到父亲睡了,我才从屋子里出来。母亲重新把菜给我热了热。我吃饭时,母亲还是像小时候一样静静的坐在我的旁边,目不转睛的看着我,眼神里流淌着源源不竭的爱怜。
“后天是不是要出活?”母亲问。
我点点头。
“听你爹说几个师兄都不来?”
我又点点头。
“唉!”母亲长叹一声,然后她接着说:“天鸣,要不这唢呐不吹了!咱干点别的,凭咱这双手干啥不能活命啊!”
我放下碗,转过去对着母亲。
“我知道这个理,可当年拜师的时候我给师傅发过誓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这唢呐吹下去。”
“可你看,就你一个人也吹不来啊!”
“过两天我去找师傅。”
17
我还没来得及去找师傅,师傅就先来找我了。
师傅一进院子就骂:“你个小狗日的游天鸣给老子出来。”
我出来看见师傅站在院子里,他的双脚沾满了泥,连衣服的下摆都有星星点点的泥点子。脸和我当初去拜师的时候一样黑,只是皱纹更多了,看见师傅老了一大截,我忽然上来了一些伤感。这个无双镇当年响当当的焦家班的掌门人,像入了冬的一棵老槐树,尽是令人沮丧的残败。最揪心的就是他一身灰布衣服了,还是老式样,对襟衫,几个地方都是补丁,要知道,现在无双镇像这样有补丁的衣服是不多见了,偶尔看见,不会有人说你艰苦朴素,下意识还会把你往穷人堆里推。
我喊了一声师傅。
“不要叫我师傅,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师傅往地上狠狠的啐了一口痰:“当初你是怎样说的,有口气就要把这活往下传,可这才过去多久?昨天就有人给我递话了,说无双镇的游家班散伙了,垮台了,有活也不接了,无双镇从今以后就没有唢呐匠了。”
我说师傅你先进屋,我们到屋里说。师傅一挥手:“进不起你的宝殿门,你现在哪里还瞧得上吹唢呐的?”。还是母亲出来,说焦师傅你先不要着急,进来说,天鸣正托人到处通知他的师兄弟们呢,这几天就要出活。母亲说话时不断对着我眨眼,我慌忙应和说对对对。师傅火气这才消了些。背着手走进屋,也不看我,只说,不给老子说个一二三,看老子不撕破你那张X嘴。
师傅坐下来,接过母亲倒来的茶,怒气冲冲的等我的解释。听完我的解释,师傅把茶碗往桌上狠狠一掼。
“我去找他们,几个狗日的还翻天了。”
师傅出了院门,看我还站在屋檐下,就吼:“傻了?游家班班主是我还是你?”,我哦了一声,才快步跟上去。
我跟在师傅身后,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有,但我能清晰的听见他大口大口喘气的声音。
二师兄对我和师傅的到来有些意外。当时二师兄正在打点行装,屋檐下,他正把一捆衣物狠命的往一个陈旧的蛇皮口袋里塞,口袋太小,装不下二师兄远涉的必须,就委屈地从口沿处往下撕裂,还发出吱吱的怪叫。二师兄骂了一句,抬起头就看见了师傅和我,他的嘴上下翕动着,是想说些什么,但从师傅的脸色他似乎已经明白了我们的来意,于是就什么也没有说。他放下手里的袋子,直起身子,从屋檐下的檐坎上下来,站在师傅面前,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
师傅没有理二师兄,鼻子有了一声闷哼后,径直走到屋檐下,把口袋拎到院子里,把口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掏出来往院子里抛撒。师傅的这个动作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惊讶于这个看上去个儿不大的口袋居然有如此壮观的吞吐量,等师傅捋直了身子,院子里早成了花花绿绿的晾晒场。
师傅把干瘪的口袋踩在脚下,目光盯着二师兄,那眼神像水庄六月的日头,能把人烤晕过去的。
二师兄低着头,他一句话没有说,两个手交互搓揉着,这时候有几只麻雀从天而降,欢快的在院子里那些各式各样的衣物上跳跃。二师兄忽然松开了两只互握着的手,低头从师傅旁边走过去,蹲下身子把地上的衣物一件一件的拾起来搭在臂弯处,其间还拍拍打打的扇掉衣物上的灰尘。等他臂弯放不下后,他就慢慢蹲着移到师傅的脚边,伸出一只手扯师傅脚下的蛇皮口袋,师傅一动不动,师兄却执着地扯,力量也越来越大,最后我看见师傅的身体都开始摇晃起来。我站在一边看着这对奇特的师徒,他们就像在出演一出哑剧,每一个动作和眼神都极具深意,所有的表达都在你来我往的无声的动作中了。这时我的师傅伸出一只脚,狠狠的踹向了他二徒弟的面部,我看见二师兄猝然的往后倒了下去,像刚被掏空的蛇皮口袋。好半天,师兄才复苏的蛇一样从地上卷曲着爬起来,两道殷红从他的鼻孔蜿蜒而下,几乎穿越了整个面部。他没有完全站起来,依旧半蹲着,一步步挪到师傅的脚边,伸出一只手,固执的去扯师傅脚下的口袋。
这时候,我看见我的师傅面部完全变原由网成了死灰色,五官也剧烈地痉挛着,像一锅煮烂的饺子。良久,他终于仰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叹气的感觉和水庄冬天的寒风一般,经过皮肤,直抵骨髓,能把人的那颗心都冻僵了。他终于移开了紧紧踩踏着口袋的脚,转身走了,走得很快,留给我一个颤抖不止的背影。
18
道路弯弯拐拐,曲折迂回。乡间小路就是这样,站定一个点,极目远眺,道路伸出去没多远就倏然不见了。赶上去,才发现它又折向了某一个去处,再远眺,还是只能看到一根断面条。我们就在这样一条琢磨不定的道路上走着。最前面是我的师傅,中间两个,一个大师兄,一个蓝玉,我跟在最后头。
蓝玉自从离开土庄后,没有出过一次活。今天他能站在游家班的队伍里,我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师傅是怎样说服蓝玉跟我们出这次活的。那天师傅离开二师兄家后,就直奔木庄去了。昨天晚上,蓝玉推开了我家的门。
师傅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衣服上的折痕都还清晰可见。他走得很快,像一只老当益壮的野兔。蓝玉有意把步子放慢,很快我们的队伍就断裂成了两个块,前面是师傅和我的大师兄,后面是我和我的师弟蓝玉。
和我并排着的蓝玉忽然说:“师傅老了!”。我点点头,蓝玉又说:“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出活,也是最后一次。”。我转过头看着蓝玉,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过了半晌,蓝玉自言自语:“我答应师傅的,师傅也答应我的。”。
我的师弟蓝玉就是这样,总让我琢磨不透,说话也玄机重重。我说这话什么意思?蓝玉笑笑,没说话。我就低头自己想,等我抬起头的时候,幽静的山路上就看不见人影了。
在无双镇,和其他几个庄子比,火庄一直落在后面,房屋还多是拉拉杂杂的茅草屋,道路也没有其他几个庄子来得宽敞。但火庄人老实。无双镇人到集市上买鸡蛋,特别是买土鸡蛋,都要先问问是哪个庄子的。说是其他庄子的,人家不敢买。那是因为吃过亏的,问的时候一个劲给你打包票说真是土鸡蛋,买回去打开,一眼的翻白。只有火庄的土鸡蛋货真价实,黄澄澄的不说,价格也合理。今天出活的人家在火庄的西头,看上去家境一般,房屋翻了新,但屋子里却空闹闹的,只有些日常生活必须的物事,看来是屋子翻新耗光了家资。
家境虽是一般,可仍旧热闹。这和死去的人有莫大的关系,死者是火庄的老支书。德高望重的老支书躺在堂屋里,安静得像一只睡去的猫。师傅过去恭恭敬敬的上了三炷香。晚饭毕,我们一班人聚在堂屋里,我百无聊赖,把玩着手里的唢呐。师傅则拿出他那支老黄木杆的唢呐不停地擦拭。
大师兄把唢呐放进嘴里调音,咕咕唧唧的。师傅说你们都收起来,今天天鸣一个人吹。说完把擦拭好的唢呐递给我。
我出奇的惊讶,大师兄更惊讶,连嘴里的唢呐都忘记卸下来了。
“为什么?”我问。
“他去过朝鲜,剿过匪,带领金庄人修路被石头压断过四根肋骨。”师傅面无表情的说。
“百鸟朝凤!”蓝玉一扫慵懒的模样,绷直了问。
架势是摆出来了。灵堂前一张宽大的木靠椅,一群孝子俯首跪倒在我面前。所有的人都站在院子里,仰直了脖子往灵堂里看,连一直撒欢的那条老黄狗也规规矩矩的端坐在院子里。
我忽然有了一种神圣感,像一个身负特殊使命的斗士。那些眼光让人着迷,在每天来来往往,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你是看不到这种眼神的。它是那样的干净无邪,仿佛春雨过后山野里散发着的清新气息,又像是冬雪里萦绕在山巅的蒸腾雾霭。
师傅站了出来,对着灵堂鞠了三个躬,然后转过身对众人说:
“百鸟朝凤,上祖诸般授技之最,只传次代掌事,乃大哀之乐,非德高者弗能受也。”,我知道这几句是《百鸟朝凤》曲谱扉页上的几句话,下面的人是听不懂这几句话的,所以还是一贯的沉默。师傅接着说:“窦老支书我不多说了,他的所作所为金庄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无双镇还有人能受得起‘百鸟朝凤’这个曲子的,窦老支书算一个,今天,给窦老支书吹奏送行的,是游家班的班主游天鸣。”。师傅的诚恳让跪倒在我面前的一干人开始发出呜呜的低鸣声。
“大哀至圣,敬送亡人,起奏!”师傅高喊。
我把唢呐送到嘴里,忽然眼前一片漆黑。
直到今天我都活在那段悔恨中,我本可以从容的完成一个乡村乐师所能完成的最高使命,可以让后人提起这段近乎传奇的事件时还能提起我的名字,本可以让乐师这个职业在乡村实现最动人的谢幕演出,甚至可以用一种近于神圣的方式结束我的乐师生涯。可就在那一瞬间,这些可能统统没有了,我的行为让无双镇这个古老的职业用一种异常丑陋的形式完结掉了,连在湮没于时代变化中的最后一刻也未能保持它曾经拥有的尊严。所以,在记录下这段经历的时候,我面临着可怕的记忆煎熬,我感觉我心灵深处的一块被时间慢慢治愈的伤疤又被重新揭开,我清楚的看见它鲜血淋漓,继而是透骨的疼痛。
重新睁开眼,一双双焦渴的眼睛全都在看着我。我把唢呐从嘴里慢慢抽出来,站起来对我的师傅说:
“对不起大家,这个曲子我忘了!”
出人意料,师傅笑了,下面的人也笑了。下面的人还在笑,师傅却哭了,他蹲在地上放声痛哭,我、我的大师兄,还有我的师弟蓝玉,我们站在师傅的身边,谁都不说话。师傅哭了一阵,站起来对还跪在地上的孝子鞠了三个躬,说我们对不起窦老支书,也对不起各位孝子。
焦三爷吹一个不就行了!人群中有人建议。
师傅摆摆手,说我早就没有这个资格了,这个班子不是焦家班,只有游家班的班主才有这个www.58yuanyou.com资格。师傅说完转过身从我手里抢过那支唢呐,抬起膝盖,两手握着唢呐猛力一沉。
咔嚓!
师傅走了,他迅速消失在了金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蓝玉从地上把断成两截的唢呐拾起来,又看看我,说:“看来我这辈子是听不了百鸟朝凤了!”
19
父亲对我的态度是越来越坏了,他看我什么都不顺眼,水缸空了,他骂我眼瞎了,连水缸没水了也看不见;我把水缸挑满了,他还骂我,说我除了挑水还能干啥?
父亲骂得对,我都二十六七岁的人了,还窝在家里。你看水庄和我一般年纪的人,娶妻的娶妻,生子的生子,还有大部分早就打点好行装,爬上开往县城、省城的客车走了,除了过年过节能看到他们一两眼,平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村里几乎就看不到了。
自从游家班解散后,我再没吹过一天唢呐。
游家班的解散没有什么仪式,自自然然的,仿佛空气蒸发了一样,请也没人请了,吹就更没有人吹了。我和大师兄在无双镇的集市上遇到过一次,我们互相问候,还谈了今年庄稼的长势,最后还到无双镇的馆子里喝了一顿烧酒,可谁都没有说关于游家班的事情,哪怕一丁点也没有,像这个班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
我二十八岁了,水庄的冬天又来了,水庄的冬天如今是越来越随便了,连场像模像样的雪都没有,最近两年更是蹬鼻子上脸,连点缀性的雾凇也看不见了,整个冬天都邋里邋遢,只知道一个劲的落冰雨,钉得人脸手生疼不说,还把一个水庄搅得稀泥遍地。
我现在最怕和父亲照面,不光是怕他骂我,是看着他一天天老去的模样我就会内疚。别人的儿子每年都能给家里寄回来数目不等的钱,我却只能坐在家里吃吃喝喝。母亲不像父亲那样责骂我,但她总是一声接着一声的叹气,叹气的声息像一块永远挤不干水的海绵,这比父亲的责骂让我更难受。就这样,我不得不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逃避。父亲每天吃完饭就去庄上看人打牌去了,他不参与,只是看,其实父亲很想坐上去摸一摸的,可他的口袋不允许。母亲则是每天都在灯下一直坐着忙,忙到实在疲乏得不行了才去睡觉。
我每个夜晚都早早爬到床上,却往往到了天亮还没有睡着。
今年从稻谷返青开始就没有落过一泼雨。本来都乌云密布了的,天地也陡然黑暗了,眼看一切前奏都摆足了,一庄子人都站在天地间等着瓢泼的雨水了。结果呢,稀稀拉拉的下来几滴,在地上留小几个濡湿的坑点,立马就云开雾绽了。反复几次,水庄人的希望和耐心像田里的稻谷一样,都干枯瘪壳了。
父亲的背越来越佝偻,像一张松垮垮的泥弓。父亲每天都守在他的稻田边,脸色和稻子一样枯黄。他的眼神散漫无力地在一坝子干瘪的稻浪上翻滚,跟着风的摆动,晃来荡去,软弱无力。就这样一直到黄昏,他才直起腰来,在一阵吱吱嘎嘎的骨头摩擦声中,开始把枯朽的身躯往自家屋子里搬运。
偶尔我会在院子里遇见他,他总是呆呆的看着我,没有了愤怒,也没有了讥讽,目光蛛丝一般的柔软,缠得我有些透不过气来。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季的稻谷最后全枯死在了田里。我站在水庄后面的山头,视野里是一片灼人的枯黄,那黄一直向天边延伸,这样的颜色真让我绝望。但水庄的游本盛更让我绝望。一张脸黄得肆无忌惮。肝癌晚期,我和母亲竭力要求把圈里的老牛卖掉给他治病,可游本盛说:算了,我就是田里的稻子了,再大的雨水也缓不过来了。
一个月来,父亲的身体在木床上越来越小。从医院回来,父亲就再没有离开过家里那张宽大的木床。木床是爷爷留下来的,父亲当年就在这张大床上降生,如今,他又即将在这张大床上死去,像完成了一个可笑的轮回。
早晨我把家里的老牛牵到水庄的河滩边吃了一些草。中午回家的时候,我居然看见父亲站在庄头,阳光把他捏成一小团,他把身体靠在土坎上,土坎上有茂密的青色,这样他就像一朵从草丛里长出来的黄色蘑菇。我远远就看见了他,惊讶过后眼泪就下来了。
我怕他看见我的眼泪,拭干了才走近他。他颤颤巍巍地过来,像刚学走路的小孩儿。拍了拍老牛的脖子,父亲说:“把它卖了吧!”,说完了居然下来了两滴眼泪。我明白了,父亲还不想死,他毕竟才五十出头,这样年纪的水庄人,都身强体健的穿梭于田间地头,还有使不完的劲,眼前的路还远得看不到头呢!“早该卖了,早卖早治的话,也不至于这样了。”我说。
牛卖掉那天,我在无双镇给父亲买了一双软底布鞋,我想过了,进城治病难免要走来走去的,软底布鞋穿上不硌脚,父亲全身只剩下骨头了,什么都该是软的才对。
晚上回来把鞋子递到父亲手里,他竟然从床上翘起来给了我一耳光。
“谁叫你费这钱?狗日的就是手散!”
耳光一点不响亮,听见的反而是骨头炸裂的声音。
我没有说话,把父亲扶下躺好,他两个鼻孔和嘴都大口大口的呼着浊气。喘了好一阵子,父亲终于平静了下来,他先是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艰难地把身体侧过来对着我说:“天鸣,我听说金庄的唢呐也吹起来了。”我点点头。
其实不光金庄,无双镇除了水庄其他几个庄子都有唢呐了。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城里下来的乐队就从无双镇消失了,就像停留在河滩上的一团雾,一阵风过,就无影无踪了。乐队一消失,唢呐声就嘹亮起来了。
“把游家班捏拢来。”父亲说:“无双镇不能没有唢呐。”
“有哩!除了水庄其他庄子都有了。”我说。
“日娘,那叫啥子唢呐哟!”父亲面色灰土,喘气声也大了许多,额头上还有汗出来。
我呆坐在床边,不说话。父亲的喉咙里有咕咕的声音,像地下的暗河,涌动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良久,我听见父亲发出呜呜的哭声,哭声尖而细,如同一柄锋利的尖刀,划过屋子里凝滞的气息,继而如撕裂的布匹,陡然凄厉得紧。
此刻我才发现,我的父亲,水庄的游本盛心里一直都希望他的儿子吹唢呐的。在游家班解散后,父亲那种看似寡毒的蔑视、打击、嘲讽,其实是伤心欲绝,是理想被终结后的破罐子破摔。我又想起了父亲带着我拜师的那个湿漉漉的日子,还有他跌倒后爬起来脸上那道殷红的血痕。
我伸出手,摸到了父亲夸张的锁骨,它坚硬地硌着我的手,更硌着我的心。
我试试吧。我说,声音很小,但父亲还是听见了。
尽管屋子里光线很暗,但我还是看见了父亲眼里的亮光,我的话像一根划燃的火柴,腾地点亮了父亲这盏即将油尽的枯灯。
“我就知道,你狗日的还想着唢呐。”笑容在父亲枯瘦狭窄的面容上铺开,氲成一团凄苦和苍凉。“知道我为什么卖牛吗?”父亲纯真得像一个孩子:“我那是给游家班买家什用的,我想过了,啥子鼓啊锣啊,都老旧了,该换新的了。”接下来就是一阵咳嗽,父亲太兴奋了,又呼啸了一阵才平静了下来,父亲又说:“我死了,给我吹个四台就行了。”
“我给你吹‘百鸟朝凤’。”我说。
父亲摆了摆枯瘦的手,半天才说:“使不得,我不配!”
20
父亲病得越来越重了,话也越来越少了,开始是整夜整夜睡不着,后来是睡过去就醒不来。母亲总是守在父亲旁边,隔一阵子就看一回,探探他的鼻孔,摸摸他的额头,怕他睡过去就永远醒不来了。
我则在无双镇几个庄子之间昼夜奔走。
在无双镇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在如此密集的时间里听田间的蛙鸣,山谷的鸟叫。夜晚,我一个人在狭窄的山间小路上行走,天边的一弯冷月漠然地朗照,大地如逝者的巴掌一样冰凉,裹紧衣服才发现,寒冷正不可抗拒地到来。脑子里又浮现出父亲孤独无助的眼神和日渐枯槁的面孔。我怕他等不到我把游家班捏拢他就走了,那样我的父亲就听不到唢呐声了。对于水庄的游本盛来说,没有唢呐的葬礼是不可想象的。
无双镇被我的双脚丈量完毕了,我仍像一个出海旬月却两手空空的渔人。我的师兄师弟们,此刻正在繁华而遥远的城市挥汗如雨,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般,整整齐齐地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
大师兄还在。他不去城市不是他不想去,而是一次意外让他拥有了一条断腿,而这条腿也成了他和城市之间永远的屏障。我把香烟递到他手上的时候,他还满含神往的给我讲述了师弟蓝玉去年来看他时的情景。“小屁股,抽的烟一支顶你这个一盒,你还别不服气,那烟抽起来就是他奶奶的顺口。”“看来,城里这钱还真他奶奶的好挣。”
听完我的来意,大师兄惊奇地盯着我,然后他说,你见过两个人吹的唢呐吗?旧时一般穷苦人家都四台,你想造个两台?埋条死狗还差不多。我说不是埋死狗,是埋我的父亲。大师兄脸上才起来了一层歉意,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说去火庄吧,那里起来了好几个班子,听说场面很大,都有十六台了。奶奶的,十六个人一起吹唢呐,怕死人都能给吹活呢!
我走了好远,大师兄站在山梁上喊:“去看看吧!如今无双镇的唢呐都成他们的天下了。”
我到火庄正赶上这里的唢呐班子出活。
确实很让人惊讶。
十六个唢呐匠占据了整个院坝,连死者这个理所当然的主角都被逼到了狭窄的一隅。一排条桌浩浩荡荡的拉出了雄壮的架势。条桌上的茶盘里有香烟和瓜子。瓶装的润嗓酒也精神抖擞的站成一列。唢呐匠一色暗红色西服,大宽领,下摆还卷了圆边,一个个像即将走入洞房的新郎。条桌顶头是一件银灰色西服,还扎了根猩红的领带,胸前挂了一块亮闪闪的牌子。看样子,他就该是班主了。
最显眼的还不是班主,而是他面前盘子里的一沓钞票,百元面额的,摞出了一道耀眼的风景。“起!”班主发声,接下来就是一场宏大的鼓噪,唢呐太多了,在步调上很难达成一致,于是就出现了群鸟出林的景象,呼啦一片,沸沸扬扬,让人感到一些惶然的惊惧。我甚至满含恶意地发现,有两个年轻的唢呐匠腮帮子从头到尾都瘪着,要知道,这个样子是吹不响唢呐的。这是我见过场面最大的唢呐班子,也是我听过的最难听的唢呐声。我的大师兄说得不对,十六台的唢呐不能把死人吹活,但没准会把活人吹死。
我回到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凑到他的耳朵边说:给你请个火庄的八台吧!父亲忽然睁大眼睛,脑袋拼命地摆动,喉咙里咕咕地响着。我知道,他不要火庄的唢呐,他说过的,火庄那不是真正的唢呐。
水庄的游本盛是水庄的河湾开始结冰时离开这个世界的,他静悄悄的就走了,头天晚上还挣扎着吃了半碗稀饭,第二天一早,发现身体都已经变得冰凉了。他死的时候瘦的像个刚出生的婴儿,把一张木床映衬得硕大无比。我把卖牛的钱将父亲安葬了。他的葬礼冷清得如同这个季节,唢呐声自然是没有的,倒是北风从头到尾都在不停地呼啸。
那个黄昏,我守在父亲的坟边。从此以后,水庄再没有游本盛了,他和深秋的落叶一起,凄凄惶惶地飘落、腐烂。我在夕阳里想了好久,都没有想起我到底给了我的父亲什么。而我对于他,只有一个又一个的失望。我的唢呐没了,游家班也没了,直到死去,他连一台送葬的唢呐都没有。
好久没有看到水庄这样的黄昏了,在我的印象中,水庄的黄昏总是转瞬即逝的,刚发现它,它就一头栽进黑夜。其实心细一点观察,水庄的黄昏是很好看的,落日静止在山头,草的须穗摩挲着它的脸面,有了麻酥酥的微痒;风翻滚着从山梁上滑下来,撩开大山的衣襟,露出暗红的裸背。大地,就在这样简单的组合中,变得古老而温暖。
我从怀里抽出唢呐,对vwTEDDYUsO着太阳的方向,铜碗里就有了满满的一窝儿夕阳。
曲子黏稠地淌出来,打了几个旋儿,跌落在新鲜的坟堆上,它们顺着泥土的缝隙,渗透进了冰冷的黄土。我知道,我的父亲能听见他儿子的唢呐声。从我学艺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没有听我吹奏过这曲“百鸟朝凤”。开始唢呐声还高亢嘹亮着,渐渐地就低沉了,泪水把曲子染得潮湿而悲伤,低沉婉回的曲子中,我看到父亲站在我的面前,他的眼神如阳光一般温暖,那些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在朦胧的视线里逐渐清晰起来。
起风了,唢呐声愈发凌乱,褪掉了肃穆的色彩,却有了更多的凄凉。我的喉咙被一大团悲伤嗝得生疼,唢呐终于哭了,先是呜咽,继而大恸。连绵不绝的群山,被一杆唢呐搅得撕心裂肺。
21
今年第一场雪刚过,村长领着几个人到了我家。
我站在院子里,村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就是无双镇游家唢呐班子的班主。
很年轻啊!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说。
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是省里面派下来挖掘和收集民间民俗文化的。
我说你就说找我什么事情吧。
戴眼镜的说我们想听一听你的唢呐班子吹一场完整的唢呐。我说游家班已经没有了,火庄有,你们去看看吧。那人笑笑,说我们刚从那里过来,怎么说呢!他干咳了一声:“我们听过了,他们那个严格说起来还不能算纯正的唢呐。”
你看?他递给我一支烟说。
我说怕不行了,我的师兄弟们全进城了。
这时候站出来一个年轻一些的,村长赶忙出来介绍说这是县里来的宣传部长。年轻的部长很豪迈的一挥手,说去把他们都叫回来,费用我们来出。他的语调和姿势让我热血一下涌了上来,我仿佛看到了我的游家班整齐出场的场景,那是多么让人神往的一个场面啊!七八个人一字排开,悠悠扬扬的吹上一场。我梦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
我说好。
冬天快过去了,我接到了蓝玉的一封信,他在信上说,他已经在省城站住了,拥有了自己的纸箱厂。我决定去省城把我的师兄弟们找回来,我要把我的游家班重新捏拢来,我要无双镇有最纯正的唢呐。
省城真大,走下客车我有了溺水的感觉。
根据地址东寻西找了一整天,我终于在一个胡同里找到了蓝玉的纸箱厂。
推开铁门,一个守门的老头在门里一间昏暗的屋子里看报纸。
请问蓝玉在吗?
“蓝厂长出门去了。”老头答:“你找他什么事?”老头抬起头问。
“师傅!!”
……
那天夜里,蓝玉把在这个城市的师兄弟们都通知到了一处,还请大家去了一家金碧辉煌的饭店吃了一顿饭。师傅还是老样子,饭桌上一句话没有,沉默寡言的吃。我说明来意,师傅的眼里掠过一抹亮光,然后他抹了抹嘴,说上面都重视了,这是好事啊!
好多年没摸那玩意了。二师兄感叹。
我从包裹里取出来一支唢呐递给二师兄,说试试?二师兄把唢呐接过去,端平,刚把哨管放进嘴里,他的眼神暮然黯淡,然后他举起右手,我看见我在木材厂打工的二师兄中指齐根没有了。
让锯木机吃掉了。他说,这辈子都吹不了唢呐了。
在水泥厂负责卸货的四师兄接过唢呐,说我试试,他架子还在,像模像样的摆好姿势,唢呐在他嘴里没有想象和期待中的嘹亮,只闷哼了一声,就痛苦地停滞了。他抽出唢呐吐出一口浓痰,我看见地上的浓痰有水泥一样的颜色。
别回去了,留下来吧!蓝玉看着我说。我喝了一大口酒,说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看着桌子上的师兄师弟们,我忍不住哭了,师傅也哭了。
我知道,唢呐已经彻底离我而去了,这个在我的生命里曾经如此崇高和诗意的东西,如同伤口里奔涌而出的//www.58yuanyou.com热血,现在,它终于流完了,淌干了。
夜晚,师傅还有师兄弟们送我去火车站。我们沿着城市冰冷的道路一直走,没有人说话,只有往来的车辆拉出让人心悸的呼啸,偶尔有行人经过,都一色的低着头,把脑袋往前伸,急冲冲的扑进城市迷离慌乱的大街小巷。
在车站外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下,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正举着唢呐呜呜地吹,唢呐声在闪烁的夜色里凄凉高远。
这是一曲纯正的“百鸟朝凤”。
泉城时光 只跟影迷和有意思的人在一起
长按上图识别关注。入微信群联系微信 qqxietian
↓购票可点“阅读原文” 有话要说请“写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