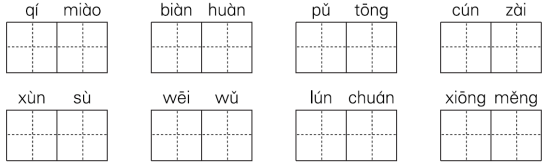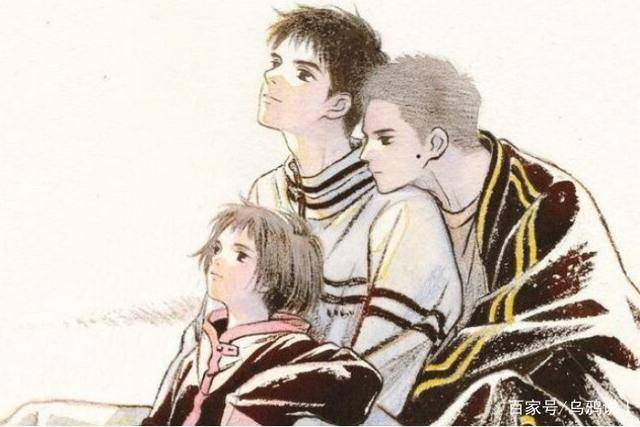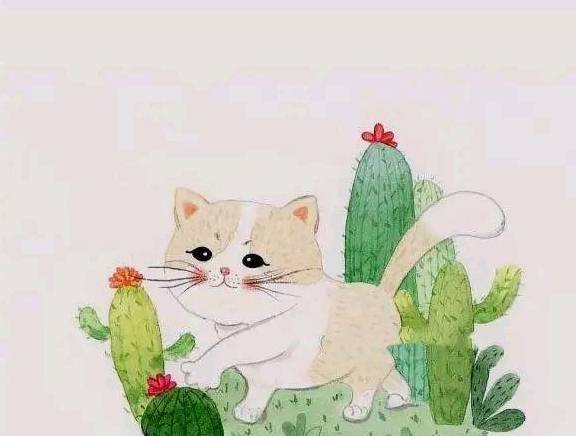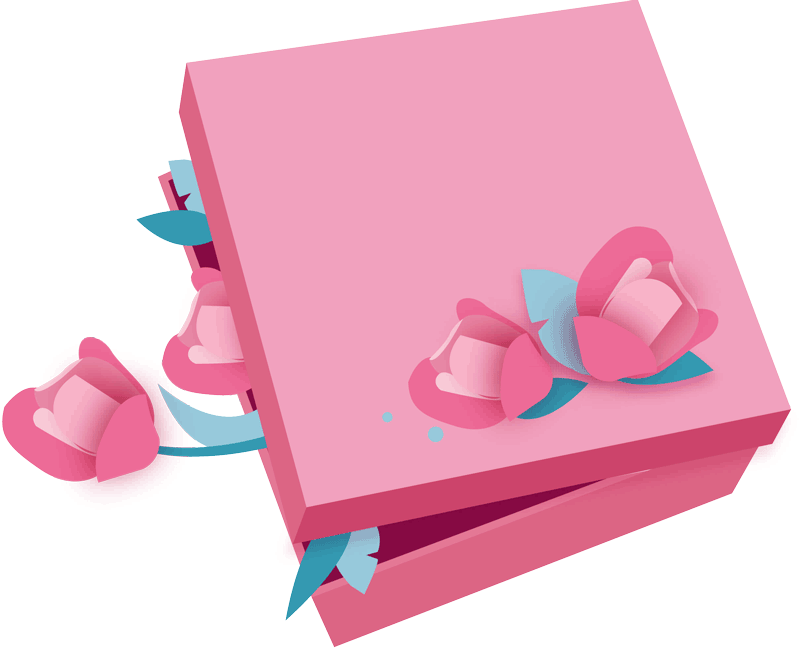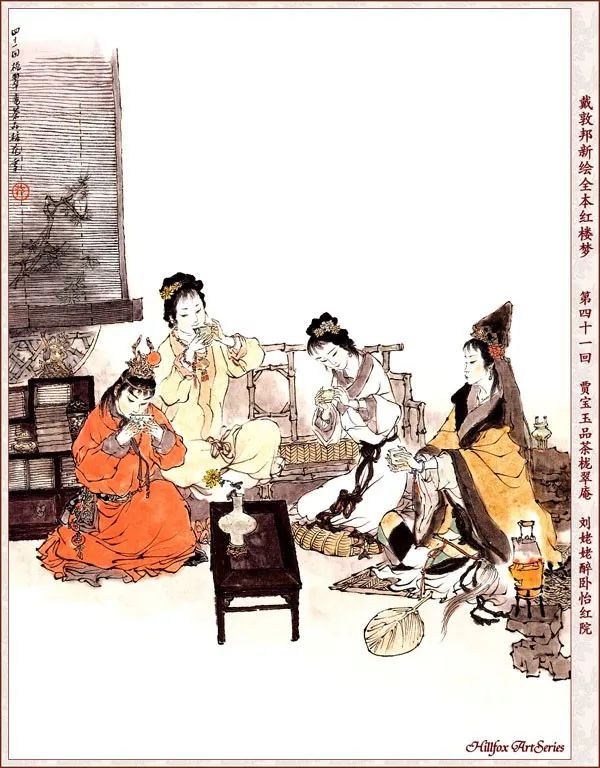未能安仁须学利仁
——以朱子对“知者利仁”的诠释为中心
作者简介丨杨根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原文载丨《道德与文明》,2018年06期。
摘要
历来对“知者利仁”诠释的分歧都比较大,主要有“借仁济私”和“以仁为利”两种诠释。朱子认为“利仁”是指: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针对自以为达到“安仁”境界的狂妄者以及为一己之私而放弃仁义的假儒者,朱子认为只有做到“利仁”,坚持做克己复礼工夫,才能有望达到安仁境界。朱子主张“未能安仁,须学利仁”,对当今志于儒学的人来说应当有所启发。
“安仁”“利仁”之说主要见于《论语里仁》和《礼记表记》,《论语里仁》第二章记载,“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历来解此章者,对“仁者安仁”一语较为推崇,对此语的诠释分歧也相对较小,而对“知(智)者利仁”一语的诠释则分歧较大,//www.58yuanyou.com见解深浅不一,不可不辨。
对“知者利仁”的不同诠释,主要是由于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不同:何为智者?“利仁”之“利”字究竟何义?在这两个问题中,问题更为关键,因为对“利仁”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界定了“何为智者”。在《论语》的诠释史上,对“利仁”之“利”字的理解不同,造成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诠释:第一种,将“利”字解为“利用”,作如此解的话,智者行仁,就是为了利用仁,从行仁之中获取私利(姑且称此说为“借仁济私”说);第二种,将“利”字训为“贪”,“贪,欲也”,即“欲得之”或“欲有之”之义,作如此解的话,“智者利仁”就应理解为智者想要得到仁德,智者的人生目标是成就仁德,“仁”对于智者来说不是谋利之手段,而是目的(姑且称此说为“以仁为利”说)。
持上述第一种诠释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皇侃的《疏》和邢昺的《疏》。梁皇侃《疏》云:“智者,谓识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见行仁者若于彼我皆利,则己行之;若于我有损,则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1]皇《疏》认为,智者行仁是因为他认识到行仁对他人和自己皆有利;如果对自己的利益有损害,则停止行仁。如果细究皇《疏》的这一诠释,我们可以看出,智者在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作为是否行仁的最终根据的同时,毕竟还是考虑到他人利益的,智者还不至于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所以,皇《疏》的这一诠释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但不管怎么说,皇《疏》终究还是将行仁看成手段,将获利看成目的。到了宋代邢昺的《疏》中,直接将一己之私利作为智者行仁的依据,智者成了“有智谋”者,行仁的动机就只是“贪利”。需要说明的是,皇侃的《疏》和邢昺的《疏》都是对《何晏集解》中王肃的注所作的疏解。王肃注云:“智者,知仁为美,故利而行之也。”依王肃,智者是因为“知仁为美”,所以才“利而行之”。王肃此注的关键应该是“知仁为美”,然而对“知仁为美”可以作两种不同的理解:智者认识到“仁”德可以带来外物之利,因此认为“仁”德是美的,而非以仁德本身为美;智者认识到仁德本身就是美的,以仁本身为利,成就仁德是智者的人生归属。基本上,以皇《疏》、邢《疏》为代表的对“利仁”的诠释应该是基于前一种理解。
持第二种诠释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朱子,其在《论语集注》中说:“利,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知者则利于仁而不易所守,盖虽VWHsjJOHg深浅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夺矣。”[2]在朱子之后,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和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对“利仁”的注解也属于第二种诠释。刘宝楠说:“‘安仁’者,心安于仁也。‘利仁’者,知仁为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则可久处约,长处乐。”[3]孙希旦说:“利仁者,真知仁之可好,而必欲得之者也。”[4]钱穆先生说:“利仁:知仁之可安,即知仁之为利。此处利字,乃欲有之之义……利仁者,心知仁之为利,思欲有之。”[5]将后三人的注解与朱《注》稍加比对,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对“利仁”的注解与朱《注》极其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将朱子看成第二种诠释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从朱子的注中我们可以看出,智者对仁德是“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并且能够“利于仁而不易所守”。这种诠释不仅仅与“借仁济私”说不同,而且在性质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在朱子看来,“利仁”不仅是成德之事,属于为己之学,而且还是道德修养中重要的一环。与此相反的是,在“借仁济私”说中,将“私利”置于“仁”之上,如此理解的话,智者显然与儒家的道德主张相背离。“借仁济私”说如果能够成为“知者利仁”的正解的话,那么智者在《论语》中的地位应该是极其卑微的。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论语》经常“仁”“智”对举,“智”和“仁”都属于德,《中庸》甚至称“智、仁、勇”为三“达德”。可见,《论语》对“智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仅从这一点来说,“借仁济私”这一诠释不可能成为“知者利仁”的正解。
然而问题是,朱子对“利仁”的注释不但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而且还遭受抨击。譬如,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不但认为皇《疏》较朱《注》为胜,而且对朱《注》所引的谢氏(上蔡先生)语极为不满。他说VWHsjJOHg:“此章圣人不过泛论,谢氏乃借此以贬抑圣门,真别有肺肠矣。朱子不察而误采之,可谓全书之玷。”[1](229)程氏所云“谢氏乃借此以贬抑圣门”,应该是指谢上蔡所说的“诸子虽有卓越之才,谓之见道不惑(笔者按:即智者)则可,然未免于利之也”一语。上蔡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门诸子虽有卓越之才,但只能属于“知者利仁”,尚未达到“仁者安仁”的境界。这在程树德看来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是赞同皇《疏》的。如果将孔门诸子看成“知者利仁”,也就是认为诸子“借仁济私”。然而,程树德似乎又想要维护朱子,说朱子“不察而误采之”。朱子果真是“不察而误采之”?以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判析疑似,辨别毫厘”(《四库提要》语)观之,程氏之说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子根本不能认同“借仁济私”那种诠释。不但如此,与那些重视“安仁”、轻视“利仁”的诠释不同,朱子本人十分看重“利仁”,朱子甚至不惜说程颐看“利仁”太浅。
那么,朱子为什么不能认同“借仁济私”那种诠释呢?他是如何理解“知者利仁”的呢?又是如何看待“利仁”与“安仁”两者关系的呢?以及对于志于仁德的学者来说,应该是学“安仁”还是学“利仁”呢?本文接下来将试图探究这些问题。而一旦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知者利仁”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朱子学。
一、“利仁”与“有所为而为”不同
朱子在诠释“利仁”时,首先明确指出其与“有所为而为”不同。以“有所为而为”来诠释“利仁”的人较为普遍,甚至程子也是如此。程子云:“‘知者利仁’,知者以仁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为之之类,皆是以为利也。”此语中的“欲有名而为之”可以理解成“有所为而为”,因为“欲有名”。朱子对此语评价道:“安仁利仁之说,程子发明亦切至矣,但若欲为而为之之类,看利仁者太浅矣。若徒为名而已,则是岂其真知仁之为利者,而亦何足以得为仁之利哉?”[6]在这里,朱子说“程子发明亦切至”应该是指“知者以仁为利而行之”以及“知者知仁为美,择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但是,朱子不能同意“欲有名而为之”之说。在朱子看来,如果“利仁”只是为名,不但没有真知仁之为利,也不足以得为仁之利,所以“欲有名而为之”看“利仁”太浅。此处朱子说“太浅”,恐怕乃是碍于师承关系,说得比较委婉。因为在朱子看来,“利仁”与“有所为而为”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朱子语类》记载:
晞逊问:“所谓利仁者,莫是南轩所谓‘有所为而为者’否?”
曰:“‘有所为而为’不是好底心,与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事,信手做将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说:‘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这只顺道理合做处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与上不同。”
又云:“有为而为之,正是说‘五霸假之也’之类。”[7]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朱子看来,“利仁”与“有所为而为”不同,“智者利仁”相当于“君子行法以俟命”,而“有所为而为”属于“五霸假之”之类。
“君子行法以俟命”一语出自《孟子尽心下》,朱子注曰:“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祸福有所不计,盖虽未至于自然(此处‘自然’指安仁———笔者按),而已非有所为而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此意也。”[2](373)在朱注中,“法”是天理之当然,而天理在人即是仁,所以“君子行之”就相当于“知者利仁”。依朱子,“利仁”虽然没有达到“安仁”的境界,但已经不是“有所为而为”了。“利仁”之意,乃与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相通。朱子对董子此语评价颇高,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义功利关不透耳。”[7](3263)显然,朱子认为“利仁”是“道义”一边事,而非“功利”一边事。也就是说,“利仁”的动机是成就“仁”德本身,是“好底心”。而“五霸假之”一语出自《孟子尽心上》,朱子对其注曰:“五霸则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2](358)既然“有所为而为”属于“五霸假之”之类,那么“有所为而为”就是指假借仁义之名,以满足个人之贪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才说“‘有所为而为’不是好底心”。
因此,“利仁”的动机是道义,而“有所为而为”的动机是私欲,二者不可相提并论。不但如此,朱子认为“有所为而为”即使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好事,也不能认可这种行为。这是因为“有所为而为”是假借仁义之名来满足个人私欲,仁义只是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表面上好事做得越多,最终造成的危害就越大。所以,朱子非常注重行仁的动机。朱子曰:“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识得假与利,只看真与不真,切与不切。”[7](1449)在朱子看来,判断“利仁”和“有所为而为”的标准就是要看行仁的动机是否真切。很明显,“有所为而为”的动机不真切,而“利仁”的动机是真切的。总之,在朱子看来,“利仁”与“有所为而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有所为而为”实际上就是前文所说的“借仁济私”,而“利仁”则是另外一回事。

二、“利仁”乃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
那么,“利仁”的动机是如何真切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来了解朱子是如何从正面诠释“利仁”的。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对“利仁”之“利”字注曰:“利,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如前文所述,此注中的“贪”字为“欲得之”之义。在朱子看来,智者之所以一定想要得到仁,是因为对仁“深知”“笃好”。那么,何为“深知”,何为“笃好”?以下分别述之。
朱子在诠释“利仁”时,首先强调对仁的“深知”。朱子云:
如所谓利仁者,是真个见得这仁爱这一箇物事好了,犹甘于刍豢而不甘于粗粝。若只是闻人说这个是好,自家也仿佛见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刍豢之悦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7](642)
在朱子看来,“利仁”是自己心里真切地体会到仁爱之好,犹如孟子之“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吿子上》),而不是听别人说好,自己也似乎觉得好。这就是朱子在《论语集注》中所说的“深知”之义,这种“深知”也就是“真知”。朱子云:“真知是知得真个如此,不只是听得人说,便唤作知。”[7](376)而在朱子的义理系统中,真知必能行。因此,如果能做到真正体会到仁,就必然会行仁。
何为“笃好”?在字面上,“笃好”的意思是十分爱好。朱子在解释《论语里仁》之“我未见好仁者”章时曾说:“好仁,恶不仁,皆利仁者之事。”[7](652)我们不难发现,在朱子看来,对仁的“笃好”应该是指《论语里仁》篇中的“好仁者,无以尚之”。朱子云:
盖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无以加之。[2](70)
“好仁者无以尚之”,只是将无以加之来说,此与“恶不仁”一段相对。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无以加此。若是说我好仁,又却好财、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须天下之物皆无以过之。[7](654)
“好仁者无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变易之者。“恶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恶之笃,而不使不仁之事加于己。此与“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皆是自己上事。非是专言好人之仁,恶他人之不仁也。[7](653)
在朱子看来,因为真知仁之可好,所以天下之物都不能超过仁。如果是真的好仁,就必须在心中将“仁”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财色等外物都在仁之下,而不能等量齐观。如若一个人说自己既好仁,同时也好财色等外物,而且对仁与外物是同等地爱,那么这在朱子看来并不是真的好仁。并且,朱子还强调好仁是自家事,如“好好色”。盖在朱子,仁是自家本有的事物,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所以好仁非好他人之仁,而是好自己本有之仁。可以说,对仁的笃好是建立在对自己心中本有之仁“真知”的基础之上。
基于以上对“真知”“笃好”的理解,朱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对仁真知、笃好,那么他就必然想要得到仁,也就必能行仁。这种“必能行仁”是真知、笃好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硬去做”(勉强而为)。朱子云:“吕氏所谓向慕勉强者,亦未及乎利仁也。以《中庸》达德、《表记》三仁之序考之可见矣。”[6](172)《礼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原由网礼记表记》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依据《礼记中庸》和《礼记表记》,“三仁之序”为“安仁”“利仁”和“强仁”,朱子以此认为“利仁”与“强仁”不同。
关于利仁与强仁之别,朱子云:
学而知者,有所不知,则学以知之,虽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虽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无蔽,得粹之多,而未能无杂,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学而未达,困心衡虑,而后知之者也;勉强而行者,不获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强矫而行之者也。此则昏蔽驳杂,天理几亡,久而后能反之者也。[6](82)
安、利、勉强,皆是真切,但有熟不熟耳。[7](1449)
在朱子看来,利仁与强仁之分别有二:一是气禀(气质之禀)不同,二是为学工夫之生熟不同。就气禀而言,利仁者虽然不如安仁者生知安行,但已经是禀清明之气较多、赋质较纯粹,天理小失,能够主动急切地通过“学以知之”以恢复人心本有之仁德;而强仁者所禀之气质昏蔽驳杂,天理几亡,只能通过“困学知之”,“勉力强矫而行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本心之明德。就工夫之生熟而言,利仁者工夫已经做到“真知其利而必行之”,工夫比较熟;而强仁者“学而未达”,“未知其利”,工夫不熟。而利仁与强仁在工夫上生熟不同的标准在于对自家本有之仁德是否“真知”,利仁者是真知仁之为美,而强仁者“学而未达”,没有达到真知,只能借助勇气勉强行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强仁”与“利仁”“安仁”一样,同属于成德之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朱子看来,“利仁”的真正内涵是: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此“必能行之”不是勉强而为,而是“真知”“笃好”的必然结果。在这当中,对仁德的“真知”是“利仁”的关键,只有真知才能笃好,只有真知才不会勉强而为。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理解朱子主张“下学穷理”工夫的原因之一在于达到对仁德的真知。从上面分析“利仁”与“强仁”的区别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利仁”是不如“安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利仁”与“安仁”加以比较,以便深化对“利仁”的理解。
三、安仁、利仁之异同
在分析安仁、利仁两者异同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朱子是如何诠释“仁者安仁”的。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对“仁者安仁”的解释是:“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2](69)。朱子这里所说的“无适不然”,是指仁者应物毫无差错,皆合义理。例如,朱子在《中庸》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语后注曰:“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2](18)其实,对于“安仁”的解释,朱子更欣赏的是谢上蔡之“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一语,认为“此句为‘仁者安仁’设”。也就是说,在朱子看来,“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是“仁者安仁”最好的解释。那么,朱子是如何理解“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的呢?朱子云:
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7](642)
才有私意,便间断了。所以要“克己复礼”,便是要克尽私意。原由网盖仁者洞然只是这一箇心。如一碗清水,才入些泥,有清处,有浊处。[7](644)
仁者温淳笃厚,义理自然俱足,不待思而为之,而所为自帖帖地皆是义理,所谓仁也。[7](643)
众所周知,在朱子的义理系统中,析心与理为二,主张“性即理”,反对陆九渊之“心即理”。但是在朱子诠释“仁者安仁”的这几段话中,朱子认为仁者之所以安仁,是因为仁者之心便是仁,此心与理浑然为一。既然心与理为一,仁者之心就无纤毫私意,尽是天理。因此,“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就是说仁者本心莹然,随心所欲,自然中理,没有一毫私意间隔此心之发用流行,表里如一。由此也可以看出,“仁者安仁”与孔子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所表达的道德境界相同。简言之,在朱子看来,仁者之所以安仁,最关键的原因是其心中没有任何私意。
现在我们来看朱子是如何理解“安仁”“利仁”之分别的,朱子云:
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带之忘腰,屦之忘足。利仁者是见仁为一物,就之则利,去之则害。[7](643)
“知者利仁”,未能无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无私意处是好,所以在这里千方百计要克去箇私意,这便是利仁。[7](642)
从第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安仁、利仁的区别在于安仁者“不知有仁”,而利仁者“见仁为一物”。何谓“不知有仁”?根据上文所述,安仁者之心与理浑然为一,所思所为皆合乎义理,所以“不知有仁”应该就是指朱子所说的“不待思而为之”,也就是自然而然,如带之忘腰、屦之忘足。也可以说,安仁者行仁是无意为之,因为安仁者本心之发用不会受到纤毫私意阻隔。而利仁者与此不同,利仁者是见仁为一物,因为利仁者已发之心未能与理合而为一,尚有私意在,只不过利仁者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行仁,千方百计地要克去私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朱子看来,克去私意并不是要抑制私意、使其不发作,而是要找到私意之病根,连根拔起。因此,安仁、利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安仁者心中毫无私意,利仁者胸中尚有私意。正因为如此,朱子特别欣赏谢上蔡所谓“安仁则一,利仁则二”一语,再三诵之[7](644)。也就是说,安仁者本心之发用没有私欲阻隔,一贯流行;而利仁者本心之发用受到私意阻隔,虽然利仁者禀清明之气较多、赋质较纯粹,天理小失,然而在朱子看来,只要有纤毫私意尚在,就需克己复礼的工夫。
在朱子看来,安仁、利仁虽然深浅不同,但是两者皆非外物所夺。安仁者自不必说,自然安于仁而不为外物所迁。利仁者虽然尚有私意阻隔本心之发用,然而由于其对仁德真知、笃好,所以在义理与私欲之间,能够取于义理而克去一己之私,随时随地做克己复礼工夫,自强不息,以期至于圣域。利仁者犹如颜子之箪瓢陋巷不改其乐,不像小人久处贫困则放溢为非,久处富贵则骄佚无礼,不取仁义,乃为“妾妇之道”。
四、未能安仁,须学利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安仁者浑然天理,安而行之,利仁者天理小失,尚须着以克己复礼之工夫。那么,从做工夫的角度看,朱子认为学者应当做安仁工夫,还是做利仁工夫呢?朱子云:“唯圣人自诚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诚,须是利仁。”[7](643)朱子这句话中的“自诚而明”与“自明而诚”出自《中庸》,其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朱子对其的注释为:“德无不实而明无不明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2](32)由此可以看出,在朱子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安仁,如果是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则须做利仁工夫。也就是说,安仁乃圣人之事,利仁乃学者之事。
然而问题是,从周敦颐开启的学做圣人的道学传统来看,我们为何不学圣人之安仁而学利仁呢?这是因为在朱子看来,圣人是生知安行。朱子云:
生而知者,生而神灵,不待教而于此无不知也;安而行者,安于义理,不待习而于此无所咈也。此人之禀气清明,赋质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丧者也。[6](82)
在舜则皆生而知之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2](294)
这就是说,圣人禀气清明,赋质纯粹,天理浑然,如舜天生就是仁义已根于心,所行皆从此出,安而行之,不待教而自能安仁。可是,圣人生知安行之资质乃为天赋,对于众人来说,气禀各有一偏,那该如何做呢?朱子云:
惟舜便由仁义行,他人须穷理,知其为仁为义,从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须是利仁。利仁岂是不好底!知仁之为利而行之。不然,则以人欲为利矣
圣人是人与法为一,己与天为一。学者是人未与法为一,己未与天为一,固须“行法以俟命”也。[7](1474)
很明显,依朱子,众人在资质上未能与仁为一,所以必须穷理,明辨何为天理、何为人欲,以达到对仁德真知、笃好而必行仁义。如若不然,则可能存在以人欲为利的危险。简言之,在朱子看来,学者“既未能安仁,亦须是利仁”。
事实上,朱子非常强调学者当学利仁,反对那种企图一蹴而就以达安仁境界。例如,朱子的学生主张学“由仁义行”(即安仁),朱子批评道:“此是江西之学(指陆九渊之心学———笔者按)。”因为在朱子看来,“圣人便自有圣人底事”[7](558),而“学者且只是做学者事”,工夫尚未纯熟,就不要对安仁之境界妄加猜测[7](558)。所以,朱子认同谢上蔡所说的“安仁者非颜闵以上不知此味”,即便是孔门德行排前两名的颜渊和闵子骞,尚且未到安仁处,其他人则相距更远。但是,在朱子看来,圣人与学者之间也不是说一定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圣人之生知安行不可学,然而学者如果不间断地做克己复礼的工夫,圣人地位则可学而至。工夫越熟,离圣人地位就越近,正如朱子所说:“圣贤是已熟底学者,学者是未熟底圣贤。”[7](825)所以,就做工夫而言,朱子认为要做利仁工夫,真切地做到以仁为利,而非以外物为利。至于安仁,朱子认为其为义精仁熟后的效验,着不得工夫。
要言之,朱子认为,学者只要尚有私意阻隔本心之发用,就须学利仁,而非学安仁。果真能做到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行之,虽未能完全达到圣人境界,但如果能达到颜回之“三月不违仁”的地位,已经是大段好了,而且在此地位仍然会努力地做克己复礼的工夫,圣人之安仁境界也是可以期待的。
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在诠释“安仁”与“利仁”时,显然非常重视“利仁”,这与很多思想家只重视“安仁”而轻视“利仁”不同。首先,“利仁”与“借仁济私”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利仁者的动机是志于仁,而“借仁济私”者的动机是一己之私欲。从道德领域看,“借仁济私”根本不属于道德行为,即便其在表面上做了一些仁义之事,因为在朱子看来其动机不良,是不好底心。其次,“利仁”的真正内涵是: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此“必能行之”不是勉强而为,而是“真知”“笃好”的必然结果。而要做到“利仁”,“真知”是关键,“真知”是“笃好”的基础,真知必能行仁。再次,通过对“安仁”“利仁”之异同的分析,我们知道,安仁者本心之发用没有私欲阻隔,一贯流行;而利仁者本心之发用受到私意阻隔。但是,利仁者虽然尚有私意阻隔本心之发用,然而由于其对仁德真知笃好,所以在义理与私欲之间,能够取于义理而克去己私,以期成就仁德。朱子将包括颜渊在内的孔门诸子看成未免“利仁”,并没有贬低诸子,因为利仁者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与安仁者一样皆非外物所能夺。最后,从为学工夫上看,朱子认为,对于志于仁德的学者来说,只要纤毫私意尚存,就须学利仁,做到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至于“安仁”,在朱子看来,对于气禀各有一偏的众人来说,“安仁”是工夫做到义精仁熟后的效验,“安仁”本身着不得工夫。
总而言之,从朱子的立场看,对于志于仁德的学者来说,只有真正做到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行之,不为功名富贵等外物所诱惑,才能有望达到安仁境界。然而,要真正做到“利仁”并不容易,朱子曾说:“今学者都不济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齐放倒了!”[7](650)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恐怕不仅仅是朱子当年的学者“不济事”。由此我们可以说,朱子主张“未能安仁、须学利仁”,可谓是用心良苦。清代李二曲先生在《四书反身录》中写的一段话与朱子之意较合,兹特录之以作结束语。其曰:“故吾人处困而学安仁,未可蹴几,须先学‘知者利仁’,时时见得内重外轻,不使贫窭动其心,他日必不至败身辱行,自蹈于乞燔穿窬也。吴康斋遇困窘无聊,便诵《明道先生行状》以自宽,其庶几‘智者利仁’欤!吾侪所宜师法。”[8]
参考文献
[1]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8.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69.
[3]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0.
[4]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01.
[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77.
[6]朱熹.四书或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72.
[7]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04:642.
[8]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442.
轮值主编 | 刘 梁 剑
编辑 | 宋 金 明 李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