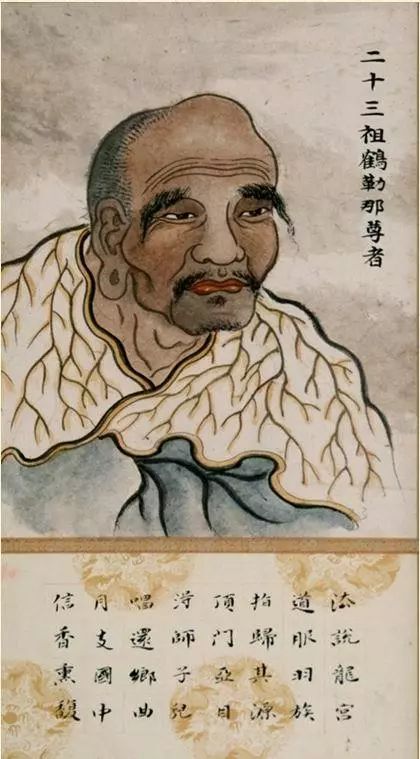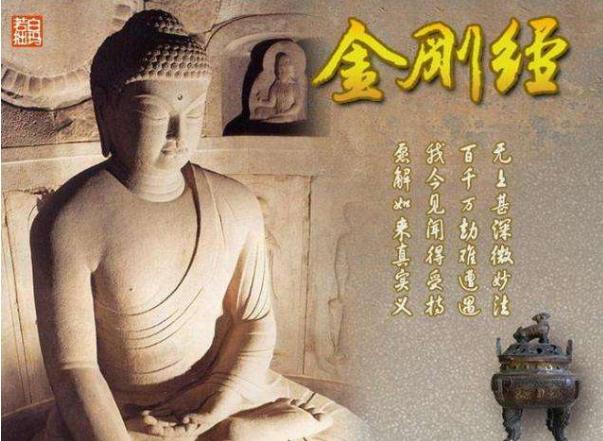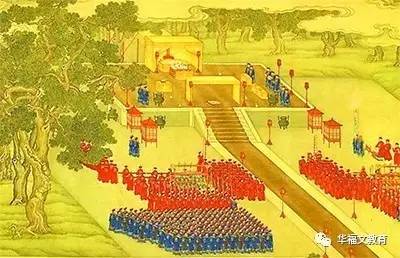术有专攻终生以之,学以致用家国情怀
——我的求学历程与治学体验

(朱士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一、几经拼博走上治学之路
1939年春,家父与家母在家乡湖北汉阳与荆州为日寇侵占后,就近投奔大后方,在当时的四川省丰都县(今属重庆市)生下我。不久又到战时陪都重庆,家父任职于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补给科,家母带我住在重庆南岸半山坡上一座民宅里。待我长到两三岁时,在日寇飞机对重庆持续滥施轰炸,白天夜间忙于躲警报钻防空洞的危难时刻,家母仍不忘对我进行启蒙教育,教我学“人、手、足、刀、尺”等汉字及当时通行的注音符号;及至满3岁,又送我去附近的民生公司幼稚园接受培育。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已进入民生公司子弟小学读一年级。在之后的几年国内战乱期间,全家随同父亲辗转迁徙于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重庆、成都等地。待到家父于1949年底在成都随机关起义后,旋即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学校接受培训,全家又自成都迁至重庆。1952年夏,因抗美援朝战争,国家财力紧张,无法安排家父等起义军人的工作,被资遣回家乡武汉市自谋职业,于是才回到武汉原籍生活。就是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我度过了少年时期;继重庆民生公司子弟小学后,又先后在南京四条巷国民中心小学、重庆中兴路凉亭子小学、成都川西实验小学、重庆川东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及重庆大学附属小学等6所学校读完了小学。幸亏父母对我上学事十分认真尽责,学校老师教书育人非常出色,加之我也勤奋上进,所以尽管长期生活在战乱环境里,小学学业未曾荒废。
1952年7月全家回到家乡武汉市,安家定居于汉阳区后,当年10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实验中学读初中;1955年7月初中毕业后,按当年政府就地上学政策,考回设于汉阳区的武汉市第三中学读高中,并于1958年7月毕业。中学6年虽然总体上处于和平环境里,但当时国内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与社会变革,如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及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城市里搞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及大跃进、灭四害运动,及至国外的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报告等等都时时对我们这些处于青年时期的中学生有所影响。但就我而言,虽也参与了上述不少社会政治运动,但始终将中学文理科各门功课及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刻苦努力加以学好。升入高二年级时已开始考虑考大学与选专业问题。当时受在高中生中广为流传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影响,决定学习理工科专业;特别是受苏联修建古比雪夫等大型水电站取得成功的影响,一心响往做一名水电工程师,在祖国的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上设计修建水电站,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然而到1958年春天,在距高考不到半年之际,因偶然间读到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一书,深深为他用通俗浅显的文字阐明了深邃奥秘的哲理所折服,突然感到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对人们的思想以及对社会与历史发展影响至巨,于是决定改学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为坚定这一决定,还特地向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同班女同学作了陈述。就这样到高考报名时,按当时每个考生可报9个志愿的规定,第一、二个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文系,第三、四志愿报的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与中文系;第五志愿报了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因看到招生简章上写明学习该专业后可参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及执行等工作,我感到这方面的工作意义重大,也填报了;第六、七志愿就是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之哲学系与中文系,第八、九志愿则为当时的湖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等两个系。但到8月中旬收到的却是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录取通知书。当时的心情是既高兴又困惑,因我报的中山大学志愿是文科经济地理专业,不知为何将我录至理科自然地理专业?当然那时改变专业已无可能,只能服从分配,于是在8月18日所写的一首诗中吟诵道:
考上中大实偶然,本非我的真志愿。
不知为何变专业,红榜揭晓已定案。
服从分配无多虑,适应需要少思迁。
看我高歌乘铁马,长驱直达珠江边。
就这样,我于1958年9月初,告别了父母与弟妹,乘火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奔驰,来到珠江边的康乐园,开始了为时5年的自然地理专业知识与工作技能的学习。
应该说,一进入中山大学校园,不仅对她美丽的校园十分钟情,更主要的是对中山先生为她手定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极为倾心。加之我就读的自然地理专业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中山大学(其前身名广东大学)成立不久,在几位德国教授协助下率先在国内建立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体制完备。除课堂教学外,还十分重视野外实习考察;这又极大地激发起我的兴趣与学习的主动性。在校期间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因为是开架式借书,一进入书库就在书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或浏览,或精读,每次都是满意而归。当时也曾赋诗一首,表述自己内心畅快而又满足的心情。诗曰:
每当我离开图书馆,
都好似一艘满载的船。
知识啊,像劲风吹动我心中的帆,
去追寻真理,去探索自然!
就在我循序渐进地学习自然地理专业各门课程,力争做一名合格的自然地理工作者时,1962年夏季进入大学四年级后的几件经历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途程。当年夏季系里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委托,组织一部分师生到海南岛西南部进行综合自然地理调查。因五年级同学面临毕业不便参加,就从我们班里选择了二十几名同学随同几位教师承担这项任务。我有幸被选中,考察中我在当时的东方县(今东方市)丘陵台地上见到一种耐干旱的草本植物——“飞机草”。它本有学名,因是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占领海南岛后用飞机播种方式引进的一种绿肥植物,所以群众呼之为“飞机草”。后这一俗名竟为植物学界所采用。这一现象十分新奇,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未作进一步的思考,但却有了自然地理环境也受人为活动影响而有所改变的朦胧认识。然而到当年秋季在野外考察结束回到康乐园进行资料整理与报告撰写时,我读到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侯仁之教授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上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文中阐述到:“人类的生活环境,经常在变化中”,“这种变化在人类历史时期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的活动不断加工于自然的结果,至于不因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虽然也有,但比较起来,确是非常微小的”。读后联想到琼西南丘陵台地上飞机草出现的缘由以及它的出现与繁衍导致的琼西南丘陵台地植物群落构成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使我深受启发。同时侯先生的上述理论观点还促使我结合4年来在自然地理专业方面的学习情况,进一步思考到,虽然自然地理学能使人们认识到当前我们生活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各要素之具体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如气候状况对动植物类型、河流水文状况、土壤性状等有很大影响,而植被也对气候状况有反向影响等等,并使人们借此以适应地理环境并进行建设改造。但因自然地理学只能使我们对地理环境之当前状况有所了解,而对它的过去状况以及由过去状况变为当前状况之过程与原因缺乏认识,对人为活动在地理理环境变化中的重大作用更缺乏具体深入的认识,所以就大为限制了人们自觉调控自身行为,促使人类社会更科学更富有远见地进行开发建设与改善自然环境的工作;有时甚至还会因举措失误造成重大的负面效果,使人类社会深受其害,这类事例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滥伐森林,滥垦草原等等。所以认为自然地理学也当吸纳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有关理论,既促使学科向纵深发展,也对国家建设作出更具实质意义的贡献。而机缘更为凑巧的是,到1963年春天,政府改变了保送大学毕业生读研究生的政策,由大学毕业生自主报考;同时还号召应届大学毕业生踊跃报名参加考试,“做勇攀科学高峰的登山队员”。但当时因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工作,所以报考的并不多。而我因对历史地理学从切身体验中有了较为具体深入的认识,而且日益产生了浓厚兴趣,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研究生。通过认真准备,顺利通过了有关课程考试,并于当年夏季毕业分配前夕收到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录取通知书,成为全班45位同学中唯一一名,中山大学一千多名毕业生中二十余名以及当年全国15万名大学毕业生中800余名研究生之一。于是在当年9月初如愿以偿进入燕园,成为我国新兴的历史地理学科的一名新兵。
到了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给我安排了多门课程,除与同年级研究生上英语课与自然辩证法课外,他每周一次亲自为我讲授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此外还让我学习了考古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等课程。1964年暑假带领我与另三位青年教师,组成历史地理小组,参加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组织的毛乌素沙地考察;1965年暑假又让我独自一人再赴毛乌素沙地城川地区考察。然而正当我兴趣浓郁地投身沙漠历史地理考察与研究中之时,1965年夏秋之交北大因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极左路线控制下,学校有关部门以我父亲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为理由,认为我不能留在北大深造,决定让我参加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就这样发电报让我从内蒙古鄂托克旗立即停止考察回到学校,于8月底离开北京分配至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工作。尽管文革后家父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得到平反,我也被北京大学补发了研究生毕业证书,但都无法补偿我被迫离开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岗位的损失。好在因为我对历史地理学打心眼里挚爱,所以在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工作期间,一方面认真投入有关水土保持专业调查研究工作,撰写了一些技术性调研报告,如陕北靖边县杨桥畔大队引水拉沙造田、神木县窝兔采当大队营建防风固沙农田防护林、绥德县郝家桥沟小流域治理、关中富平县赵老峪引洪淤灌、陕南宁强县飞播造林等等;但我同时也利用下乡工作之机,运用历史地理学理论,对陕北黄土高原与风沙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生产发展历程及其对环境变迁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考察与研究,仍然坚持进行历史地理学的探索思考。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后,原本学得都很不错的俄语与英语都丢生了,但历史地理学却没有荒废。正因为这样,所以1976年冬文革闹剧收场不久,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委托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在西安小寨工人文化宫举办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之审稿会,经侯仁之师向史先生推荐,我也有幸受邀参加了文革后全国历史地理学界这一盛会。在会上与侯师劫后久别重逢,更增师生之情。会议期间他几次谈及要我“专业归队”。当时想让我回家乡武汉工作,于是向他的燕京大学校友,时任武汉大学考古教研室的石泉教授举荐。石先生欣然允诺,武汉大学党委与人事部门也都研究同意;但因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坚持不放人,而且还将我妻子从武汉调到西安,解决了我们夫妻异地分居问题,所以未获成功。待到1979年夏,侯师来西安主持全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次学术会议时,即改向史念海先生推荐,史先生应允后,见省水土保持局仍不同意让我调离,即上书当时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端同志,经他批准,省人事厅下调令,省水土保持局才于1982年元月给我办了调至陕西师大的手续。这样时隔16年半,我才专业归队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当时我已年近43岁,人到中年,尽管这样我仍感到为时不晚,还大有可为。于是不顾子女尚幼,家庭生活条件艰困,重又捧起专业书籍,投入到我所热爱的历史地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这之后,在史先生指导与诸多校内外同行专家帮助下,通过发愤努力,于1986年晋升为副教授,1987年增列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被教育部批准增列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97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出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又被任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1999年10月28—30日,在山东省莒县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莒文化研讨会上,继首任会长史念海先生之后被选为中国古都学会会长;2000年出任陕西师范大学新组建并为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高校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2001年出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主编;2002年受命带领的学校历史地理学科团队,被教育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2004年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托,担任国家新修《清史》之《生态环境志》项目主持人,负责该志纂修工作;2006年9月于参加工作41年后,以67岁高龄退休;嗣后于2007年5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同年9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张萍教授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获评为2007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从前述1982年春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实现了专业归队以来二、三十年间一路走来,工作似乎顺风顺水,十分顺利;但其间实包含了不断的进取拼搏。为了补上被躭误的青春年华,赶上学科进展的步伐,付出了比常态情况下要多许多的精力与时间,且不能稍有懈怠。
在我的求学、治学历程中,尽管所选之专业方向有过变化,然而在报考研究生时所选定的历史地理学专业,却是我接受了五年自然地理学专业学习,在此基础上通过工作实践,深刻地接受了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的启迪与感召,由衷地感受到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功效,因而选定了这门学科作为我人生最终归宿,且终生以之,不论在自己的人生途程中遭遇到什么崎岖曲折,都孜孜以求,甘愿为之奉献出毕生的精力。
回顾我从高中时期一个懵懵懂懂,不谙世事,头脑中充满飘浮不定的种种人生理想与追求的毛头小子,到考中研究生以来选定了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且心无旁鹜不断追求的历程,我总结出以下三点具体体验,或感悟。即:
其一,选择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主攻方向,尽管家庭、学校与社会都会有影响,但最终只有经本人深思熟虑后选定的专业才是自己的真爱,并愿为之自觉自愿地作出持续不断地努力;才不会仅仅是为“稻粮谋”去从事某个谋生的职业,才会充满激情与灵感,身心愉快地投入其中,并有所成就。
其二,选择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主攻方向,尽管个人的兴趣爱好会起相当大的作用,但还不能仅凭个人兴趣爱好,还必须理性关注这一专业研究的主体内容与当代社会发展之关系,确立自己的专业主攻方向在其中所能作出的努力与贡献,以便能从中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CSGwroNhO生抱负。如我在报考大学时所选专业,最初想报考理工科专业,具体选择水电专业,其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后改为哲学、文学,它们对社会发展与人们精神世界的广泛深入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至于我还选定的经济地理以及后来学习的自然地理,它们对国家建设的具体指导作用,更是世所认定的;到最后我投身于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因为它能大为丰富地理科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理论与研究内容,还因为它能从人类历史时期人为活动与环境变迁相互关系中系统深入揭示人地关系规律,给当今人们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使我对历史地理学兴趣倍增,因而最终选定它作为终身致力的专业研究方向。
其三,选择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方向要在求学与工作历程中善于抓住机遇,实现人生途程上的重大飞跃。即以我之亲身经历而言,1963年春季大学本科毕业前国家首次公开招考研究生,当时因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包分配政策,所以同届毕业同学对报考研究生大多不积极。因不考研究生还可早日参加工作;考上研究生,反而要多当三年学生。我所在班级有45名同学,仅我与另一同学报名参加考试;最后我考入北京大学读开究生,那位同学虽未考上,却也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而这次报考研究生对我走上历史地理学研究道路确是一次十分难得的良机。如果我不考,根据我之家庭出身与我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多半会分配至某地某所中学任教;虽有职业,但并非我衷心追求响往的工作。所以对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当年我是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考试,根本不考虑北京大学地理专业应届毕业生亲聆过侯仁之先生教诲所具有的竞争实力,以及当年一个导师一般只招一名研究生的严峻现实,只专注于自己认真准备,奋力拼搏。最终取得成功,进入了我国历史地理学之学术殿堂,为实现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追求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所以有哲人说,人世间的机会诚然不少,但却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只有我们在专业追求上成为了一个有心人,自会捕捉到擦身而过的种种机会,以之促成我们在专业研究上的转轨与跃升。
二、我的三点治学体验
从我1963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师从侯仁之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以来,从学习到从事教学、科研,在我国这一新兴学科领域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其间虽自1965年秋至1981年底有将近17年时间我一度离开了历史地理学专业工作岗位,对我从事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仍时时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观察思考相关问题,也有相当的弥补。总结五十余年来总的治学体验,可以用“遵师循道,传承创新”八个字来概括。
首先我要谈及的是在我五十余年的求学治学生涯中,我有幸得到多位名师的指导,助我走上学术坦途。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位:
第一位当然是我研究生导师侯仁之院士(1911.12.6—2013.10.22)。他是我走进历史地理学学术领域的引路人。他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最主要的创建者,他创立的学科理论以及他的学术实践,他在治学上的开创的精神、开扩的视野、开放的胸襟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影响,令我终生受益。
第二位是辛树帜先生(1894.8.8—1977.10.28)。辛老祖籍湖南省临澧//www.58yuanyou.com县,民国时期先后创办了西北农学院与兰州大学。与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重要创建者顾颉刚先生关系十分亲密。共和国建立后再次出任西北农学院院长。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文革后期从“牛棚”中放出后,得悉老伴康成懿女士不堪受辱愤然自杀身亡的噩耗,竟不因这一家庭悲剧而消沉,反而化悲痛为力量,倡导编著《中国水土保持学》一书,深入总结我国历史上水土保持理论观念与技术经验,推动农村治山治水治田工作。我当时任职的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应辛老要求派我前往西农协助辛老组织编著该书。1976年夏,他还不顾已82岁高龄,坚持带队赴南方川、滇、桂、湘、沪、鄂等6省市进行实地考察。当年书稿编成后因感到所撰内容理论高度不够,毅然将书名由《中国水土保持学》改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后由农业出版社在他辞世后于1982年出版。在辛老身边工作的3年多时间,他除安排我到设于西农图书馆中之古农学研究室工作,并指导我阅读室中收藏的史籍与古农学专著外;还常请我到他家吃晚餐,在进餐中与晚餐后散步时对我畅述他的学界见闻和治学思想。既补上了我在北大两年学习期间未能多读史籍的不足,又在治学理念上获得新的教益。因有辛老的尽心培育,我得以在农史、林史与水利史等领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并取得一批成果。大为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丰富了我的专业素养。
第三位则是史念海先生(1912.6.24—2001.3.27)。史先生与侯先生一样,同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重要创建者顾颉刚先生及谭其骧院士高足,抗战胜利后曾被辛老聘为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代主任,1954年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并长期兼系主任。
自1976年冬西安召开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审稿会上史先生见到我后,会后他即对我十分关心,曾几次骑自行车由陕师大至城内西一路省水土保持局看望我;并多次通知我参加在陕师大举行的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后又应侯仁之先生之请求,亲自出面给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马文瑞同志写信,通过行政措施将我自省水土保持局调进陕西师大。
1982年1月我调进陕师大后直至史先生辞世,20年间,我在史先生身边工作。一方面史先生不断给我出题目,交任务,让我在历史地理学术领域经受锻炼,顺利成长;另一方面,耳濡目染,我从史先生身上也看到他勤于治学,勇于开拓,谦虚严谨,不耻下问的崇高精神,令我感佩,促我学习。
调入陕师大30余年间,正是在史先生带领与督促下,我参加了历史地理学领域几项大的学术工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编绘及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在新的21世纪里,我又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托,主持了《清史生态环境志》的编撰工作。始终居于历史地理学之学术活动的主流队伍中。
还应特别提及的是,我调入陕师大后,史先生不仅支持鼓励我继续从事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还直接敦促我参加了中国古都学研究,为我的历史地理学术研究打开了又一个广阔的天地。因而自我1982年初调入陕师大后之第2年,即1983年9月我在陕师大参加中国古都学会成立大会与首届学术研讨会后,30余年来除2011年一年外,参加了中国古都学会历年之学术研讨活动。从而在中国古都学以及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史学等领域也做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作出了一些贡献。
以上三位先生均是曾较长时间直接对我进行过培育的老师;
除他们外,还有好几位,如顾颉刚、谭其骧、陈桥驿(浙江大学教授)、石泉(武汉大学教授)、曾昭璇(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润田(河南大学教授)等先生,他们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对我均产生过教育启示作用,所以我也都奉他们为师,同时也从他们身上获得教益。
同时我还应该谈到的是,对老师我当然是十分敬重的,但对他们的某些学术观点我也不盲从。例如对侯仁之师。1965年夏我按他的安排独身一人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城川公社一带进行考察后,发现他在1965年春发表在《地理》月刊当年第1期上的《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一文中将城川古城定为唐代的旧宥州城是错误的,于是在结束考察后写的考察报告《对城川地区湖泊古今变迁的初步探讨》中明确予以指出。令人没想到的是,我给侯师交了该报告后即于8月底离开北大,第二年即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但在过了将近八年后的1972年,侯师在刚结束了他在江西鄱阳湖滨鲤鱼洲农场的劳动回到北京后,应《文物》编辑部约请撰写的文革爆发后第一篇学术论文《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中就坦然接受了我的批评,承认了他对城川古城定名是错误的,接受了我将城川古城所定的是唐元和十五年(820年)以后的新宥州城的见解。当我读到他给我寄来的刊载有该文的《文物》1973年第1期有关内容时,内心感到极大的震撼!对仁之师的开放的胸襟与恢弘的气势更为钦敬!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师生间建立在尊重真理基础上的互相敬爱之情是多么的珍贵!
至于具体的治学体验则有以下三点:
其一,认真学习深刻把握学科之基本理论,以之指导自己的治学实践,并尽力为丰富发展学科理论作出贡献。
认真学习并深刻把握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学科理论是治学之本,也是推动自己从事该门学科之学术研究的动力源泉。
就历史地理学之学科理论而言,其基本理论就是“人地关系”学说。
关于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学说这一基本理论,我的研究生导师侯仁之院士作为这一基本理论的奠基者曾作过精辟的阐释。早在上世纪60年初代,他在那篇著名的论文《历史地理学刍议》中就具体论述到:
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
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根本论点,就是说人类的生活环境,经常在变化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属于自然的景观如此,属于人为的景观更不例外。……而在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缔造经营,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周围地理的变化,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那是非常微小的。
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
由于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在指引我走上了历史地理学治学之路,并在有了一定理论素养之后,我就加以发挥运用,还努力做了一些传承创新工作。这不仅体现在自1965年以来做的科研工作与所写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中,还体现在我将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所作的阐释与推广工作方面。如我写的下列论文:
《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1999年3月;该文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99年第6期全文转载;还为《新华文摘》1999年第6期收入“报刊文章篇目辑览”。
《探析环境变化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之关系,推动古都名城研究的深入发展》,《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5卷第1期,2006年3月。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建设刍议》,《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Vol.39 NO.2,2009年4月15日;后又收入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2010年2月15日。
《历史地理学中的“时空交织”观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20日,A05版。
上述文论都是我在学习、把握了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之后,力图在历史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与区域历史地理学、流域历史地理学之理论建设上有所建树;有的则是遵循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力图对自然地理学、中国农史、城市史、环境史以及流域文明史研究有所助益。
例如:
在对历史时期某个区域或某个城市之地理环境进行研究方面,我就提出分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两个层次进行具体研究阐述的见解;
在对历史时期某个区域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方面,提出了环境变迁是一个“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念;
在对历史时期都邑与城市进行研究方面,提出了“环境与文化”的理论观点。
对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的学习与探求,与我之学术研治工作始终相伴随。由理论指导治学实践;又通过治学实践,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并对丰富深化历史地理学理论有所建树。
对学科理论从学习领会到运用建构,是与治学生涯相始终的长期过程。这是我第一个治学体验。
其二,洞悉学科之学术发展史,力求融入本学科之主流队伍,进入学术研究的前列。
了解、熟悉本学科之学术发展史,是治学之起点。只有全面系统地掌握了本学科,特别是自己从事研究的学科方向迄今之进展状况与取得的具体成果及其价值意义,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登上一个有着扎实基础的并达致学术前沿的起点,也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所传承创新,推动学科发展。为此就要时时振奋精神,关注学科发展。在这方面我就牢记辛树帜先生的教导,注意及时阅读本学科有关期刊上发表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努力融入本学科之主流队伍。为此,对我国历史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我是每次必到,每会也必定提交论文,与同行专家近距离交流切磋,亲历本学科当代之发展历程。
通过熟悉把握本学科之学科发展史,既使我能具体深入认识到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与所取得的成就,以便承继发扬他们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又可使自己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依托他们打下的坚实基础,目标明确地进行创新性研究,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在其中可说是个受益者,当然也成就了我作为这一学科主流队伍中的一员干将。这是我的第二个治学体验。
其三,深入认识学科之性质特点,从而促使自己在学术研究中充分利用学科性质、特点所具之优势与潜力,保持学术上的敏锐性与执着追求的精神,永葆学术青春。
当今学术园地中林林总总的诸多学科,由于它们各自的学科门类的归属与研究对象、任务的不同,其学科之性质、特点也各异。就现代历史地理学之学科性质、特点而言,究其实质,我将之归纳为:
文理兼容,史地结合,时空交织,古今贯通。
很显然上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原由网学科性质与特点,既为我们展示了这门学科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也为我们提示了一些必须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新的研究方法。如“文理兼容原由网”、“史地结合”所禀赋的多学科综合思维与交叉研究理念;“时空交织”所蕴涵的对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之纵向变迁历程与横向空间分异进行立体观察思考的观念;“古今贯通”所要求的立足古代,观照当今的穿越式治学www.58yuanyou.com要旨等。无不时时处处促使我们,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推动历史地理学科向纵深与新锐境界发展。
正是因为我对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及其学科发展史以及学科性质、特点认识与把握逐步加深,我对这门学科也更为热爱,以致将之与自己的生活以及生命融合为一体,保持了旺盛的兴趣与敏锐性以及一种执着的追求精神。不仅在看书刊报纸时,凡涉及生态环境变迁与历史文化方面的讯息,都会引起关注,如近年来出现的“大历史”、“人类世”等新概念等;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养成了观察周围环境,探寻其变化痕迹的习惯。如在外出乘飞机坐火车时均要选坐靠窗的座位等。这显然与自己原学自然地理学,后又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这一专业有关,是一种职业性特征。早期还曾一度希望在去县、乡出差及在野外考察中,在岩石及地层中找到古代的砖头瓦块以及某些文物古迹,甚至还想发现一个古人类头盖骨;后则转移到对某些现象、事物进行学术性思考上。例如2011年5月下旬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院举办的“纪念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期间,我抽空补看了上海世博会闭幕后保留下来的中国馆。一走进大厅迎面墙上霓虹灯打出的“城头山——中国最早的城市”大幅标语立即引起我的注意与质疑。几经考虑,返家后即写成《城头山并非中国最早的城市》一文,后发给《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该报于2011年8月25日刊登在第5版上。同时在该文中,还在指出城头山古城址作为新石器时代之古城址,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因此不能作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后,又根据我所确立的古代城市之定义与条件,明确指出我国最早的城市应是距今三千余年的西周丰镐。
很显然,通过深入认识学科的性质特点,保持学术上的敏锐性与挚着追求的精神,是一种在学术上充满自信与自觉的表现;也是促使我们在学术上保持旺盛的活力,开展创新性研究的一种优良品质。这是我第三个治学体验。
三、我的三个梦
(一)关于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成为一级学科的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至今在国内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史念海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三大历史地理学术重镇,也即学界所盛传的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足鼎立”格局;然而同时又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太原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安文理学院、郑州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所陆续建立了研究机构,或拥有了颇具实力的专业研究队伍,实己形成了群星闪烁众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在2011年之历史学学科体系调整中,在世界史与考古学由原历史学之二级学科升格为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的一级学科后,原历史学留下的6个二级学科合并精减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与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学等4个二级学科,共同组建为中国历史学。这充分表明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现代新兴学科,经过数十年发展,已成为在现代学术园地里扎牢了根基,在其众多分支领域均取得显著成果,并对多门相关学科产生了促进作用,还在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效应的一门显学。
所以我的第一个梦,就是希望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继续有新的更大的发展,继世界史与考古学之后升格为一级学科。
(二)关于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科继续获得发展的梦
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科在史念海先生的长期努力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由史先生自谦所说的“小国寡民”,发展成为国内历史地理学三大研究重镇之一,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院鼎足而立。面对当前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均重视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科还当在原有基础上作出更大努力,不仅使其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地位更形稳固,还应使其学术成果更加丰硕,学术影响更为广泛。这是我第二个梦。
(三)关于我个人还想在有生之年再推出几本学术专著的梦
目前我个人在学术专著撰著方面已有三部与相关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其中之《中国古都学》一书,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另有与蓝勇教授、史红帅博士合著的《清代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一书也与福建人民出版社谈定。这都要在今后几年内陆续完成。除此之外,我还想撰写一部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方面的专著,将我多年来在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求索探寻方面的所思所得写进去。这就是我的第三个梦。虽然说好事多磨,但我真希望好梦成真!
2016年4月30日
微刊发布:每周日晚发布最新一期《微享周刊》,敬请留意微信提醒。
查阅往期:回复对应期号(阿拉伯数字)即可获取相应微刊。如输入数字【132】,将会收到第132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