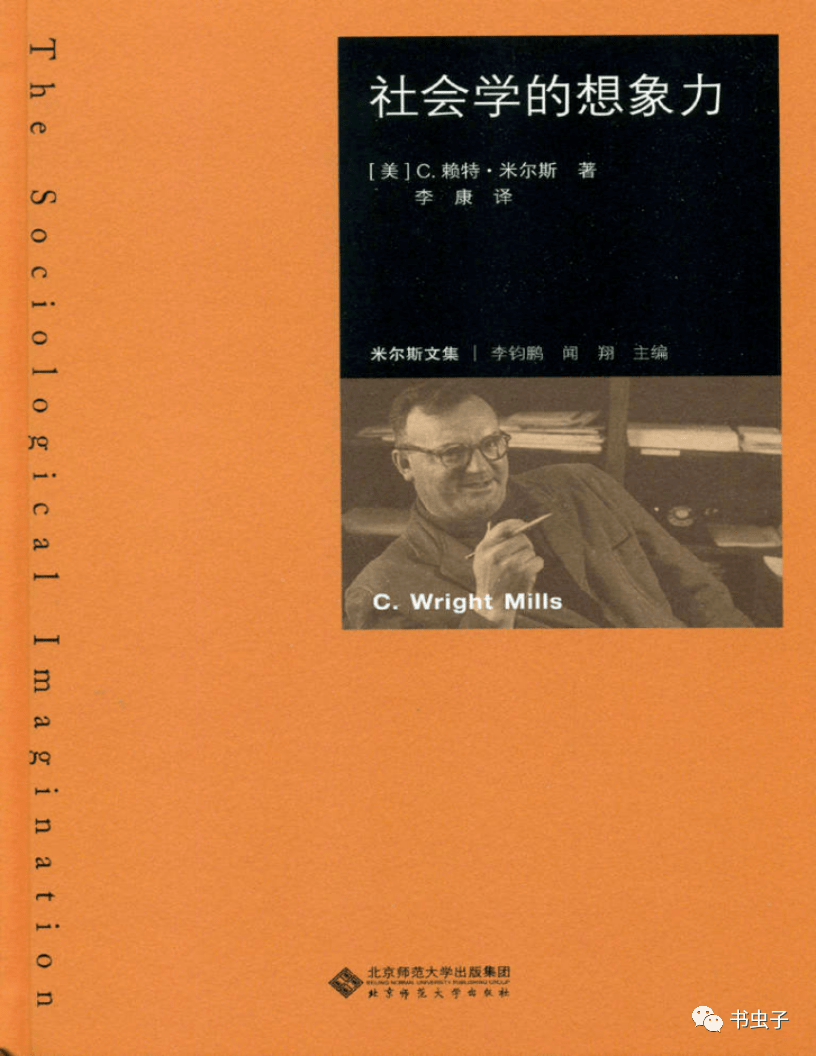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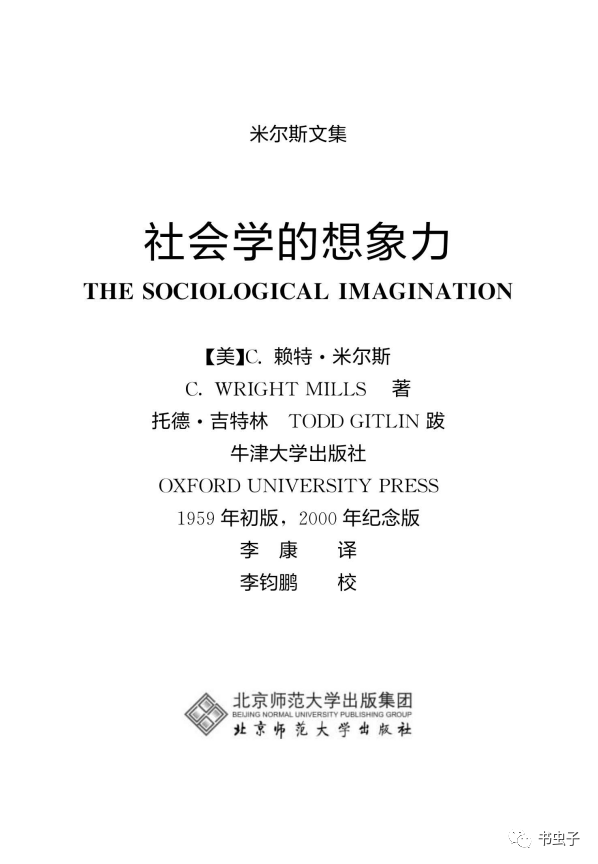
总序
1961年,在一篇向英国学界介绍美国社会学的论文中,30来岁却已是学界翘楚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梅尔瑟(Neil Smelser)以轻蔑的语气对C. 赖特米尔斯做出如是评价:“[米尔斯先生]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界无足轻重,虽然其著作在学术圈外颇为畅销,并在某些政治圈子里广为传阅。……由于占据了大众和商业媒体的重要发言平台,他影响了圈外人士对社会学的印象。他是在美国头号评论媒体《纽约时报书评》上对学界同行做出最多点评的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和斯梅尔瑟显然未能预见米尔斯对社会学的持久影响力。时至今日,米尔斯已成为社会学史上的传奇人物。1997年,国际社会学会选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部社会学著作,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高居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
米尔斯去世已超过半个世纪,当代中国社会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更是天差地别。我们今天读米尔斯,不在于书中的历史细节和政策是非,而在于他迫使我们反思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学家应如何想象?
首先,社会学家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必须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他并不主张学者抛开研究,以社会活动为业,而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为审美而审美的研究理念,反对狭隘的经验研究与科学主义。在他看来,社会学的技艺在于转译(translation)和赋权(empowerment)。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www.58yuanyou.com可能真正得到改善。米尔斯一方面炮轰空中楼阁的宏大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反对研究方法凌驾于实质议题之上的经验主义。时过境迁,米尔斯所批判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再看中国,社会学重建30多年以来,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从理论到方法,从后现代到大数据,我们对西方学术前沿已不再陌生。然而,我们是不是让术语和数据掩盖了事实本身?有没有忘了自己投身学术最初的感动?社会总体结构如何?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如何?这个社会中的获利者是谁?米尔斯敦促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正面回答。
其次,社会学研究不可脱离历史维度。对于马克思和韦伯等奠基人来说,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无泾渭分明的边界,他们的研究既是横向的结构剖析,也是纵向的历史叙事。但随着行为主义和量化分析的崛起,历史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初开始分家;历史学家对社会学家提炼一般化理论的尝试不屑一顾,社会学家则将历史学家视为提供史料的体力劳动者。米尔斯对这一现象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随着历史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兴起,这一现象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未得到真正的有机融合。如果我们遵循米尔斯的建议,历史社会学就不是社会学的分支领域,而是一切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历史社会学不是研究历史的社会学,而是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学;它将时序性(temporality)置于核心地位,强调因果关系在时间上的异质性。具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必然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结构是历史事件的产物。以转型期的中国为例,我们所处的社会和面临的社会现象从何而来,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社会是什么关系,传统社会、转型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何联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最后,社会学研究必须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体验。米尔斯并不主张大而无当的无病呻吟,而强调“大”和“小”的辩证关系。在分析权力精英、核武器这些时代的大问题时,研究者必须学会利用个人体验。从小镇到大城市,从务农到白领,经典之作《白领》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他本人的人生经历。对于未来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建议是:先反思你的个人经历,再把个人经历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所谓“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不仅回避了学者应有的社会担当,更抽离了学术灵感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个研究者对其所做的研究并无亲身体验,甚至没有个人兴趣,他又怎么能指望吸引甚至影响读者呢?对于中国的社会学者来说,我们最缺乏的并非事实,我们的普查和抽样数据已经不少;我们缺乏的是由小而大,大中见小的社会学想象力。
2016年是米尔斯诞辰100周年,我们推出这套译丛,既是向这位社会学巨人的献礼,也是社会学想象力的真诚邀约。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理应感到庆幸,因为这个转型的大时代是学术研究和公共关怀相互促进的难得机遇。我们任重道远,但满怀期待。
李钧鹏 闻翔2016年1月17日
献给哈维(Harvey)与贝蒂(Bette)
第一章 承诺
现如今,人们往往觉得,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在日常世界里,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克服这些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还颇有道理:普通人直接意识到什么,又会努力做什么,都囿于自己生活其间的私人圈子。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力量,都受限于工作、家庭、邻里那一亩三分地。而在别的情境下,他们的行止只能透过别人来感受,自己始终是个旁观者。对于超出他们切身所处的那些抱负和威胁,他们越是有所意识,无论这意识多么模糊,似乎就会感到陷得越深。
而支撑着这种陷阱感的,正是全世界各个社会的结构本身所发生的那些看似非个人性的变迁。当代历史的诸般史实,也正是芸芸众生胜负成败的故事。随着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农民成了工人,而封建领主则被清除或成为商人;随着各个阶级的起伏兴衰,个人找到了岗位或丢了饭碗;随着投资回报的涨跌,人也会追加投资或宣告破产。战事一开,保险推销商扛起了火箭筒,商店员工操作起了雷达,妻子独自在家过日子,孩子的成长也没有了父亲的陪伴。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社会的历史,只有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对其有所体会。
不过,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
当然,这也不足为奇。有那么多人如此彻底、如此迅疾地遭遇如此天翻地覆的变迁,那这是什么样的时代?而美国人之所以不了解这样的剧变,正如其他社会的众生男女所了解的那样,是因为一些正迅速变成“仅仅只是历史”的史实。如今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置身于这个时代的这个舞台,仅仅经过一代人的工夫,人类的六分之一就从完全的封建落后状况,转变成现代、发达却又令人满怀忧惧的状况。政治上的殖民地获得了解放,但新型的、不那么显见的帝国主义形式却开始扎根。革命爆发了,人们却感受到新型权威的严密掌控。极权主义社会兴起了,然后又被彻底摧垮,或者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获成功。资本主义经历了200年的上升趋势,如今看来,只是让社会成为某种工业机器的一种方式。抱持了200年的企盼,人类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获得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欠发达世界,到处都能看到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摧毁,朦朦胧胧的期待化作了迫不及待的要求。而在高度发达的世界,到处都能看到种种权威手段和暴力手段在范围上变成了总体性的手段,在形式上也变得具有科层性。人性本身现在就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是哪一极的超级大国,都以惊人的协调能力和庞大的规模,竭力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今,历史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让人们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基于往昔珍视的价值找寻方向。往昔珍视的是些什么价值?即使在尚未陷入恐慌的时候,人们也常常感到,老派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已经瓦解,新的萌芽却还暧昧不清,从而导致了道德上的阻障。普通人骤然面对那些更广阔的世界时,自觉无力应对;他们无法理解所处的时代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他们出于自我防御,在道德上越来越麻木,试图彻底成为私己的人,这些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逐渐感到坠入陷阱,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他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信息。在这个“事实的时代”,信息往往主宰了他们的注意力,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尽管他们获得这些技能的努力往往耗尽了本来就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
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可以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
这种想象力的第一项成果,即体现它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这个教益往往会是痛苦的一课,但又常常让人回味无穷。究竟是坚毅卓绝还是自甘堕落,是沉郁痛苦还是轻松欢快,是乐享肆意放纵的快活还是品尝理性思考的醇美,对于人的能力的这些极限,我们并不知道。但如今我们开始明白,所谓“人性”的极端,其实天差地别,令人惊惧。我们开始明白,无论是哪一代人、哪一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社会当中;他活出了一场人生,而这场人生又是在某个历史序列中演绎出来的。话说回来,就算他是由社会塑造的,被其历史洪流裹挟推搡而行,单凭他活着这桩事实,他就为这个社会的形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份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而经典社会分析家的标志就是接受这一任务和承诺。无论是言辞夸张、絮叨啰唆、无所不写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还是风度优雅、寻根究底、善良正直的E.A. 罗斯(E.A. Rose),无论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还是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抑或是敏感纠结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都具有这一特征。卡尔马克思之所以在智识上秀出群伦,根本上在于这一品质;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之所以洞见犀利、讽才卓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所以能从多种角度构建现实,关键皆在于这一品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深刻与明晰概源于此,W. E. H. 莱基(W. E. H. Lecky)的心理学视野同样建基于此。当代有关人和社会的研究,精华的标志正在于这一品质。
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不管经典社会分析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无论他们考察的社会现实多么局促或宽广,只要他们充满想象力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承诺,都会坚持不懈地追问三组问题:
(1)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彼此如何关联?它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何分别?在其内部,任一具体特征对该社会的维系和变迁具有什么意义?
(2)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是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着它不断变迁?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它居于什么位置,又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任一具体特征,是如何影响了它所属的历史时期,又是如何受后者影响的?至于这一历史时期,它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它与其他时期有何差别?它塑造历史的方式有着怎样的特色?
(3)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男人和女人的主流类型一般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趋势如何?他们是怎样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或被压迫,又是怎样变得敏感或迟钝的?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我们观察到的行为和性格中,揭示出了哪些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人性”有着怎样的意义?
无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强权大国,还是一种意境、一户家庭、一所监狱、一则教义,一流的社会分析家都要追问这些问题。它们是有关社会中的人的经典研究的学术支点,是任何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头脑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因为所谓想象力,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例如,从政治视角转向心理视角,从对单个家庭的考察转向对全球各国预算的比较评估,从神学院转向军事机构,从石油工业转向当代诗坛。这种能力上及最为遥远、最非人化的转型,下至有关人的自我的最私密的特征,并且还能考察这两端之间的关系。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应始终蕴含着一种冲动,要去探知置身于这个社会、这个时期,并被赋予其品质和存在的个体,在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上具有什么意义。
综上诸因,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人们现在可以期望把握世事进展,理解自身遭遇,并视之为人生与历史在社会中的相互交织的细小节点。当下的人在看待自己时,就算不是作为永远的陌生人,至少也会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这种立场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人们能深刻认识到社会的相互依存性,认识到历史的转型力量。而这种自觉意识最富收益的形式,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这种想象力,原本心智活动范围狭隘的人往往开始感到,自己仿佛在一座本该熟悉的房子里突然惊醒。无论正确与否,他们往往开始觉得,自己现在可以得出充分的概括、统合的评估、全面的定向。过去显得理据充分的决定,现在来看,似乎成了无法解释的糊涂脑袋的产物。他们感受惊奇的能力重焕生机。他们获得了新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价值的重估。简言之,他们通过冷静的反思和敏锐的感受,认识到了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
二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最富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这种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社会科学中所有经典研究的共有特征。
困扰发生在个人的性格当中,发生在他与别人的直接关系当中;它们必然牵涉到他的自我,牵涉到社会生活中他直接地、切身地意识到的那些狭隘的领域。因此,这些困扰的表述和解决完全在于作为一个人生整体的个体,在于他的切身情境所及,而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某种程度上他的有意活动,所能直接触及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场景。困扰是一种私人事务:某个人觉得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而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必然会超出个体所置身的这些局部环境,超出他内在生活的范围。它们必然涉及许多这类情境是如何组合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而各式各样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叠,彼此渗透,以形成社会历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结构。议题是一种公共事务: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至于那种价值究竟是什么,威胁它的到底是什么,往往众说不一。这样的争论常常缺乏焦点,哪怕只是因为议题本质如此,不像困扰,9甚至是广为蔓延的困扰,它无法基于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环境,对议题做出精准的界定。事实上,议题还往往牵扯到制度安排方面的某种危机,而且经常关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
我们不妨从这些角度来看看失业问题。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要想施以救济,我们应该看看这人的性格,还有他的技能,看看他眼前有什么机会。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任何一个个人所面临的机会的范围内就能找到解决之道。因为机会的结构本身已经崩溃。要想正确地表述问题所在,并找出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考察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只是零散个体的个人处境和性格。
让我们再来看看战争。战争一旦爆发,相关的个人问题也许是如何保全生命或死得荣耀,如何趁机大捞一笔,如何在军队系统中爬得更高从而保全自己,或是如何为结束战争尽一份力。简言之,战争爆发后,要根据一个人所持有的价值,找到一套情境,在其中求得安全保命,或是让自己的牺牲在其中变得富有意义。但有关战争的结构性议题必须涉及它的起因,涉及它让什么类型的人仓促上位,发号施令,涉及它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和宗教制度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为何陷入散乱无序、无人负责。
让我们考虑一下婚姻。在一桩婚姻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能会体验到个人困扰。但如果结婚头四年中的离婚率达到每1000对夫妻中有250对离婚,这就表明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影响它们的其他制度出现了某种结构性问题。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大都市(metropolis),也就是令人恐惧、美丑混杂、壮丽奢华肆意蔓延的大城市(the great city)。在许多上层阶级人士看来,对于“城市问题”的个人解决办法,就是在市中心买套带私家车库的公寓,而在40英里开外,拥有一片方圆100英亩的私有土地,里面有一座亨利希尔(Henry Hill)设计的房子,附带有盖瑞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设计的园林。两处环境皆属可控,两边都有一小队服务人员,并由私人直升机交通往返。在这样的可控环境下,绝大多数人都能解决城市现状所导致的许多个人情境的问题。但无论这一切多么令人赞叹,也不能缓解城市的结构性现状所引发的公共议题。该如何对付这种令人惊叹的奇形怪状呢?把城市全部拆分成零散的单元区域,融合居住区与工作区?在现有区位上重新翻建?或者,彻底清空,炸毁干净,另择他地,重绘蓝图,筑造新城?那又该有怎样的新计划呢?不管决策如何,谁是决策者,谁又是执行者呢?这些议题都是结构性的。我们要直面这些议题,求得解决之道,就必须考虑那些影响着数不清的情境的政治经济议题。
只要经济安排不佳,导致疲软,失业的问题就不再是个人能解决的了。只要战争是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工业化进程不平衡的题中应有之义,普通人囿于逼仄情境,无论有没有心理援助,都不会有能力解决这种体系原由网或者体系的匮乏强加给他的那些困扰。只要家庭作为一项制度,把女人变成形同奴隶的小宠物,把男人变成独挑大梁的供养者和断不了奶的依赖者,那么纯粹私人的办法就始终不能解决美满婚姻的问题。只要过度发达的都市圈(megalopolis)和过度发展的小汽车是一个过度发展的社会的固有特性,那么仅凭个人才智和私有财富就无法纾解都市生活的议题。
如前所述,我们在各式各样具体情境中的体验,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迁所导致的。有鉴于此,要想理解许多个人情境中的变迁,我们就必须有超出这些个人情境的眼光。而随着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些制度涵盖面越来越广,彼此关联越来越复杂,这类结构性变迁也日渐增多,愈益复杂。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醒认识,并能敏锐运用它,就要有能力透过纷繁多样的情境捕捉到这类关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具备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三
在我们这个时代,公众面临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私人经受的关键困扰又有哪些?我们要想梳理出这些议题和困扰,就必须搞清楚,在我们所处时期的标志性趋势下,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却遭受威胁,又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同时也得到倡导。无论我们讨论的价值是遭受威胁还是得到倡导,我们都必须要问,这里可能牵涉到哪些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并且不觉得它们面临什么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安乐(well-being)。而当他们珍视某些价值,但 的确感到它们面临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危机——危机要么限于个人困扰,要么成为公众议题。一旦他们所抱持的价值似乎无一幸免,他们就会觉得受到整体威胁而陷入恐慌。
但是,假如人们对自己珍视什么价值浑浑噩噩,又或者没有体验到任何威胁呢?这就是所谓漠然(indifference)的体验。而如果这种态度似乎波及所有价值,那就成了麻木(apathy)。最后,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呢?那就会体验到 不安(uneasiness),体验到焦虑(anxiety),如果牵涉面足够广泛,就成了完全无法指明的不适(malaise)。
我们的时代弥漫着不安和漠然,但这种不安和漠然又还不能得到清楚阐明,并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体察。它们往往只限于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恼,而不是从价值和威胁的角度得到明确界定的困扰。它们往往只是沮丧的情绪,让人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却不能上升为明确的论题。人们既说不清面临威胁的价值是什么,也道不明究竟是什么在威胁着他们。一句话,它们还没到能让人做出决策的程度,更不用说被明确梳理成社会科学的问题了。
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基本没有什么怀疑,只有某些自欺欺人的工商界人士觉得经济议题也就是一堆个人困扰。在这些有关“资本主义的危机”的争论中,对马克思的梳理,以及许多未曾明言的对其著述的重新梳理,或许确立了这个议题的主导论调,有些人开始从这些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个人困扰。大家都很容易看到是哪些价值受到威胁并予以珍视,而威胁它们的结构性矛盾也似乎一目了然。人们对这两点都有广泛而深切的体验。那是一个讲政治的年代。
然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遭受威胁的这些价值,人们往往既没能广泛承认其为价值,也没能普遍感受到它们面临威胁。大量私人的不安就这么得不到梳理,大量公众的不适,以及众多极具结构相关性的决策,都从未成为公共议题。而对于接受理性和自由之类的传统价值的人来说,不安本身就是困扰,漠然本身就是议题。这种不安和漠然的境况,就是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特征。
这一切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观察家们往往解释道,如今需要梳理的问题的类型本身已经有了变化。我们常常被告知,我们这十年的问题,甚至我们时代的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这个外部领域,现在成了与个人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这其中其实牵涉到这么一个问题:是否不久之后就不再有什么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个人生活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童工,而是漫画;不再是贫困,而是大众休闲。不仅有许多私人困扰,而且有许多重大公共议题,都被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描述。这样的努力往往显得可悲,因为这是在回避现代社会的大议题、大问题。这样的表述似乎往往只依赖于一种狭隘的地方意识,只对西方社会感兴趣,甚至只对美国感兴趣,从而忽略了全人类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它还常常武断地将个人生活与更大范围的制度相脱离;而人们的生活就是在那些制度中展开的,后者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有时会比孩童时节的亲密环境更为严重。
比如,如果不考察工作,我们甚至无法表述休闲问题。要想把漫画书引发的家庭困扰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就不能不结合当代家庭与社会结构的新近制度之间的新关系,考察当代家庭所面临的困境。要是没有认识到不适与漠然如今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个人倾向,那么,无论是休闲,还是它那些令人萎靡不振的实际应用,都不会被视为问题。在这样的风气和倾向下,如果没有认识到进取心作为在合作经济中工作的那些人的职业生涯的重要成分,也已遭遇危机,那就无法阐述更无法解决任何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
精神分析学者反复指出,人们的确常常“愈益感到被自己内心无法确定的模糊力量所推动”,事实确实如此。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有言曰:“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就是他自己的桀骜本性,就是他心中被禁锢的黑暗力量。”然而,此言 谬矣。正相反,现如今,“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即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遍渗透的改造。
现在,社会科学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两个维度在此互相重合——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当代的不安与漠然都包括哪些成分。这是其他文化工作者——从自然科学家到艺术家,乃至于整个学术共同体,对他们提出的核心要求。我相信,正是由于这项任务和这些要求,社会科学将日渐成为我们这个文化时代的共同尺度,而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将愈益成为我们最需要的心智品质。
四
在思想上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某种思考风格趋于成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不过,放眼当下,有许多思想时尚蔚为流行,却也只是各领风骚一两年,然后就被新的时尚所取代。这样的狂热或许会使文化这场戏更加有滋有味,但在思想上却只是轻浅无痕。而像“牛顿物理学”或“达尔文生物学”之类的思维方式则不是这样。这些思想世界个个影响深远,大大超出观念和意象的某一专门领域。无论是引领时尚的论家,还是籍籍无名的学者,都能基于这些思维方式的用语或从中衍生的用语,重新定位自己的观察,重新梳理自己的关切。
在现代西方社会,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已成为严肃思考与大众玄学的主要共同尺度。“实验室技术”成为普遍接受的程序模式和学术保障的源泉。这就是学术上的共同尺度这一观念的意义之一:人们可以基于它的用语陈述自己最牢固的信念;而其他用语、其他思考风格,似乎沦为回避问题和故弄玄虚的手段。
一种共同尺度大行其道,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思维风格或感受模式。不过它的确意味着,往往会有更加普遍的学术兴趣转向这一领域,在那里得到最明晰的梳理,一旦其得到如此梳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已经成功,即便不是成功找到解决之道,至少也是成功找到一种有益的推进方式。
我相信,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主要的共同尺度,成为其标志性特征。这种心智品质体现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但远远不限于我们目前所知的这些研究的范围。个体乃至整个文化共同体要获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乃需要点滴积累,往往也需要蹒跚摸索,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品质缺乏自觉意识。他们似乎不知道,要做出他们可能做出的最佳研究,关键就在于运用这种想象力。他们也不明白,由于未能培养出这种想象力并加以应用,也就未能满足日渐赋予他们的文化期待,那原本是他们这几个学科的经典传统留下来的可用遗产。
不过,出于对事实与道德的关注,文学作品和政治分析通常要求具备这种想象力的品质。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已经成为判定思想努力和文化感受的核心特征。一流的评论家和严肃的新闻记者都很好地展示出了这些品质。事实上,两者的工作往往都是从这些角度来评判的。流行的批评范畴,如高雅趣味、中级趣味和低俗趣味,在现在的社会学意味与美学意味至少可以说不相上下。小说家的严肃作品体现着对于人类现实流传最广泛的界定,其中往往就蕴含着这种想象力,并努力满足相关的要求。借此,人们便可以寻求从历史的角度为当下定向。由于有关“人性”的意象变得更成问题,人们感到越来越需要更加密切地、更具想象力地关注那些社会惯例和社会巨变,因为它们在这个充满民间躁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揭示着(并塑造着)人的性质。虽说时尚往往正是被应用时尚的尝试所揭示出来的,但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它是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似乎以极其令人瞩目的方式,承诺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来理解我们自身私密的现实。它并不只是一种与当代诸多文化感受力并立的普通的心智品质。 唯有这种品质,它的应用更为宽广,更为灵便,并会就此做出承诺:所有这类感受力,其实就是人的理性本身,将会在世间人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自然科学作为更传统的主要共同尺度,其文化意义越来越让人怀疑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自然科学有些不够充分。科学风格的思维和情绪、想象与感受,其充分性当然从一开始就面临宗教上的质疑和神学上的争论。但我们的历代科学前辈们成功地平息了这类宗教质疑。目前的质疑是世俗的,是人本主义的,往往很让人困惑。自然科学晚近的发展固然在氢弹的发明及其环球运载手段方面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却并未让人感到,对于更大的思想共同体和文化公众群体所广泛知悉并深切思虑的那些问题,它能就其中任何一个提出解决之道。人们认为这些发展是高度专业化的探究的结果,这没有问题,但要觉得它们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就有些不合适了。它们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所引发的问题其实多于它们已经解决的问题,而它们所引发的问题则基本全部属于社会事务,而非自然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人看来,征服自然,克服稀缺,明显几近大功告成。如今在这些社会里,科学作为这种征服的首要工具,让人觉得肆无忌惮,漫无目标,有待重估。
现代社会对科学的敬重早已徒具其表,而时至今日,与科学维系一体的那种技术精神和工程想象与其说是充满希望与进步的情怀,不如说更可能是令人惊惧、形象模糊的事物。诚然,所谓“科学”,意涵并非尽在于此,但人们恐惧的是,这样的意涵会慢慢成为科学的全部。人们觉得需要对自然科学进行重估,就反映出需要找寻一种新的共同尺度。从科学的人文意义和社会角色,到其牵涉的军事议题和商业议题,乃至其政治意涵,都在经受着令人困惑的重估。军备方面的科学进展有可能导致世界政治重组的“必要性”,但人们并不觉得这种“必要性”仅凭自然科学本身就能解决。
有许多曾经被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如今被人们视为模糊不定的哲学。有许多曾经被当成“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常常让人觉得只不过给出了人们生活其间的那些现实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家不再试图描述作为整体的现实,或者呈现有关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所谓“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定向手段,不如说是一套“科学机器”,由技术专家操作,受商界和军界的人控制,而对于作为精神和取向的科学,这些人既无法体现,也无从理解。与此同时,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们又往往把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体验视同人的体验,宣称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上种种使许多文化工作者越来越觉得,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文明中一种相当暧昧的成分。
不过,借用C. P. 斯诺(C. P. Snow)的讲法,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无论是历史还是戏剧,是传记、诗歌还是小说,文学一直都是人文文化的精华。不过,人们现在也经常提出,严肃文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艺术。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并不只是因为大众群体的扩大、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这一切给严肃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还要看当代历史的性质如何,以及具备鉴赏力的人们觉得需要如何把握这种性质。
在当代政治事实和历史现实面前,有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艺术努力可以一争短长?在20世纪历次战争事件面前,又有什么戏剧中的地狱景象能够与之相称?对于置身原始积累创痛中的人们的那种道德麻木,又有什么样的道德斥责足以衡量深浅?这就是人们想要了解的社会历史现实,所以他们常常觉得,靠当代文学不足以洞彻真相。他们渴求事实,追寻事实的意义,希望获得可以相信的“全貌”,并在其中逐渐理解自身。他们还想获得助人定向的价值,培养适宜的情感方式、情绪风格和描述动机的词汇。但泰纳们并不容易在当代文学中找到这些东西。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 要在那里找这些东西,而在于人们往往没能找到。
从前,文人们身兼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身份,会在行走英格兰或远游美利坚时撰录见闻。他们努力概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征,并捕捉其间的道德意义。假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或泰纳(Taine)重生当世,他们难道不会成为社会学家吗?《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就提出了这个有关泰纳的问题,他认为:
泰纳始终把人首先看作一种社会动物,把社会视为多个群体的组合。他的观察细致入微,是个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又具备一种品质……特别有利于洞察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种品质就是生气勃勃。他过于关注当下,从而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史家;他过于擅长理论分析,所以无法试手创作小说;他过于推重文学,视之为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档案,故此无法成为第一流的评论家……他有关英国文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在探讨英国文学,不如说是在评论英国社会的道德风尚,并被借来宣扬其实证主义。全面观之,他首先是一位社会理论家。
但泰纳依然算是个“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这或许证明,19世纪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满心想的就是热忱追寻“法则”,据说这样的“法则”堪比想象中自然科学家发现的“法则”。由于缺乏充分确凿的社会科学,批评家与小说家,戏剧家与诗人,就都成了梳理私人困扰甚至公共议题的主要干将,而且往往独力担当梳理的任务。艺术的确表现出了诸如此类的情感,也能常常彰显它们,并以戏剧性的犀利见长,但仍然不具备思想上的明晰,而这是人们今天理解或缓解这些困扰和议题所必需的。现今的人们如果要克服自己的不安与漠然及其所导致的各种棘手苦恼,就必须直面这些困扰和议题,而艺术并没有也无法将这些情感梳理成涵盖它们的问题。事实上,艺术家对此往往也没有兴趣。不仅如此,严肃的艺术家本人就深陷困扰。在这方面,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有望在思想和文化上助上一臂之力。
五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要界定社会科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义。我想具体确定有哪些努力在背后推动着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发展,点明这种想象力对于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连带意涵,或许还要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必备条件给出一些建议。我打算通过这些方面来揭示今日社会科学的性质与用途,并点到即止地谈谈它们在美国当前的境况。
当然,无论何时,“社会科学”的内涵都包括名正言顺的社会科学家正从事的研究,但问题是他们绝没有人人都干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干的连同类事情都算不上。社会科学也在于过去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做的研究,可是不同的学者会选择构建并诉诸自己学科中不同的传统。当我说“社会科学的承诺”时,我希望读者清楚,我指的是我看到的那种承诺。
就在当前,社会科学家对自己所选研究的可能走向也普遍感到不安,在学术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皆是如此。而在我看来,这种不安,连同那些产生不安的令人遗憾的趋势,都属于当代思想生活的一种整体不适。不过,社会科学家身上的这种不安或许更为刺痛,哪怕只是因为引领他们领域中的大部分早期研究的承诺更加宏大,他们所处理的主题性质特殊,以及今日的重要研究面临的需要相当急迫。
并非人人都有这种不安,只不过有些人对于承诺念兹在兹,心怀赤诚,足以承认当前许多努力外表矫饰,实质平庸;对他们来说,许多人并无不安这一事实本身,只会加剧他们的不安。坦率来讲,我希望加剧这种不安,确定它的某些源泉,以便将其转变成一种具体的激励,去实现社会科学的承诺,清理场地,另起炉灶:简言之,我希望去指明眼前的一些任务,点出目前必须做的研究中可以利用的手段。
目前来说,我所倡导的社会科学观尚未占据上风。我的观念反对将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这些约束、晦涩和琐碎已经导致当今社会研究出现了危机,并且丝毫看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有些社会科学家强调需要有“技术专家研究小组”;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学者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殚精竭虑,反复打磨调查方法和技术;另一些人则认为,学术巧匠的治学之道正在遭人遗弃,现在应当重振其活力。有些人的研究遵循着一套刻板的机械步骤;另一些人则力求培养、融入并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些人沉溺于所谓“理论”的高度形式主义,把一堆概念拼来拆去,这在另一些人看来属于过分雕琢。后面这类人只有在明显能扩大感受范围、增进推理所及的时候,才有冲动去详细阐发术语。有些人格局狭隘,只研究小规模的情境,指望能“逐步积累”,以发展成有关更大规模结构的观念;另一些人则直接考察社会结构,力求在其中“定位”许多较小的情境。有些人完全忽略比较研究,只考察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一个小共同体;而另一些人则基于充分的比较视角,直接研究全球各国的社会结构。有些人将自己的精细研究局限于时间序列上非常短暂的世间人事;另一些人则关注仅在长期历史视角下才能凸显的议题。有些人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另一些人则广为借鉴各个系科,根据话题或问题来确定研究,而不管它们在学院体系里位居何处。有些人直面各式各样的人生、社会与历史,另一些人则不会这样。
诸如此类的对比,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对比,都不必然是真实确凿、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虽说在如政客一般的激烈争吵中,或是在贪懒求安的专业化旗号下,它们往往被当成这样的抉择。在此我只想初步地谈谈,本书结束时我再回到这个问题。当然,我很希望能够呈现出自己所有的偏见,因为我认为,评判应当是坦诚的。但我也努力抛开自己的评判,阐述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当然,相比于我打算考察的那些人,我们的偏见程度可谓是半斤八两。就让那些不喜欢我的偏见的人拒绝我的偏见,以此让他们的偏见也像我一样,努力变得清楚明确、公开坦诚吧!这样一来,社会研究的道德问题,也就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项公共议题的问题,就会被人认识到,讨论也就有可能展开了。如此,人们在各方面将更为自觉,这当然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事业能够具备客观性的前提条件。
概言之,我相信,可以被称为经典社会分析的是一系列可以界定、可以利用的传统,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的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我还相信,这一传统的赓续目前遇到了重大阻碍,无论是在社会科学内部,还是在其学院环境和政治环境方面,尽皆如此。但不管怎么说,构成该传统的心智品质正愈益成为我们整体文化生活的一个共同特性,无论其面目多么模糊不清,包装多么芜杂混乱,总归是越来越被人们视为不可或缺。
在我看来,许多实际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的人,都谨小慎微,迟迟不愿应对当下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事实上,许多人已经放弃了社会分析的学术任务和政治任务,还有些人无疑只是担不起他们仍然被赋予的角色。他们有时显得几乎是特意故技重施,怯懦可谓变本加厉。然而,尽管如此迟疑,无论公共关注还是学术关注,现在都非常明显地聚焦在他们宣称要研究的那些社会世界上,所以必须承认,他们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机遇。透过这种机遇,我们看到了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看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化用益,也看到了有关人与社会的研究的政治意义。
六
公开自称是社会学家的我一定会倍感尴尬,因为我在下文诸章中将会探讨的所有令人遗憾的趋势(或许只有一种例外),都落入一般人们所认为的“社会学的领域”,虽说这些趋势所隐含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退弃,无疑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许多日常工作的特点。从政治学和经济学,到历史学和人类学,无论诸如此类的学科中实际情况怎样,显然在当今的美国,人们所知的“社会学”已经成为有关社会科学的反思的中心。它已经成为对于方法的兴趣的中心,你可以从中找到对于“一般理论”的最狂热的兴趣。已经融入社会学传统的发展的学术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着实令人瞩目。要把这样多姿多彩的研究解释成“一种传统”,本身就很鲁莽。不过,人们或许大体会同意,现在被视为社会学研究的东西往往朝一到三个整体方向发展,其中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偏离正轨,乃至走火入魔。
趋势一:趋向一种历史理论。例如,在孔德笔下,就像在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那里一样,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努力,关注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它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系统性的:所谓历史性,是因为它处理并运用过去的材料;所谓系统性,是因为它这么做是为了识别出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识别出社会生活的规律。
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被扭曲成一件跨历史的紧身衣,在这件紧身衣中,人类历史的各种素材都会被强塞进去,有关未来的先知预言般的观点(往往还是阴郁的论调)则会被从中硬拽出来。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研究就是广为人知的例子。
趋势二:趋向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理论。比如,在形式论者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齐美尔(Simmel)和冯维泽(Von Wiese)的著述中,社会学开始处理一些特别的观念,旨在将所有社会关系逐一归类,并洞察它们据说普遍一致的特征。简言之,这种理论注重在非常高的概括层次上,以相当静态和抽象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结构诸要素。
或许是为了回击趋势一里的歪曲,趋势二可以彻底舍弃历史:有关人和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精致而乏味的形式论,其核心任务就是没完没了地对各个“概念”进行拆分与重组。在我所称的“宏大理论家”(Grand Theorists)当中,观念(conceptions)的确已经变成了概念(Concepts)。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研究就是美国社会学在当代最典型的例证。
趋势三:趋向针对当代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尽管在约1914年以前,孔德和斯宾塞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并且来自德国的理论影响也清晰可见,但经验调查还是早早就在美国占据了核心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和政治学早早取得了学院建制地位。有鉴于此,只要社会学被界定为对某个特定的社会领域的研究,就容易沦为社会科学中某种打零工的人,打工内容就是研究各种学术剩余的大杂烩。有的研究城市和家庭,有的研究种族关系和族裔关系,当然还有的研究“小群体”。我们将会看到,由此导致的大杂烩被转换成了一种思维风格,我下文的考察将其概括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liberal practicality)。
有关当代事实的研究很容易沦为罗列有关情境的一系列事实,彼此互不关联,往往也无关紧要。美国社会学开设的许多课程就彰显出这个特点。或许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领域的教科书可为最佳例证。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往往会成为适用于几乎任何事物的研究方法的专家,在他们那里,多样的方法(methods)已经变成了单一的“方法论”(Methodology)。乔治伦德伯格(George Lundberg)、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斯图亚特多德(Stuart Dodd)、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等人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当前的榜样,而他们的精神气质就更是如此。这些趋势各自的关注零零散散,又都为了方法而打磨方法,倒是同声相应,尽管并不一定同时出现。
我们可以把社会学的独特性理解为它的某种或多种传统趋势的偏离,但或许还得从这些趋势的角度来理解它的承诺。今日的美国呈现出某种希腊化一般的大融合(Hellenistic amalgamation),体现出来自好几个西方社会的社会学的多种要素与宗旨。但危险在于,在这样的社会学繁荣当中,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将变得急功近利,而社会学家也会匆忙赶着进行所谓“研究”,乃至于丢掉真正有价值的遗产。不过,在我们的境况中也存在着机遇:在社会学传统里面,包括了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的充分承诺的最出色阐述,也有某些对于这种承诺的局部实现。社会学学者能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的诸般精义与启示难以被简单概括,但任何社会科学家只要将其掌握在手中,定能有丰厚的回报。把握了这些东西,就不难帮他在社会科学中为自己的研究确立新的取向。
我将先考察社会科学中一些久而成习的偏向(第二章到第六章),然后再来探讨社会科学的各项承诺(第七章到第十章)。
亨利希尔(1913—1984),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盖瑞特埃克博(1910—2000),美国著名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师。1950年盖瑞特出版《宜居景观》( Landscape for Living)一书,阐明花园的功能意义,说明怎样将市郊生活的日常必需设施如晒衣场、儿童游戏沙坑和烧烤野餐地等融入新花园设计。——译注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57 年11月15日。
有必要指出,我对“社会研究”(the social studies)这个词的喜爱程度远超过“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原因并不在于我不喜欢自然科学家(恰恰相反,我很喜欢),而在于“科学”这个词已经获得了巨大声望,并且意涵相当模糊。我觉得实无必要强行倚仗其声望,或者把它用成一种哲学比喻,从而把意涵搞得更不清楚。不过,我也担心,如果我讨论“社会研究”,读者们想的可能只是高中公民课,而这正是所有人文学识领域中我最想摆脱干系的一块。至于所谓“行为科学”,根本就是空中楼阁。我猜想,人们捏造出它,只是一种宣传伎俩,用来从基金会和把“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国会议员那里为社会研究谋取经费。最佳用语应该包括历史(以及心理学,只要它还关注人类),应当尽可能不存争议,因为用语本身应当是我们进行争论的 手段而不是对象。或许“人文学科”(the human disciplines)也行,这一点姑且不论。我只希望不要引起广泛误解,所以尊重习惯,选用更标准的“社会科学”。再有一点是:我希望我的同行会接受“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个用语。读过这部书稿的政治学家建议用“政治学的想象力”,而人类学家提议用“人类学的想象力”,如此等等。比用语更重要的是观念,我希望随着本书的展开,观念会逐渐清晰。当然,我之所以选这个用语,并不只是想指作为学院系科的“社会学”。它对于我的意味有许多根本不是由社会学家来表达的。比如,在英国,作为一门学院系科的社会学某种程度上依然位居边缘,但在英国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小说中,尤其是历史学中,社会学的想象力其实发展得非常好。法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的反思之所以既令人迷乱,又勇敢率直,就在于它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命运的社会学特征感受敏锐,但推动这些潮流的是文人,而不是职业社会学家。不过,我还是使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原因在于:第一,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无论如何,我是个社会学家;第二,我真的认为,回顾历史,还是经典社会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频繁也更鲜活地展示出了这种心智品质;第三,既然我打算批判性地考察许多令人费解的社会学流派,自己的用语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章 宏大理论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一个宏大理论的实例,摘自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该书被广泛视为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之一。
所谓价值,就是共享符号系统的一个要素,充当着某种判据或标准,以便从某个情境中固有的开放可用的多个取向替换方案中做出选择。……不过,基于符号系统的角色,我们有必要在行动的总体性中,将其动机取向的面向与“价值取向”的面向区分开来。这个面向关注的不是期望中的事态对于行动者就其满足—剥夺平衡而言的意义,而是选择标准本身的内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取向这个概念就成了一种逻辑工具,用以梳理将各种文化传统融入行动系统的关联方式的一个核心面向。
依据上述规范取向的派生结果,依据上述价值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认为,所有价值都涉及某种可称为社会参照的东西……行动系统有一个内在固有特性:用术语来说,行动是“规范性取向的”。如前所示,这一点系源于期待这个概念及其在行动理论中的位置,尤其是在行动者追求目标的“积极行动”阶段。因此,期待,再配上被称为互动过程的“双重偶变性”(double contingency),就引发了一个绝对无法回避的秩序问题。这个秩序问题进而可以区分出两个面向,一是使沟通成为可能的符号系统中的秩序,二是动机取向与期待的规范性面向之间的契合所体现的秩序,即所谓“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
所以说,秩序问题,因此也是社会互动的稳定系统之整合的性质问题,也就是社会结构问题,26关键就在于行动者的动机与规范性文化标准的整合,这些文化标准在我们的人际场合中整合着行动系统。用上一章所使用的术语来说,这些标准就是价值取向模式,并就此成为社会系统的文化传统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能有的读者现在很想跳到下一章了,我希望他们不要放纵这种冲动。所谓“宏大理论”,也就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组合与拆解,值得深究一番。当然,它的影响还不如下一章要考察的方法论上的约束那么重要,因为作为一种研究风格,它的传播还比较有限。事实上,它不那么容易理解,人们甚至怀疑它根本就不可理解。诚然,这也算是一种起到保护作用的优势,但如果它就是要通过公开声言(pronunciamentos)来影响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习惯,那就得说这是一种缺陷了。不开玩笑、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宏大理论的产物已经被社会科学家们以如下一种或多种方式接受了:
至少对于某些声称理解并喜欢宏大理论的人来说,这是整个社会科学历史上最伟大的进展之一。
对于许多宣称理解但不喜欢宏大理论的人来说,它东拉西扯,笨拙生硬。(这类人其实很少,只是因为不喜欢、没耐心,许多人便不想努力求解其意。)
还有些人并不宣称理解,却非常喜欢宏大理论,这类人还不少。对他们来说,它是一座令人惊叹的迷宫;并且正因为时常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索解,它才充满魅力。
更有些人既未宣称理解又不喜欢宏大理论,假如他们有勇气保留这份信念,他们就会觉得,其实它只是皇帝的新衣。
当然,还有许多人会有所保留。更多的人会耐心保持中立,静观宏大理论在学界的后果——如果真能有影响的话。虽然这一思想可能令人生畏,但除了风言风语,许多社会科学家甚至对其一无所知。
所有这些态度都戳中了一个痛处,即可理解性。当然,这一点并不限于宏大理论,但既然宏大理论家们与此牵扯甚深,我们恐怕真的必须问一问:宏大理论究竟只是一堆胡乱堆砌的繁文冗词,还是终究有些深意蕴藏其间?我的答案是:确实有些干货,虽然埋藏颇深,但毕竟不乏洞见。所以问题就成了:扫除理解意涵的一切障碍,将有望理解的东西呈现出来后,宏大理论到底说了些什么?
一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办法只有一个:我们必须转译一段最能代表这种思维风格的语例,然后来看看译文。前文已经举出了我选的语例。必须指出的是,我并不打算在此评判帕森斯整个研究的价值。如果我引述到了他的其他著述,那只是为了以经济有效的方式澄清他这本书里蕴含的某个论点。在把《社会系统》中的内容转译成英文时,我也不想冒称自己的翻译很出色,只能说在翻译中没有丢失任何明确的含义。我保证,这段译文包含了原文中所有可以理解的东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将努力从有关词汇的界定中,从有关词汇关系叠床架屋的界定当中,筛选出有实质内容的陈述。这两方面都很重要,混为一谈是对明晰性的致命打击。我首先来转译几段话,以彰显需要做的事情的类型;然后我将给出两段对整本书的简略译文。
先来转译本章开头引用的语例:人们常常共享标准,并彼此期望遵循标准;只要他们依此行事,所在社会便有望呈现出秩序感。(转译完毕)
帕森斯写道:
这种“契合”又有一种双重结构。首先,通过将标准内化,遵从标准就会对自我产生个人性的、表意性的和/或工具性的重要意义。其次,他我(alter)对自我的行动(action)做出反应(reactions),作为约制(sanctions),这些反应不断结构化,就是他对于标准的遵从的一项功能。因此,遵从作为满足他的需求倾向的一种直接模式,与遵从作为引发他人有利反应、避免他人不利反应的一项前提条件,往往两相契合。只要参照众多行动者的行动,遵从某种价值取向标准,就同时满足了这些要求,也就是从系统中任一给定行动者的视角来看,它既是满足自身需求倾向的一种模式,又是“优化”其他具有显著意义的行动者的反应的一项前提。那么,这个标准就可以说被“制度化”了。
这个意义上的价值模式始终会在某个互动(interaction)情境中被制度化。因此,与之相关的得到整合的期望系统始终存在双重面向。一方面,有些期望关注被视为参照点的行动者即自我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该行为设定标准,这些期望就是他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系列期望牵涉到他人(他我)具有偶变性可能的 反应(reaction),这些期望可称为“约制”,并可根据是被自我感受为促进满足还是剥夺满足,进一步细分为正向约制与负向约制。角色期望与约制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交互性的。对自我而言属于约制的东西,对于他我而言就是角色期望;反之亦然。
因此,在一个个体行动者的整体取向系统中,围绕与某个特定互动情境相关的期望组织起来的某个部分,就是角色。它与一套特定的价值标准相整合,这些价值标准主导着与彼此相契互补的一个或多个他我之间的互动。这些他我不一定是界定清晰的一组个体,而可以涉及任何他我,只要它与自我之间结成某种互补性互动关系,而这样的互动关系又牵涉到参照有关价值取向的共同标准,在多个期望之间达成交互性。
一套角色期望的制度化,以及相应的约制的制度化,显然存在程度深浅的问题。这个程度是两组变项的功能。一方面是那些影响价值取向模式的实际共享程度的变项,另一方面是那些决定对于实现相关期望的动机取向或承诺的变项。我们会看到,有多种因素能够通过这些渠道影响制度化的程度。不过,还存在着与充分制度化对立的一极,即失范,也就是互动过程的结构化互补性的缺失;换言之,就是上述两种意义上的规范性秩序的彻底崩溃。不管怎么说,这个概念是有局限的,从来不能描述一个具体的社会系统。正犹如制度化的程度有深有浅,失范的程度也是轻重有别。两者互为对立。
所谓制度,不妨说就是某些制度化角色整合的复合体,它对于所讨论的社会系统具有关联全局的结构性意义。制度应当被视为比角色更高一层的社会结构单元;事实上,它是由多种多样相互依赖的角色模式或其要素组成的。
换言之:人们相互配合,针对彼此而展开行事。人人都会考虑他人的期望。当这类相互期望足够确定、足够持久时,我们就称其为标准。每个人也会期望他人将对自己之所为做出反应,我们称这些被期望的反应为约制。其中有些约制似乎很令人满足,另一些则不是。当人们受着标准和约制的引导,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在一起扮演着角色。这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打个比方,事实上,我们所称的制度或许最好被界定为一套相对比较稳定的角色。如果在某个制度里,或者在由这类制度构成的整个社会里,标准和约制都不再能约束人们,我们就可以遵照涂尔干的说法,称之为失范(anomie)。因此,一个极端是所有标准和约制都清晰有序的制度,另一个极端则是失范:如叶芝(Yeats)所言,中心再也保不住了。或者照我的讲法,规范性秩序已经崩溃。(转译完毕)
必须承认,这段转译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我只是稍稍发挥了一些,因为这些都是很不错的观念。事实上,宏大理论家的许多观念一旦被转译,就是许多社会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的比较标准的讲法。不过,就“制度”而言,上文给出的定义并不很完备。对于译文,我们还必须加上:构成一项制度的那些角色往往并不只是一些“共享期望”的大范围“互补性”。你曾经在一支军队、一座工厂或者哪怕只是一个家庭中待过吗?对,这些都是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有些人的期望似乎比其他任何人的期望都更需要尽快得到满足。我们不妨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更大。或者用更有社会学味道的方式讲,一项制度就是以权威分等的一套角色,尽管这也不完全是社会学性质的说法。
帕森斯写道:
从动机的角度考虑,依附于共同价值就意味着行动者具有支持价值模式的共同“情感”。不妨对它这样界定:遵从相关期望本身被视为一件“好事”,相对独立于能从这种遵从中获得的任何具体的工具性“好处”,如避免负向约制。不仅如此,这种对于共同价值的依附尽管有可能切合行动者的直接满足性的需求,却也始终有着“道德性”的面向。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遵从规定了行动者在自己所参与的更广泛的社会行动系统中的“责任”。显然,责任的具体焦点就是由特定的共同价值取向所构成的那个集合体。
最后,很显然,就其具体结构而言,支持这类共同价值的“情感”并不能常常展现出有机体的先天属性。它们一般都是习得的或者说后天获取的。不仅如此,它们在行动的定向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主要是像被认知并被参照“调适”的文化客体,而是像逐渐被内化的文化模式。它们构成了行动者人格系统本身的结构的一部分。因此,诸如此类的情感或所谓“价值态度”都是人格真正的需求倾向。只有通过制度化价值的内化,行为才能在社会结构中获得真正的动机整合,更加“深层”的动机层次才能得到驾驭,以实现角色期望。只有当这一切得到高度实现,才有可能说一个社会系统得到了高度整合,也才有可能说,集合体的利益与组成该集合体的成员的私人利益达成了契合。
一套共同价值模式与各成员人格的内化需求倾向结构之间达成这样的整合,正是社会系统的动力机制的核心表现。除了转瞬即逝的互动过程,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都有赖于一定程度的这种整合。这一点可谓社会学的根本动力原理。任何分析若要宣称是社会过程的动态分析,都要以此为主要参照。
换言之:当人们共享同样的价值时,往往会以他们彼此期望的方式行事。不仅如此,他们还往往把这种遵从当成很好的事情,哪怕看起来有悖于自己的直接利益。这些共享价值是后天习得的,而非先天传承,但这丝毫无损于它们对人的动机激发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们成了人格本身的组成部分。它们由此将社会维系一体,因为社会角度上的期望成了个体角度上的需求。这一点对于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都至关重要,所以我如果要分析某个自己持续关注的社会,就会以此作为首要出发点。(转译完毕)
我估计,以此类推,可以把厚达555页的《社会系统》转译成150页左右的直白英语。其结果不会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它会以非常清晰的用语陈述原书的核心问题,以及书中对该问题给出的解答。当然,任何观念、任何书籍,都既可以言简意赅,一言以蔽之,也可以洋洋洒洒写二十大卷。问题在于,一个陈述需要多么充分来把某事说清楚,而这事情又有多么重要:它能让我们理解多少经验,能有助于我们解决或至少陈述多么广泛的问题。
例如,我们不妨用两三句话来表达帕森斯这本书:“我们被问道: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我们被给出的解答似乎是:共同接受的价值。”这就是全部了吗?当然不是,但这是主要论点。但这是不是不公平?什么书都能这么处理吗?当然可以。下面就对我自己的一本书如法炮制:“说到底,谁在掌管美国?没人能独掌大局,但要说有什么群体在掌权,那就是权力精英。”至于您手头这本书,则可以这么处理:“社会科学都在说什么?它们应当讨论人与社会,并且有时确实如此。它们试图帮助我们理解人生与历史,以及二者在各式各样社会结构中的关联方式。”
以下四段话,就是对帕森斯这部著作的转译: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我们称为“社会系统”的某种东西,个体在其中参照彼此而行事。这些行动往往相当有序,因为系统中的个体共享价值标准,共享有关得体而实用的行事方式的标准。这些标准中有些我们可以称之为规范,那些遵循规范行事的人在类似的场合下往往也会有类似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往往非常持久的“社会规律性”。对于这类持久稳定的规律性,我称之为“结构性的”规律。不妨认为,在社会系统中,所有这些规律性会达成一种蔚为壮观、错综复杂的平衡。这只是个比方,不过我现在打算忘掉这一点,因为我想让你们把我的“社会均衡”(The social equilibrium) 概念当成是确凿的实在。
要维持社会均衡,主要有两种方式,如果其中一种或两者都失效,就会导致失衡。第一种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生个体塑造成社会人的所有方式。这种对于人的社会塑造部分在于让人获得动机,以采取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社会行动。第二种方式是“社会控制”,指的是让人循规蹈矩,以及他们使自己循规蹈矩的各种方式。当然,所谓“规矩”,我指的是社会系统通常期望和赞成的任何行动。
维持社会均衡的第一个问题,乃在于使人们主动想要做他们被要求和期望做的事情。一旦失败,第二个问题就在于采取其他方式让他们循规蹈矩。对于这些社会控制,最好的分类和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给出的,我没有什么补充。自他以后,像他说得那么好的论家倒也还能数出几位。
不过有一点的确让我有些困惑:鉴于这种社会均衡,以及装备它的种种社会化和控制,又怎么会有人不循规蹈矩呢?从我有关社会系统的“系统性、一般性的理论”(Systematic and General Theory)角度,我不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还有一点也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清楚:我该怎么解释社会变迁,或者说解释历史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只要遇到相关问题,就去做经验研究吧。(转译完毕)
或许这就够了。当然,我们还能转译得更完整一些,但“更完整”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充分”。读者不妨亲自读一读《社会系统》,会有更多的体会。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三项任务:其一,概括宏大理论所代表的逻辑性思维风格的特点;其二,厘清这个具体语例中那种并非特例的含混;其三,点明如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是如何提出并解答帕森斯笔下的秩序问题的。总而言之,我的目的就在于帮助宏大理论家们走下华而不实的高坛。
二
社会科学家当中真正重要的差别,并不在于一拨人光看不想,另一拨人光想不看,而在于具体怎么想、怎么看,如果思考与观察之间有关联,又是怎样的关联。
宏大理论的根本原因是一开始就选择了特别一般化的思考层次,导致其践行者逻辑上无法下降到观察层次。他们作为宏大理论家,从来不曾从高远的一般性下降到具体历史背景和结构背景中的问题。如此缺乏对于真切问题的坚实把握,又会加剧他们行文当中显露无遗的那种不切实际。这就造成了一个特点,就是似乎任意武断且没完没了的细分辨析,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又不能彰显我们的体验。进而,这会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故意放弃努力,不打算平实晓畅地描述和说明人的行为和社会。
当我们考察一个词语代表什么意思时,我们处理的是它的语义(semantic)面向;而当我们结合其他词语来考察它时,我们就是在处理它的 句法(syntactic)特性。我之所以引入这些简称,是因为它们以简明准确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宏大理论”沉溺于句法,却无视语义。它的践行者并不真的明白,当我们定义一个词语时,其实只是在邀请别人采取我们喜欢的用法来使用它。定义的目的就在于让争辩聚焦于事实,而好的定义的适宜结果,就是把用语之争转换成事实之辩,从而把争辩推向进一步的探究。
宏大理论家们如此迷恋句法意义,对语义指涉如此缺乏想象力,如此刻板地局限在如此高的抽象层次上,导致他们攒出来的所谓“类型体系”,以及他们为此而做的研究,看着更像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而不是努力给出系统的定义,也就是清晰有序地界定要讨论的问题,并引导我们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宏大理论家的著述中,这样的定义是系统性缺失的,由此我们可以吸取一点深刻教训:每一位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随时意识到(也因此随时有能力控制),自己正在怎样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有能力自如并明确地来回穿梭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之间,正是思想家具备想象力和系统性的标志性特征。
围绕着“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科层制”“权力精英”或“极权主义民主”之类的术语,常常有些颇为夹缠而含混的隐含意义。若要使用这些术语,我们必须细究并控制这类隐含意义。围绕这类术语,常常有好几套“复合”的事实与关系,以及纯靠猜测的关联因素和观察结论。这些也都必须小心筛选,在下定义和应用时予以阐明。
要搞清楚这类观念的句法维度和语义维度,我们必须明白每一个观念下包含的特定性的等级层次,并有能力考察所有的层次。我们必须问,如果打算用“资本主义”这个观念,我们想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单纯指所有生产工具都归私人所有这一事实呢,还是想在该术语下包括进一步的观点,即有一个自由市场作为价格、工资和利润的决定机制?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有权假定,根据定义,这个术语除了包括有关经济制度的主张,还意味着有关政治秩序的主张?
我觉得,这样的心智习性正是通向系统性思考的必经之道;一旦缺失,势必通向对“概念”的盲目崇拜。如果我们现在来更具体地考察帕森斯著作中一个重大的混淆之处,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缺失会带来何种结果。
三
宏大理论家宣称要阐述“一般性社会学理论”时,其实是在阐述一个概念王国,他们从中排除了人类社会的许多结构性特征,而这些特征长久以来都被恰当地认可为对于理解人类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表面看来,这样做用心良苦,旨在使社会学家的关切成为专业化的努力,并有别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切。按照帕森斯的讲法,社会学必须处理“社会原由网系统理论中的特定面向,即关注社会系统中价值取向模式的制度化现象,关注这种制度化的前提条件;关注模式的变化,关注遵从这类模式和偏离这类模式分别有哪些前提条件,关注所有这些情况下牵涉的动机过程”。就像任何定义应当做的那样,转译一下,把预设去掉,这句话就可读作:像我这样的社会学家会喜欢研究人们想要什么,珍视什么;我们也想搞清楚这类价值为何会多种多样,又为何会发生变化;一旦我们确实找到多少算是统合一体的一系列价值,我们会想搞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遵从它们,而另一些人却不会遵从。(转译完毕)
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曾经指出,这样的陈述使社会学家不再对“权力”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有任何关注。我的看法还不止于此。这样的陈述,实际上包括帕森斯的整部著作,与其说是在探讨某一种制度,不如说是在讨论传统的所谓“合法化”。我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根据定义,将所有制度性结构转换成某种道德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转换成所谓“符号领域”。为了阐明这一点,我想首先说明有关这块领域的一些东西,然后讨论它的所谓自主性,之后再看看帕森斯的观念是如何把事情搞得非常困难,哪怕只是提出几个分析社会结构都要涉及的最重要的问题。
那些把持权威的人,为了使自己对于制度的统治正当化,会努力将其与被人广泛相信的道德符号、神圣象征和法律条文相联系,仿佛这种统治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些核心观念或许指向一位或一组神,“服从多数”,“人民的意志”,“贤能至上或财富至上的贵族政体”,“天赋王权”,或是统治者本人自称的超凡的禀赋。社会科学家遵循韦伯的看法,称这类观念为“合法化”,有时也称之为“正当化符号”。
已经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家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这些观念:莫斯卡(Mosca)的“政治程式”(political formula)或“宏大迷信”(great superstitions),洛克的“主权原则”,索雷尔(Sorel)的“统治神话”(ruling myth),杜鲁门阿诺德(Thruman Arnold)的“民俗”(folklore),韦伯的“合法化”,涂尔干的“集体表征”,马克思的“支配观念”,卢梭的“公意”,拉斯韦尔(Lasswell)的“权威符号”(symbols of authority),曼海姆的“意识形态”,赫伯特斯宾塞的“公共情感”(public sentiments)。以上种种,诸如此类,都证明主导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占有核心位置。
与此类似,在心理学分析中,这类主导符号被私人接受后变得很重要,成为理由,往往还成为动机,引导人们进入角色,并制约他们对于角色的具体实施。比如,如果从这些角度对经济制度做出公开的正当化辩护,那么再要诉诸自利来为个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也就可以接受了。但是,如果公众都觉得有必要从“公共服务与信任”的角度为这类制度提供正当化辩护,那么旧有的自利动机和理性就可能会在资本家当中引发罪疚感,至少也会引发不安的情绪。在公共层面上行之有效的合法化,待时机成熟,往往作为私人动机也一样有效。
如此看来,帕森斯等宏大理论家所称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主要处理的就是有关合法化的主导符号。事实上,这是一个有用且重要的主题。这类符号与制度性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科学问题。话说回来,这类符号并没有在一个社会中形成某种独立自在的王国,它们的社会相关性就在于能够用来证明或反对权力安排,以及有权有势的人在这种权力安排中的位置。这类符号的心理相关性在于它们其实成了遵循或对抗权力结构的基础。
我们或许不能单纯假定,必然会有某一系列的价值或合法化占据主流,以免社会结构瓦解。我们或许也不能假定,社会结构必然会被某个诸如此类的“规范性结构”塑造成统合一体。当然,我们更不能单纯假定,任何这类“规范性结构”无论多么主流,在这个词的什么意思上讲,真的是独立自在的。事实上,就现代西方社会而言,尤其是拿美国来说,有大量证据表明,上述所有假定的反面描述都更为准确。往往会有组织得非常好的对立符号,用来证明叛乱运动的正当性,揭露统治权威,虽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不是这样。美国政治系统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受到内部暴力的威胁,这样的延续性其实相当罕见。这一事实或许也和其他一些因素一起,误导了帕森斯产生有关“价值取向的规范性结构”的意象。
“政府”并不一定像爱默生(Emerson)认为的那样,“在人的道德认同中扎下根源”。要相信政府真的是这样,就是将它的合法化与其致因混为一谈。这样的道德认同或许是因为事实上,制度统治者成功地垄断了甚至是强加了他们的主导符号。这种状况往往就像其他某个社会中的人那样,甚至比他们更为普遍。
有些人相信,符号领域是自我决定的,而诸如此类的“价值”或许真能支配历史。也就是说,为某种权威提供正当化辩护的符号,是与实施权威的实际的人或阶层相分离的。数百年前,人们已经基于这些人的假定,富有成效地讨论了这个话题。因此人们认为,进行统治的是“观念”,而不是使用观念的阶层或人。为了使这些符号的序列具备延续性,它们被呈现为以某种方式彼此关联。这样一来,符号就被视为“自我决定的”事物。为了使这个奇怪的观念更让人信服,人们往往将符号“人格化”或赋予其“自我意识”。由此,人们可以把它们设想为“关于历史的诸概念”,或一系列的“哲学家”,它们的思想决定了制度的动力机制。我们或许还能再补充一句,“规范性秩序”这个“概念”也可能被盲目崇拜。当然,我只是在转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讲法而已。
一个社会的“价值”,无论在各种私人情境下多么重要,如果没有为制度做出正当化辩护,没有给人们以动机激发,让他们履行制度角色,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上就是无关紧要的。当然,在提供正当化辩护的符号、制度性权威、遵从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有时候,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赋予主导符号以因果重要性,但不可误用这个观念,将其当成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一体性的 唯一理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还有更好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一体性”,通过这些方式来梳理与社会结构有关的重大问题会更加有用,也更加切近可观察的素材。
鉴于我们对“共同价值”感兴趣,要增进我们对这些价值的理解,最好是先考察任何给定社会结构中每一个制度性秩序的合法化过程,而不是径直试图把握这些价值,并基于此“说明”社会是怎么组成和统一的。我认为,当一个制度性秩序中相当多的成员已经接受了该秩序的合法化,当人们从这样的合法化角度成功宣示了遵从,或者至少自以为是地确保了遵从,我们就可以谈“共同价值”。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符号来“界定”各式角色遇到的“情境”,并以此作为标尺来评估领导者与追随者。展示出这类普遍而核心的符号的社会结构,自然属于极端而“纯粹”的类型。
而在另一个极端,有些社会存在一套支配性制度,这些制度控制了整个社会,并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来强加其价值。这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因为可以通过正式的纪律来有效调控人们;有时候,如果不接受制度性的纪律要求,人们将毫无谋生机会。
比如,一位训练有素的排字工受雇于一家立场保守的报纸,他可能只是为了谋生,保住饭碗而遵从雇主纪律的要求。但在他的内心,走出工作间后,他可能是个激进的鼓动家。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听任自己成为德皇旗下纪律严明的士兵,尽管他们的主观价值其实属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到行为并返诸符号的距离很长,并且也不是所有整合都建于符号之上。
强调这样的价值冲突,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协调的力量”。言行不一往往是人的特点,但力求协调同样也是。我们不能基于所谓“人性”或“社会学原则”,或是在宏大理论的授权下,先验地确定在某个社会里何者居于支配地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种社会的“纯粹类型”,拥有一套纪律完善的社会结构,其中受支配的人们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无法放弃他们预定的角色,却并不共享支配者的任何价值,因此根本不相信秩序的合法性。这就像一艘配备着苦力船工的轮船,桨橹的划动纪律分明,将桨手化减为机器上的齿轮,只在罕见情况下需要执鞭的船主挥舞暴力。苦力船工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船往哪个方向去,尽管船头稍一偏转都会让船主暴怒不已,他是这船上唯一一个能够看到前方的人。不过,或许我已经开始在描述而不是想象了。
在“共同价值系统”和强加的纪律这两种类型之间,还有五花八门的“社会整合”形式。绝大多数西方社会已经融合了纷繁多样的“价值取向”,它们的一体性包含着合法化与强制的形形色色的混合形态。当然,不仅是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任何制度性秩序都有可能是这种情形。父亲要对自己的家庭施加要求,可以威胁收回继承权,也可以运用政治秩序或许允许他使用的暴力。即使是在家庭这样的神圣小群体里,“共同价值”的一体性也绝不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任和憎恨倒可能恰恰是维系一个彼此关爱的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同理,即使没有宏大理论家相信普遍存在的这种“规范性结构”,一个社会当然也可以获得相当充分的繁荣。
这里我并不想就秩序问题细致地阐发任何解决方案,而只想把问题提出来。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必然会遵照相当武断的定义要求,假定存在“规范性结构”。而根据帕森斯的想象,那正是“社会系统”的核心。
四
按照“权力”这个词在当代社会科学里的一般用法,有关人们生活其间的各种安排、有关构成所属时期历史的诸项事件,无论人们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是它必然要处理的问题。超出人的决策范围的事件确实存在;社会安排也确有可能不经明确决策而发生变化。但只要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以及只要原本可以做出某些决策但其实没有),做(或不做)决策时都牵涉到谁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关权力的根本问题。
今天我们不能假定,对人的统治归根到底必须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管理和操纵人对权力的赞同如今已跻身常见的权力手段。我们不知道这种权力的界限,虽说我们希望它确有界限。但这一点并不能抹杀如下事实:当今许多权力的成功施行并没有受到遵从方的理性或良知的制约。
当然,如今我们无须争论就明白,归根结底,强制(coercion)就是权力的“终极”形式。但我们绝不是始终处在归根结底的状况。除了强制,我们还必须考虑权威(authority,即自愿遵从的一方所持的信念使之正当化的权力)和操纵(manipulation,即无权方在无所知晓的情形下对其行使的权力)。事实上,当我们思考权力的性质时,必须始终分辨这三种类型。
我想我们必须牢记,在现代世界,权力往往并不像它在中世纪时显示的那么有权威。统治者要想行使权力,其正当化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或缺了。至少对于当今许多重大决策来说,尤其是那些国际性决策,大众“说服”已不再“不可或缺”,事就这样成了。不仅如此,有权方明明可以用许多意识形态,却往往既不采纳也不使用。通常是在权力遭到有效揭露时,意识形态才会被祭出以为应对。而在美国,诸如此类的对立晚近并没有强大有效到足以引发对于新型统治意识形态的明显需要。
当然,今天有许多人虽然脱离了通行的效忠关系,却还没有获得新的效忠关系,因此对任何政治关怀都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他们只是漠然。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对于白痴的定义,即彻底私己的人,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许多社会里的许多公民其实就是白痴。这种境况,准确地说,这种精神境况,在我看来就是理解政治知识分子中许多现代不适的关键,也是理解现代社会里许多政治迷惘的关键。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要让权力结构维持下去甚至日益壮大,并不一定需要思想“信条”和道德“信念”。可以肯定,就意识形态的角色而言,西方社会今日有两桩关键的政治事实: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众漠然盛行于世。
无论做什么样的实质研究,持有上述权力观的人都会遇到许多问题。但帕森斯那些误入歧途的假设对我们也毫无帮助。他只是假设,每个社会都存在他所想象的那种“价值等级秩序”。不仅如此,这种假设的引申之意会系统性地妨碍我们对关键问题的清晰梳理:
要接受他的图式,我们就需要从这幅图景中读出种种有关权力的事实,这事实其实是有关所有制度性结构,特别是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制度性结构的事实。可在这种奇怪的“一般性理论”里,诸如此类的支配结构却不见踪影。
在他提供的术语里,我们无法恰当地提出以下经验性问题:在任一给定情况下,制度在何等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得到合法化。宏大理论家们提出的规范性秩序观念,以及他们处理这个观念的方式,都引导我们假定,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得到了合法化。事实上,在社会系统里,“各种角色期望之间的互补性一旦确立,其维持就不成问题……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机制来说明互补的互动取向如何维持”。
在这些术语里,有关冲突的观念无法得到有效的梳理。结构性的对抗、大规模的反叛乃至革命,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它假定“系统”一旦确立,就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本质上就是和谐的;用帕森斯的话来讲,混乱必然是被“引入系统”的。规范性秩序这个观念引导我们假定各种利益之间存在某种和谐,并将其视为一切社会的自然特性。在此体现出的这种观念和探讨自然秩序的那些18世纪哲人的观念颇为类似,都仿佛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点。
魔术般地清除了冲突,奇迹般地达成了和谐,就从这种“系统性”“一般性”的理论中去除了处理社会变迁和历史问题的可能性。我们的时代充斥着受恐吓的大众的“集体行为”,充斥着被挑动的暴民、群众和运动,但在宏大理论家依循规范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当中,这些却都找不到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没有任何有关历史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它的机制和过程如何的系统性理念,可以用于宏大理论中,帕森斯因此认为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这种理论产生之日,也就是社会科学的千禧年降临之时。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有这一天了,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当然,这个断言本身相当含糊。
以宏大理论的术语来讨论任何实质问题,几乎都不能得到清晰的陈述。更糟糕的是:它的陈述不仅老是被海绵一般语义笼统的词语弄得含混不清,而且往往负载着立场评判。比如,用“普遍主义—后天获致”(universalistic-achievement)这一“价值模式”(the value pattern)的术语来分析美国社会,却毫不提及成功在现代资本主义下所特有的那些变动不居的性质、意义与形式,或是资本主义本身结构的变迁;又比如,用“支配性价值系统”这个术语来分析美国的分层,却不考虑基于财产和收入水平差异而形成的已知的生活机会的统计分布,很难想象比这些更加徒劳无益的努力了。
即使宏大理论家们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讨论问题,讨论所采取的词汇和角度也在宏大理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并且往往与宏大理论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么说并不为过。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尝言:“事实上,帕森斯如此费力地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分析变迁,不经意间诱导他列出了一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预设,让人困惑不已……这看着几乎像是保留了两套书,一套用来分析均衡,另一套用来探究变迁。”古尔德纳继续评论道,帕森斯在讨论战败后的德国这一个案时,建议彻底摧毁容克贵族,视之为“排他性阶级特权的案例”,并从“征召新人的阶级基础”的角度来分析公务员考试制度。简言之,整个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突然就进入了视野,并且是从颇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从宏大理论所规划的那种规范性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的。这倒使人产生了希望:宏大理论家还没有彻底丧失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联。
五
我现在回过头来谈谈秩序问题。用颇具霍布斯色彩的形式来表述的话,秩序似乎是帕森斯这本书里的主要问题。这方面可以简略带过,因为它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已得到重新界定,至于其中最有用的陈述,现在不妨称之为社会整合问题。当然,后者需要给出可操作的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观念。我认为,与宏大理论家不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会给出类似如下的回答:
首先,是什么将一套社会结构维系一体,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社会结构的统合程度和统合类型千差万别。事实上,可以从不同整合模式的角度有效地领会社会结构的不同类型。一旦从宏大理论的层次下降到历史实在,我们马上就会认识到,宏大理论的那些大一统的概念无关痛痒。我们没法靠这些概念来思考人的多样性,思考1936年的纳粹德国、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1836年的美国、1866年的日本、1950年的英国、戴克里先(Diocletian)治下的罗马。我提及这样的多样性,无非就是想表明,无论这些社会可能有怎样的共性,都必须通过经验考察来揭示。如果超出空洞无比的形式范畴来对社会结构的历史跨度做出任何预测,就是把自己高谈阔论的能力错当成社会调研工作的全部意味。
人们可以从政治、亲属、军事、经济、宗教之类的制度性秩序的角度,有效地领会社会结构的不同类型。可以以特定的方式界定这些制度性秩序,以便能够在给定的历史社会中辨识出它们的轮廓,然后再问各个制度性秩序是如何彼此关联的,简言之,即它们如何组合成一套社会结构的。为方便起见,可以把这些答案弄成一组“操作模型”,用来让我们在考察特定时间的特定社会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它们是靠哪些纽带“维系一体”的。
要想象这样一种“模型”,不妨从每一个制度性秩序中提炼出类似的结构性原则。以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为例,在那个经典的自由主义社会里,每一个制度性秩序都被设想为是自主的,而其自由又需要其他秩序的协调。在经济领域中,通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在宗教领域中,多种多样的教派和教会在救赎市场上公开竞争;在婚姻市场上,设立了多种亲属制度,个人也在这个市场上相互选择。在地位领域,占据上风的人不是靠门第显赫,而是靠自力更生。在政治秩序里,存在的是争取个人投票的政党竞争;甚至在军事领域里,招募国民自卫队时也有相当的自由,大体可言全民皆兵,这种意涵其实非常重要。所谓整合的原则,亦即这个社会的基本合法化渠道,就是在每一个制度性秩序中,占据主流的都是彼此竞争的独立的人的自由进取精神。正是透过这种契合的事实,我们可以理解一个经典的自由主义社会是如何统合一体的。
但这种“契合”(correspondence)只是一种类型,只是对于“秩序问题”的答案之一。统合还有其他的类型。比如,纳粹德国就是通过“协调”(co-ordination)整合起来的。这种整合的一般模型可以阐述如下:在经济秩序中,各项制度高度集中化,少数几个大集团差不多控制了所有的经济运行;而在政治秩序中,分裂程度更大一些,许多政党相互竞争以影响国家,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足够的力量以控制经济集中化的结果,后者的结果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与其他因素一起造成的萧条。在经济萧条中,纳粹运动成功利用了大众尤其是中下阶层里面弥漫的绝望情绪,使政治秩序、军事秩序和经济秩序形成密切的契合。一个政党垄断并重塑了政治秩序,废除或合并了可能拥有竞争权力的其他所有政党。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纳粹党找到它与经济秩序中的垄断集团之间、与军事秩序中某些精英群体之间在利益上的一致点。在这些主要秩序里,首先存在着相互契合的权力集中;其次,每个秩序都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保持一致,彼此合作。兴登堡(Hindenburg)总统的军队对捍卫魏玛共和国不感兴趣,也无意于镇压一个深得民心的主战党派的行进纵队。大工商集团乐于资助纳粹党,后者承诺颇多,特别是承诺要粉碎劳工运动。这三类精英结成往往不太和谐的联盟,以维持它们在各自秩序中的权力,并与社会其他秩序相协调。作为对手的政治党派要么惨遭镇压或被宣布为非法,要么自动解散。至于亲属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和所有秩序内部及之间的一切组织一样,都受到侵蚀和协调干预,至少是被中立化了。
这三个占据支配地位的秩序中的高层角色,以极权主义式的政党国家为手段,协调自己的和其他的制度性秩序。这样的国家成了笼罩一切的“框架组织”,将目标强加给所有制度性秩序,而不只是确保“法治政府”。政党自我扩张,借助各种“辅助组织”和“附属组织”四下蔓延。它要么无限分裂,要么肆意侵蚀,总之会逐渐控制所有类型的组织,就连家庭也不能幸免。
所有制度的符号领域都受到政党控制。宗教秩序稍有例外,其他领域中则不允许存在任何对于合法自主性的对抗诉求。政党还垄断了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正式交流渠道。所有符号都被重塑,以筑造协调一致的社会的基本合法化。在一套相当程度上由结党营私的网络维系起来的社会结构里,严格等级制下具备魔魅的绝对领导原则(即克里斯玛统治)得到广泛宣扬。
不过,至此肯定足以表明我认为显而易见的一点结论:总而言之,没有任何“宏大理论”,没有任何普遍图式可供我们作为出发点,以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体性;对于老旧的社会秩序问题,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要想有效地探讨此类问题,就得依循多种操作模型,就像我刚才勾勒的那些一样。在使用这些模型时,也要立足经验,密切结合古往今来广泛多样的社会结构。
还可以把这类“整合模式”设想为有关历史变迁的操作模型,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如果我们观察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社会,再看看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立刻就会看出,19世纪结构的“维系”方式迥异于当前的整合模式。我们会问:它的各个制度性秩序是怎样变迁的?这些制度性秩序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变迁的?这些结构性变迁的节奏即速率变化如何?在每种情况下,这些变迁的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分别是什么?当然,找寻充足的原因,通常要求除了历史的研究,至少还需要有些比较的研究。我们可以用总括的方式,概括这类社会变迁分析,并就此更经济地梳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点明变迁导致了“整合模式”的转换。比如,最近100年的美国历史展现出,美国从大体上通过契合整合起来的社会结构,转换成了更多通过协调达成整合的社会结构。
历史理论的总体问题脱不开社会结构理论的总体问题。社会科学家在从事实际研究时,若以统合的方式理解这两个方面,则并不会遇到什么理论上的重大困难,我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一本《巨兽》的价值抵得上20部《社会系统》。
当然,我摆出这些观点,并不是要对秩序和变迁问题,也就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的问题给出什么定论。我只是想勾勒这类问题的大致轮廓,点出一些已有的相关研究。或许这些观点也可以用来进一步明确社会科学的承诺的某一特性。当然,我在这里提出这些观点,是为了点明宏大理论家处理社会科学的这一重大问题时是多么不够完善。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之所以未能踏实触及社会科学实际研究,是因为他满脑子想着自己已经构建出的社会秩序模型属于某种普遍模型,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对自己的“概念”盲目崇拜了。这种宏大理论的所谓“系统性”,就在于它撇开了任何具体经验问题的方式。它并不用来更精确或更充分地阐述任何具备可辨识的重要意义的新问题。发展这样的理论,也不是有什么需要要暂时高飞,以便更清晰地察看社会世界中的什么东西,以解决某个可以从历史现实的角度陈述的问题,而人和制度在这样的历史实在中,自有其具体的存在。它提出的问题,它推进的过程,它给出的解答,都是宏大理论式的。
回撤到对于观念的系统性研究,应当只是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一个形式环节。有必要提醒大家记住,在德国,这类形式研究的成果很快转向了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性的运用。那种运用笼罩在马克斯韦伯的精神之下,是德国古典传统的巅峰体现。在相当程度上,促成这类研究的正是一大堆特别的社会学研究,它们有关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与历史阐释有着密切关联。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马克斯韦伯就像其他众多社会学家一样,在与卡尔马克思的对话中推进了自己的许多研究。但我们始终得承认,美国学者是健忘的。在宏大理论中,我们现在碰到了另一场形式主义的回撤。同样,这本来也只该是一次暂歇,却似乎已经成了永恒。就像西班牙的那句谚语说的那样:“许多人洗起牌来好花哨,玩起牌来太糟糕。”
第三章 抽象经验主义
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一样,也是抓住研究过程中的某个关节不放,任其支配头脑。两者都是在社会科学的任务面前的退缩。要完成我们的任务,有关方法和理论的考虑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这两种风格下,这些考虑却成了障碍。相比于对于“概念”的盲目崇拜,方法论上的约束可谓不遑多让。
一
当然,我并不打算全盘概括抽象经验主义者所有的研究结果,而只是想揭示他们研究风格的总体特征及它的某些预设。公认的以这种风格进行的研究现在往往会陷入多少有些标准化的模式。新的学派在实际研究中,通常会对经过抽样程序选出的一系列个人进行多少属于固定套路的访谈,以作为其“数据”的基本来源。这些人的回答被逐一归类,并出于方便起见,被转制成霍勒里思代码卡片,然后研究者用这些卡片进行统计,由此寻求变量关系。这样的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任何一个才智平平者也能学会程序的那种轻松,无疑就是其魅力的主要原因。依照规范,结果会表现为统计判断:在最简单的层次上,这些具体的结果属于定比判断;而在较为复杂的层次上,对于多个问题的回答会被组合成往往很繁复的交叉分类,然后又以多种方式分解以形成等级量表。要摆弄这类数据有好几种复杂的方式,但我们在此无须操心,因为无论复杂程度如何,它们也依然是对于已显示的那种资料的摆弄。
除了广告和传媒研究,这种风格的研究的绝大部分主题或许就是“舆论”,虽说根本没想过重新阐述舆论和沟通的相关问题,视之为一块可明确理解的研究领域。这类研究的框架就是对于各种提问的简单分类:什么人在什么媒体上对什么人说了什么内容,有什么结果?对于核心术语的通行定义如下:
……所谓“公共”,我指的是牵涉的广度,即大数量人群的非私己、非个人化的情感与反应。公共意见的这一特征使我们有必要运用抽样调查。而我的所谓“意见”,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有关时事性、即时性、一般具政治性的议题的意见,还包括各种态度、感情、价值、信息乃至相关行动。要想以恰切的方式捕捉到这些东西,不仅需要运用问卷和访谈,而且需要运用投射法和量表法。
这些断言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把有待研究的无论什么对象与建议用来研究它的一套方法混为一谈。可能的意思大体如下:我打算使用的“公共”这个词指的是任何具有相当规模的总体,因此可以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既然“意见”是由人所持有的,要了解这些你就必须和人交谈;但有时候他们不想或不能告诉你,那你就可能得试试“投射法和量表法”。
绝大多数舆论研究是在美国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里做出来的,当然,也只关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段。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既没有更准确地说明“公共意见”的意涵,也没有重新梳理该领域的重大问题。囿于为它们选出的历史范围和结构范围,它们无法很好地完成任务,哪怕只是初步的探讨。
西方社会里的“公众”问题,是伴随着中世纪社会里传统的、习俗的共识发生转型而出现的。而在大众(mass)社会的观念里,它达到了今日的高潮。18、19世纪的所谓“公众”,现在正逐步转型为一个“大众”的社会。不仅如此,随着大多数人变成“大众人”,深陷相当无力的情境,公众在结构上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诸如此类的情状或许暗示着,在针对公众、公共意见和大众沟通的研究的选择和设计方面,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框架。这还要求我们充分陈述民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被称为“民主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民主”的社会。简言之,在这个领域,囿于目前践行的抽象经验主义的格局和术语,是无法陈述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的。
如果不结合某种结构背景,就无法充分陈述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的确在努力探讨的许多问题,如大众传媒的效果问题。如果你研究的人口/总体(population)“浸淫于”这些传媒只有差不多一代人的光景,那么无论研究有多么精确,又怎么能指望去理解这些传媒的效果?更不要说理解它们组合起来对于大众社会的发展的意义了。企图将“较多”和“较少”受到这种或那种传媒影响的个体筛分开来,可能是广告业非常关注的问题,但要发展一套有关大众传媒的社会意义的理论,却构不成充分的基础。
在这个学派有关政治生活的研究中,“选举行为”已经成为首要的主题。之所以选择这个,我想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容易用作统计调查。所得结果直白单调,与研究方法的精致、实施过程的精心相映成趣。搞一项全面彻底的投票研究,却毫不提及“拉选票”的政党机器,甚或干脆不提任何政治制度,看着这样的研究,政治学家们想来一定很感兴趣。而这正是《人民的选择》( The Peoples' Choice)的境遇,这部赢得适当声名的著名研究著作考察了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 County)1940年的选情。我们从书中得知,富人、农村居民、新教徒更愿意投票给共和党,而相反类型的选民则倾向于民主党,诸如此类。但对于美国政治的动力机制,我们所得甚少。
合法化是政治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当这门学科处理意见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议题时,合法化就更是核心问题。如果认真思量“意见”这个词,美国的选举政治就是一种没有意见的政治;如果认真思量“政治意义”这个短语,美国的选举政治就是一种多少没有具备任何心理深度上的政治意义的投票行为。基于这样的怀疑,有关“政治意见”的研究就显得愈发怪异。但是,针对诸如此类的“政治研究”,我们无法提出任何这样的问题,我希望上述评论也只是作为问题。这种政治研究应当是怎样的?它们需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需要有某种心理反思的风格,而这些都没有赢得抽象经验主义者的适当重视。事实上,绝大多数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也都接触不到这些。
过去20年左右的关键事件或许要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它的历史后果和心理后果限定了过去10年我们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的框架。我们目前尚未拥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的权威定论性研究,我觉得这一点有些奇怪;不过我们还是努力要把它概括成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战争形式,确定为左右我们时代的核心,这样的尝试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除了官方编撰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史录,最详尽的研究或许要算是萨缪尔斯托弗指导下对美军做的为期七年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证明,社会研究是有可能不关注社会科学的相关问题而具备行政管理上的用途的。当然,如果你希望理解美军士兵的有些战时表现,特别是要追问,怎么可能打了那么多胜仗的人却如此“士气低落”,那么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必定会感到失望。但要尝试解答这样的追问,会远远超出已获认可的那种风格的格局,而进入不足为据的“臆测”领域。
阿尔弗雷德瓦格特(Alfred Vagt)的一卷本的《军国主义史》( History of Militarism),以及S. L. A. 马歇尔(S. L. A. Marshall)在其《浴血男儿》( Men Under Fire)中为贴近战场男儿所使用的令人赞叹的报道技术,要比斯托弗的四大卷著作有更大的实质价值。
根据新风格进行的分层研究迄今尚未提出任何新的概念。事实上,其他研究风格中可资利用的核心观念还没得到“转译”,“社会经济地位”方面那些相当笼统的“指标”通常也就够用了。“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与阶级相对的地位的观念,以及在统计上颇具挑战性的韦伯的“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概念,这些相当棘手的问题在这种风格的研究者手下都没有什么进展。不仅如此,选择比较小型的城市作为研究的“抽样区”的做法仍然强有力地存在,许多方面极其糟糕,罔顾显而易见的事实:你不能把这类研究聚合加总,然后得出有关国家范围内阶级、地位和权力的结构的充分认识。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在探讨舆论研究领域的变化时,给出了一段特别的陈述,我觉得适用于抽象经验主义路线的绝大多数研究:
综上所述,(25年前与今日相比的)这些差异呈现出舆论研究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这块领域已经变得技术化、定量化、非理论化、条块化、特www.58yuanyou.com殊化、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和“群体化”,简言之,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行为科学,这块领域已经美国化了。25年前乃至更早前,作为对社会的性质和功能运行的总体关注的一部分,杰出的论家们以渊博的学识研究舆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置身于宽广的历史、理论和哲学角度,并撰写著述。而今天,技术专家团队针对特定主题实施研究方案并报告结果。20年前,舆论研究属于学术。而今天,它属于科学。
上文简短地勾勒了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的特征。我并不只是说,“这些人没有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那些实质问题”,或是“他们没有研究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说的是:他们研究了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但对于那些问题和回答的陈述都只是囿于任意武断的认识论中那些奇怪地自行强加的限制。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用词不慎: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方法论上的约束。凡此种种,意味着就结果而言,这些研究中堆砌着细节,却对形式关注不够。事实上,除了排字工和装订工提供的形式,往往也就别无其他形式了。而细节无论多么众多,也不会说服我们相信任何值得相信的东西。
二
抽象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风格,其特征并不在于什么实质性的命题或理论。它并不是基于什么有关社会或人的本质的新观念,也不是基于有关这些方面的什么具体事实。诚然,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一般都会选择研究某些类型的问题,也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研究,这都是可以辨识出来的特点。但这些研究肯定不是这种社会研究风格会享有如许赞赏的原因所在。
不过,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学派的实质结果的性质若如此,尚不足以构成据以评判的基础。作为一门学派,它是新的;作为一种方法,它的确有待时日检验;而作为一种研究风格,它现在还在逐步扩散到更全面的“问题领域”。
它最明显的特征(哪怕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特征),必然牵涉到它已经开始采用的行政管理机制,涉及它所征召和训练的学术工作者的类型。这套机制现在已经变得规模庞大,有许多迹象表明,它已愈益扩散,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学术管理人员和研究技术专家都是崭新的职业人士类型,他们现在与更寻常的教授、学者展开了竞争。
但是,上述种种发展趋势,对于未来大学的品格,对于自由人文传统,对于或许已经在美国学术生活中占据主流的那些心智品质尽管可能非常重要,却并不构成据以评判这种社会研究风格的充足基础。这些发展趋势的确有助于说明,抽象经验主义这种风格为何会魅力十足、声势日盛,其助益远超许多倡导该风格的人可能会承认的程度。就算没有别的作用,它们至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式,为半熟练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它们为这些人提供的职业生涯既享有老派学院生活的安定,却又不要求老派的个人成就。简言之,这种研究风格还伴生了一种行政大佬(administrative demiurge),对社会研究的未来及其可能的科层化都有重要影响。
不过,抽象经验主义的思想特征当中最有必要把握的一点,还是其践行者所持的科学哲学,以及他们奉行和应用这种哲学的方式。正是这样的哲学,既支撑了其所实施的那类实质研究,也支撑了它的行政机制和人事机制。无论是实际研究在实质内容上的单薄贫乏,还是这些机制表面上的需要,都能在这种特定的科学哲学中找到学术上重要的正当化辩护。
把这一点搞清楚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原本可能以为,既然一项事业如此高调地宣称要成为“科学”,哲学信条就不会在打造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占据核心位置;也因为践行这种风格的研究者通常似乎不会意识到,他们据以立足的是一种哲学。或许没有哪位熟悉践行这种风格的研究者的人会介意否认,这些研究者中有许多人满脑子想着他们自己的科学地位,最受他们尊崇的职业上的自我形象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社会科学方面各式各样的哲学议题自有主张,而其中有一点始终如一:他们 都是“自然科学家”,或者至少“代表着自然科学的观点”。而在更加精深的讨论中,或者在某个坦然微笑、备受称道的自然科学家面前,自我形象更有可能被简化成单纯的“科学家”。
在研究实践当中,抽象经验主义者往往显得更关注科学哲学,而不是社会研究本身。简言之,他们已经做的无非是倡导一套科学哲学,只是他们现在认为这就是所谓“科学方法”。这样的研究模式基本上属于一种认识论建构;在社会科学里,其最具决定性的结果就是方法论上的约束。我所说的方法论上的约束,指的是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梳理这些问题,都会受到“科学方法”相当严格的限制。一言以蔽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不过,说到底,这种状况可谓正合预期。此处所设想的“科学方法”,并不源于通常的也是恰当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经典路数,也不是对于这样的路数的概括。它基本上借鉴的是一种自然科学哲学,只是做了些为了方便起见的调整。
大体而言,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括两类努力。第一类努力中,哲学家们可以尝试考察社会研究过程的实况,然后对那些看上去最富前景的探究步骤进行概括,并使之统贯一体。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很可能会一无所获。但如果每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都对此有所努力,就会容易得多。而人人均应如此,也确实不无道理。迄今为止,这样的工作还少得可怜,并且也只是用于少数几种方法。第二类努力,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的风格,往往像是在努力以特定的方式重述和搬用自然科学的哲学,由此为社会科学工作打造一套规划和典范。
所谓方法,就是人们试图理解或说明某事时所使用的程序。而所谓方法论,就是对方法的研究。至于方法论所提供的理论,说的就是人们在自己实际研究时都做了些什么。既然可能存在许多种方法,那么方法论也往往需要具备相当的一般性,因此通常也不会提供具体的程序供人们进行实际研究,虽说它当然可以提供这些程序。而认识论比方法论的一般性程度还要高,因为做认识论的人操心的就是“知识”的理据和限制,简言之,就是“知识”的性质。当代认识论学者往往奉他们所认为的现代物理学方法为圭臬。他们往往会从自己对于这门科学的理解的角度出发,就有关知识的一般性问题做出问答。实际上,他们成了物理哲学家。有些自然科学家看起来对这种哲学工作抱有兴趣,但有些就似乎只是看个乐子。有些自然科学家赞成绝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的当前的模型,而有些则持有异议,但我们怀疑,其实有很多从事一线工作的科学家对此一片茫然。
我们被告知,物理学已经发展到如此状况,可以从严密的、数学化的理论中,推演出严密的、精准的实验问题。而它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认识论学者在自己建构的探究模式中设置了这样的相互作用。次序似乎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物理学家——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利卡普库什(Polykarp Kusch)已经公开表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叫这个名字的那些方法都可以用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概括。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的立场甚至更进一步:“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科学家的操作步骤的关键特征无非是最大限度地调用头脑, 不受任何拘限。”威廉S. 贝克(William S. Beck)则指出:“发现的机制尚不清楚……我认为,创造的过程与一个人的情绪结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要谈概括实在是个糟糕的话题。”
三
方法方面的专家也往往会成为某一类社会哲学领域的专家。有关这些人的重要之处,就今日的社会学而言,并不在于他们是专家,而在于其专业性的一项后果,就是推进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内部的专业化过程。不仅如此,他们在推进时,还配合着方法论上的约束以及可能体现这种约束的研究机构。他们的专业化设想,并不是依据“可以理解的研究领域”,或对于社会结构相关问题的某种观念而制订出的什么论题专业化方案。他们提出的专业化,单纯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管内容、问题或领域。这些并不是我的零碎印象,而很容易找到文档为证。
有关抽象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研究风格,以及抽象经验主义者在社会科学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迄今最直白的陈述出自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他也属于该学派较有资历的代言人。
拉扎斯菲尔德把“社会学”界定为一块专门领域,但不是基于什么独具的方法,而是出于它在方法论上的专门性。由此观之,社会学家就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专家。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这是社会学家的首要职能。当世间人事中一块崭新的领域即将成为经验科学的调查对象,他也将成为社会科学家的先遣军中的探路者。迈出最初步伐的正是社会学家。一方是社会哲学家、个体观察者和评论家,另一方是经验调查者和分析者的有组织的团队工作,而社会学家就是架通两方的桥梁。……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区分出看待社会研究主题的三种主要方式:个体观察者践行的社会分析,组织完备的经验科学,以及一个过渡阶段,我们称之为有关社会行为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学。……行文至此,似有必要插叙几句,谈谈从社会哲学到经验社会学的这种过渡期间正在发生些什么。”
请注意,这里“个体观察者”被奇怪地与“社会哲学家”并举。还要注意,这个陈述讲的不单单是某项学术规划,而且是一套行政计划:“人类行为的某些领域已经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其专门的名称、机构、预算、数据、职员等。其他领域在这方面尚未开发。”任何领域都可以被开发或“社会学化”。比如,“事实上,对于一门会关注人口总体的幸福的社会科学,我们甚至还无以名之。但没有什么能阻挡这样一种科学成为可能。相比于搜集有关收入、储蓄和价格的数据,搜集幸福等级得分并不更困难,甚至不会更费钱”。
所以,社会学作为一系列专门化的“社会科学”的助产士,处在两方之间:一方是尚未成为“方法”的研究对象的任何话题领域,另一方则是“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什么叫“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不过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只有人口学和经济学够格:“没有人会再怀疑有必要也有可能以科学的方式处理世间人事。百余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像经济学和人口学这样充分发展的科学,它们处理了人类行为的多个领域。”在这篇长达20页的文章里,我没有发现其他有关“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的具体陈述。
如果社会学被指派了负责将哲学转换成科学的任务,等于是假定或暗指“方法”的天赋才力如斯,并不需要对有待转换的领域具备什么传统学术知识。当然,掌握这类知识所需要的时间会比这个陈述中暗示的多一些。或许有关政治科学的一句不经意评论能点明个中况味:“……希腊人有一门叫政治学(politics)的科学,德国人谈国家学说(Staatslehr),英美人则说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直到现在,也没人做过出色的内容分析,让人能真的搞明白该领域的书都在说些什么……”
如此一来,一边是充分发展的经验社会科学家组织有序的团队,另一边是缺乏组织的个体社会哲学家。作为“方法论专家”,社会学家将后者转换成了前者。简言之,他是科学缔造者,学术与管理双肩挑,更准确地说,是“科学”与管理双肩挑。
“这场转变(从‘社会哲学家’和‘个体观察者’到‘组织有序、充分发展的经验科学’)通常的标志是有关学人的工作中的四种转向”:
(1)“首先,是从注重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向注重人的具体行为。”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将会在第六章看到,抽象经验主义并不是日常经验主义。“人的具体行为”可不是它的研究单位。这里我只点明,实践当中,牵涉到的选择往往会暴露出其明显偏向于所谓“心理主义”,不仅如此,还暴露出其始终在回避有关结构的问题,而偏好有关情境的问题。
(2)拉扎斯菲尔德继续写道:“其次,不是趋向于单单研究世间人事的某一领域,而是将其关联到其他领域。”这一点我以为并不属实。你只需要比较一下马克思、斯宾塞或韦伯的著述与任何一位抽象经验主义者的成果,就能看出并非如此。话说回来,这句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就看“关联”的特定意义:它仅限于统计学角度。
(3)“再次,是偏重于研究那些反复重现而非昙花一现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我们不妨认为这是试图指向结构性考虑,因为社会生活的“重现”或“规律”当然会附着于既定的结构。正因为这样,比如,你要想理解美国的政治选战,就需要理解政党的结构、政党在经济中的角色,等等。但这并不是拉扎斯菲尔德的本意。他是想说,选举需要有许多人投入一桩相仿的事情,而选举本身则反复再现,故此,可以用统计的方式对个体的投票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再研究。
(4)“最后,越来越强调当代的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这种非历史性的强调源于认识论上的偏好:“……社会学家因此倾向于主要探讨同时代的事件,因为他较有可能获得自己所需的那种数据……”这样的认识论偏向,相较于以梳理实质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取向,可谓截然相反。
在深入探讨这些观点之前,我必须完整引述有关社会学的这段陈述,据说它还有另外两项任务:
……社会学研究还要把科学步骤应用于新的领域。它们(拉扎斯菲尔德的看法)的设计宗旨就在于大致概括从社会哲学到经验性社会研究的转变中可能盛行的基调。……如果一位社会学家着手研究世间人事的新的领域,他必须自行搜集自己所需的所有数据。……社会学家的第二项主要职能就是结合这样的情境发展出来的。当此之时,他成了为其他社会科学制造工具的人。社会科学家不得不搜集自己所需数据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我不妨提醒你们注意其中几点。他必须经常去探问人们,他们做了什么,看到什么,想要什么。而被问的人往往不太容易都记得起来,或者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们,又或者搞不太清楚我们想要知道些什么。如此便发展出重要而难以精通的访谈技艺。……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家)还有第三项职能,即作为解释者……有必要区分对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interpretations)。在解释的层面上,我们主要会提日常语言用“为什么”来涵盖的那些问题。人们现在生孩子为什么比以前少了?他们为什么想从乡下迁到城里?选举为什么会赢或会输?……
要找出诸如此类的说明(explanations),基本的技术就是统计性的。我们必须比较多子家庭与少子家庭,比较常不上班的工人与按时到班的工人。但我们应当比较他们的 哪些方面呢?
社会学家似乎突然摆出一副真正无所不涉的姿态: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都包括解释和理论,但我们在此被告知,“解释”和“理论”本身就是社会学家的领地。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那些解释都还不是科学性的,这里的意味也就明了了。社会学家在将哲学转换成科学时所使用的那些“解释”,其实属于统计调查中很有用的“解释变量”。不仅如此,请注意在上述引文的紧接下来的一段中,倾向于将社会学的现实化减为心理变量:“我们必须假定,在人们的人格、经验和态度中存在某些东西,使他们会在由外观之一般无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行事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检验的说明性的观点和观念……”
而所谓“社会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了诸如此类的概念的系统辑录,也就是系统地搜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变量:
我们确实称这些概念是社会学性质的概念,因为它们适用于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我们指派给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搜集并分析这些概念,原由网它们都有助于解释特定领域中发现的经验结果,如分析价格、犯罪、自杀或投票统计数据。有时候,社会理论这个术语也用来指系统地呈现这类概念及其相互关联。
必须顺带提醒一句,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段陈述整体观之,究竟是属于有关社会学家实际已经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理论,还是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提议,建议社会学家应当成为助产士式的技术专家,成为万事万物的解释的监管人。如果是前者,它肯定是有欠缺的。而如果是后者,当然,任何社会学家都有自由侧重自己考虑的实质问题的利益而拒绝这样的邀请。但它到底是事实还是规诫,是陈述还是规划?
或许,它就是对于技术哲学的宣传,就是对于管理效能的崇拜,只是乔装成有关科学的自然史的组成部分。
有关研究的整体风格和社会学家,我所知最清晰的陈述就是:社会学家就该作为科学制造者、工具制造者、解释监管者,安居于研究机构。这就牵扯出我马上要更系统地讨论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