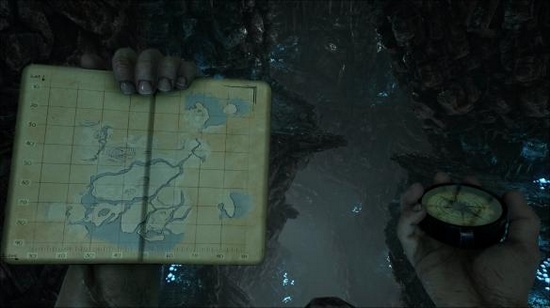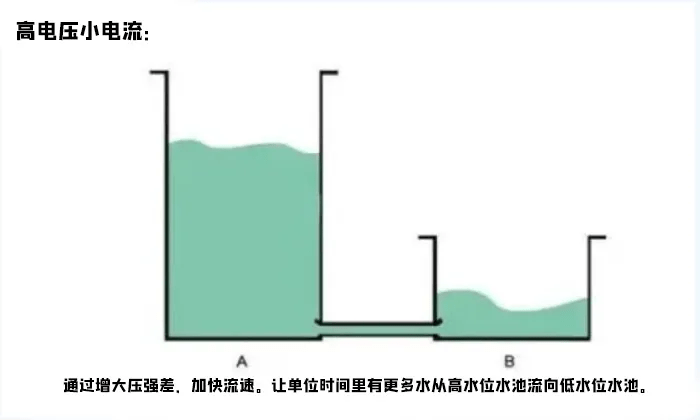继获得北京大学世界华文文学奖的作品《雨》之后,后浪文学今年出版了黄锦树的又一重要作品《乌暗暝》,为其两本出道作品合集,共收录二十一篇重量级作品。
这篇序言写于黄锦树的二十九岁,他彼时已修完博士班的学分,甫找到工作。他在本文中「也许透露了太多自传性材料,对自己却不无纪念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文中,「序里有若干争辩:烧芭、告别传统、身份困境、重写马华文学、重写马华文学史、个别作品对我个人的特别意义等,都做了颇为直白的解释。」对于读者而言,这篇序言不失为来自文学现场的可贵补充,为什么写?如何写?写什么?他有「非写不可的理由」。



//
最近偶然翻阅少作《M的失踪》 及自己当时写的得奖感言,惊觉一晃六年已然过去。那时还是彷徨前程的大学四年级生,以小说、感言等等形式在马华文坛放下的一把野火,到现在还在烧着,且时不时被我自己有意无意地在余烬残灰中重新引燃。刀耕火耨,早年耕作的经验——总要把旧有的枯枝败叶、老藤野草烧尽,翻扰故土,才能重新播种。志不在全盘否定老前辈们的努力,作品俱在,后人自有定评,我关心的毋宁是我们这一代该如何重寻出路。他们强调他们所留下的传统十分优良,后辈当宗之法之,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历史情势所造成的“不得已”,不能引以为通则。为此,不惜与马华文学传统彻底决裂。
而今,已有“马华现实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称我们的写作为“殖民文学”了。失踪的M,并非如某位评审同乡的误读,它不是圣诞节的马来译名(Krismas),而是以缩写的马来语表征的黄金马来剑(Kris emas)。和李永平、张贵兴一样,渐渐的已无法回头,不论写什么或怎么写,不论在台在马,反正都是外人。为今之计,也别奢谈什么“对历史负责”,能对自己负责就已经不错了。
收入集子的这些作品,有的是这两年写的,有的却“历尽沧桑”。《非法移民》是我最早的小说习作之一,由于屡遭退稿而历经无数次的修改,然而格局已定,似乎也没能变得更好。
把它收在这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纪念齐邦媛教授在我写作之初给予的莫大鼓励——已经是陈年旧事了,一九八八年参加同学会主办的“第五届大马旅台现代文学奖”,由于主办单位没有限制个人投稿作品篇数而赶制了一大包习作寄去。有的落选有的获奖。
在小说组,虽然是另一篇在这两本小说集中都没敢收入的习作得了主奖,原由网《非法移民//www.58yuanyou.com》却是齐老师耿耿于//www.58yuanyou.com怀、花了许多口舌为之辩护的“遗珠原由网”。对于写出的作品总觉得不满意,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如果没有一些前辈和文学奖的鼓励,是不可能持续写下去的。《大水》也是从大学到硕士阶段一再重写而老觉得不满意、老是落选、退稿,而后在《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又被做掉的旧作。故事的“本事”铭刻了一段不愉快的过去。《胶林深处》由于被不同的杂志社或把原稿丢弃、或压上超过一年,以致我也忘了写作的日期;相对于其他变成纸浆的作品,《蕉风》主编良心发现把它刊出对我而言是“失而复得”,因其时我手边已无底稿。《山俎》由于是片段组合,各切片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自然不一,横跨的时间也比较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本集子和上一本是难以分割的,不论在题材还是议题上,它们都是互补的关系;合并而观之,思考及摸索的痕迹斑斑可考。
和上一部集子类似,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胶林背景,甚至可以说,胶林几乎已是我小说写作的原始场景。原因很简单,在来台之前,我及部分家人就住在胶林中。家乡在马来半岛的南方,那个州有着美丽名字:柔佛。
有许多广袤的橡胶园油棕园,物产丰饶。不管官方公布的华巫财富比率统计数字如何,也不论有多少华人大老板以他们过人的财富刻板化了华人的形象,就个人所见,即使是在那么富足的州,一直到八○年代,算不上“小康之家”的华人家庭比比皆是。祖父母自中国大陆南来,父亲是土生土长的一代,而我则是国家独立后出生的一代,各自铭刻着不同的时间性。因某种缘故,父母亲一直都住在胶园,以割胶为生,守着祖父母毕生劳力和血汗结晶成的一小片胶园,孩子一个一个生下。毫无例外地,我们的童年都在胶园的荫影里度过,一直到学龄了才走出胶园,见识文明世界里的事物。在学校里把乳名换成学名,沟通语也从方言改为华语,和家人以外的人交往,识字。往往,半天在明亮的学校,半天在阴凉的胶林,进出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穿的衣服也是不同的。
从父母开始住进胶园,一直到搬出来的三十多年间,没有自来水,也没电。刚开始是土油灯、蜡烛,后来再加上大光灯,再后来买了小型发电机,才有日光灯,只是启用的时间有限,熬夜念书还是得靠油灯或烛光。我们常因考前开夜车而烧焦了头发,有时烧坏了桌子、板墙,偶尔还险险把房子也烧了。政府不是没有为乡区提供水电,水管和电线直奔马来Kampung(村庄)而去,吾家就因为“不顺路”而被排除在外。

从有记忆开始,对夜里的胶园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我家没有邻居,最近的一户人家也隔了好几块胶园,望不见对方的灯火。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除流萤外,家是唯一的一盏灯。仿佛随时伺机而出的恐怖就潜伏在那难以穿透的黑暗之中,虽然老虎狗熊之类的猛兽已不太可能出现,眼镜蛇、蝎子、蜈蚣等已构不成威胁,最怕的其实是人,陌生人。基于安全的考量,养了许多狗。不管多早或多深的夜里,每当狗儿厉吠,全家人都会顿时神经紧张地站起,准备好手电筒,再严重些,则是拿起部落时代的武器,戒备着。所以,常在睡梦中莫名地惊醒,常为黑暗中突然出现的灯火而紧张,因为谁也看不见谁。总会有一些宵小、赌徒、吸毒者(“白粉仔”)到处寻找下手的机会。家里也不乏女性,付不起疏忽的代价。
八0年代中期因为印尼非法移民大举入侵,官方也许因为种族(印尼人与马来人同文同种)的考量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许多印尼仔之所以频频上报就是因为他们打劫的频率极高,基于“华人比较有钱”的刻板印象,一般而言受害者都是华人 ,抢了钱不算,往往伴之以砍杀,强奸。
一九八六年我来到台湾。之前的几年,经济不景气,母亲常因忧愁而失眠。也狠狠病了一场。我来台来得勉强,然而如果不走,在马来西亚也许一点机会也没有。华人人口占三分之一,税照缴,可是在本地受高等教育、公费留学等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名额都保留给了马来人。高中快结束时,前途茫茫,更常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苦闷情境。如果不走,或走不成,也许这辈子了不起当上某个行业的“头手”。
然而台湾的中文系教育,却让人感受不到任何的血气和阳光,仿佛置身破烂的古墓,把弄文化的遗骸,与幽灵萤火共游。念大学的那几年,几乎夜夜都回到故乡的胶园,梦到收胶,在水井里捞到斗鱼,骑着脚踏车就可以回到家里……。日里夜里,都会担心家里的情况,然而却也无可奈何。
三年后第一次回马,对速度毫无概念的故乡的火车,把我送到家乡小镇时已是深夜,和亲人在烛光灯火中相对,真确地体会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欢乐的感伤。
收在集子里的《乌暗暝》和《非法移民》对我而言最大意义就在于相当程度地记录了我及家人多年胶林生活的恐惧,那样的写作绝不只是李天葆所谓的“把写坏了的题材拾掇起来” 而已,它凝结了极大的痛苦和无奈在里头。既然要写作,即使老是写不好,也非写不可。对我而言仿佛有着一种伦理上的强迫性。
在前引文中,同为小说写作者的我的同乡李天葆以相同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为基础进行解读,他相当敏感准确地道出了我写作时来不及去想(却时时思索关切)的、隐含的政治意涵。“胶林深处” 的生活,不正隐喻了大部分大马华人长期生活在敌意的环境下的无名恐惧?兢兢业业地过日子,任何时候,一瞬之间就可能让它化为乌有。有钱人可以四海为家,口中高喊维护华人权益,却置产国外,儿女都是小留学生,长大后是说纯正英语的“高级华人”。而小老百姓可是哪都去不了。
《乌暗暝》原来缺了个收尾,其时家人仍住在胶林,虽是写小说,心中却难免犯了忌讳,多年来恐惧发生、不希望发生的“结局”,即使是在小说虚构里,也不情愿让它化为真实。它的两个结尾《青月光》和《一碗清水》是在父母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因孩子一一远离不得已而从胶林中搬出来后才补上的。
一九九五年回马结婚,相当感伤的发现胶林也许真的回不去了。没有人住的房子,承受不了时间的剥蚀,其衰朽是直接而浮露的。往年回家,总是午夜抵达,睡在胶林的家的木板床上,夜里多雾、多露水,如秋日般凉。除许多虫鸣以外,总是可以听到远方猫头鹰“咕……咕”地阴阴地叫。
第二天早上在母亲锅铲声中醒来,犹以为身在台湾,做着回乡的梦。搬出来镇子后,父亲仍然风雨不改地每天一早进去胶林,为他心爱的狗群张罗吃的,锄草,照顾胶树砍除后种上的果树,一直到天黑了才出来。母亲说,即使是新年也是如此,“怕他的狗会饿死”。儿子结婚也是如此——唯提早进园去,提前出来。多年以后,那曾经是家的地方必定渐渐失去它原来的形貌;也许——写作就像是照相定影的作业,为回忆的依据找寻一个徒然的居所。
从恐惧到写作,《胶林深处》自有其现实参照,不过并无恶意,作为写作者的马华作家处境相当不容易,谨以本文向那些默默写作而不整天叫嚷“汝辈不肖”的前辈致意。而从隐喻到直接去触及,从夜的恐惧到政治遭遇,不过是一步之遥。
《鱼骸》《山俎》《血崩》《貘》《说故事者》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旧题重写”,因为前辈对这些题材都写得十分粗率,往往草草了事,或语焉不详。作为写作者,这些题材都非身之所能及,比较上是比我大上十岁、二十岁的兄长辈,或更为年长的父祖辈那一代的记忆。


记得上一本小说集出版后,时任中时开卷周报记者的朱恩伶小姐,在访问中提及我这一代的马华作家和当代大陆先锋派作家余华他们有一个共同处,都在“搜寻”上一代的恐怖、受创记忆。旨哉斯言。余生也晚,赶不上那个年代,只有以一种历史人类学家的研究热诚,搜寻考古,捕风捉影,定影成像,凿石为碑。这一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和任何文学风潮无关,只因非写不可——在重写马华文学史之前,必须(在某种形式上)“重写”马华文学。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会试着写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前提是它能保持写作原有的浓密度。要不,纯粹为了比长比多,绝比不过大陆作家。
家所在的居銮(Kluang,在马来语为蝙蝠之意)县在马来西亚成立前后一直是大马南方左翼分子活动的重心之一,是一个非常黑的“黑区”,郊区的大部分园丘,大概都曾留下那个时代之子的血汗和足迹罢—虽然大部分华人迄今仍讳莫如深,视为禁忌。
我们是被时代阉割的一代。生在国家独立之后,最热闹、激越、富于可能性的时代已成过往,我们只能依着既有的协商的不平等结果“不满意,但不得不接受”地活下去;无二等公民之名,却有二等公民之实。
同为写作者,我是多么羡慕李永平那一代,也曾去函建议他回头去写那丰沛不下于南美的大东马,惜乎他的内心仍未解严。也因为曾久居胶林及对历史的着迷,所以才对王润华《南洋乡土集》那种轻飘飘、欢乐童年、未识愁滋味的胶林书写感到极端地不耐烦,彼氏虽言《天天流血的橡胶树》,却有胶而无血无汗。然而他那个年代,却正是《鱼骸》、《山俎》所想象的革命流血杀头的年代。
也许因为如此,部分篇章并不刻意避开华人普遍化的种族情绪——在大马,出于某种政治禁忌,或为了表现出华人“和解”的诚意,种族情绪在文学作品中若不是刻意地被避免,就是消融在种族和谐的期望中 。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如此理想,和马来知识青年永远存在的排外仇华情结一样,长期(也似乎永远)得不到平等对待的族群不可能都像“圣人”那样的超脱世俗,以德报怨。当然也不该以复仇之心牢记过往的种种,而无条件的遗忘毕竟是乡愿。该做的不是去遮蔽问题,而是必须把历史化的当代问原由网题重新当代——历史化;对于华人意识深层里的“中国情结”也是那样,它并不比乡土虚构。如果把这些都抽离,华人的存在便是不可理解的抽象存在。
收入集子中的作品或多或少的都做了些文字上的修补更动。虽然某些作品颇得到一些掌声及“市场”上的成功,不知怎的,仍旧不觉得怎么满意。也许理想的作品总是在未来,如今完成的,不过是阶段性的目标。“得奖”和不得奖一样,都有其偶然性。多年前有朋友预言,以大马为背景的写作在台湾参赛,了不起得个佳作。因此,机运和偶然确实已帮了我很大的忙。对于我,得奖确实有许多现实的用处——至少有人邀稿了——虽然有的邀了还是照退。
或许参加文学奖对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投稿方式,它的好处是即使被退稿,也已经过一个比较公平严格的汰选程序;它也驱使疏懒的我快点把蛋给孵出鸵鸟来。同时,奖金也可以让我活得不致那么穷窘,补助我回乡,娶妻。另一方面,对久居小镇的家人而言,那也算是一种荣誉吧。犹记那年千辛万苦拎着沉重的联合文学“雏凤奖”奖杯抵达家门,好奇的父亲把它拿去“过磅”,以他平日客串摆地摊卖自己种的土产所用的磅称,满布皱纹的脸上露出近似孩童的顽皮的笑:“两公斤七百(克)。”
谢谢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先生及陈素芳大姐,在这文学不景气年代出版这本不可能卖钱的书。谢谢提供发表园地的诸友朋。谨把此书献给曾经一道住在胶林中的家人、目前仍居住在胶林深处的大马华人,及多年来共同客居斯地、“相依为命”的妻。
- end -
点击下图即可购买《乌暗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