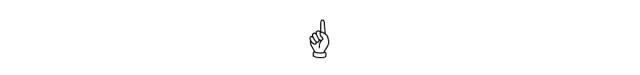原载于《山东文学》,1991年第8期。
作家简介

王方晨(1967——),山东金乡人,中国作协会员。1988年初登文坛,现供职于《当代小说》编辑部。已发表中短篇小说近200部(篇),共计60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乡土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录》)、《水洼》《十日书》,中短篇小说集《王树的大叫》《背着爱情走天涯》《祭奠清水》等,共计600余万字。作品先后近百次入选多种文学选本及文学选刊,长篇小说《老大》曾在台湾出版,并有作品被译介海外。
响桶

在人们的期望中,这个已死的人是会很快从他生活过多年的小镇上消失掉的。但至今为止,他的高大的身躯,似乎还在小镇的街巷里走动着。人们几乎看得见他那顶黄色麦秆草帽下的眼珠子,圆鼓鼓的,像玻璃球一样,不停地跳来跳去。谁也不怀疑眼前那个站在路边等待汽车开过去的魁梧的人就是犹所长。汽车开过去了,路面上的灰尘冲天而起,掩住了他,但是一会儿过后,他仍旧会在尘土和阳光中向前行走着,迈着非常均匀的步伐,只要他不转过街角,或者走出小镇太远,他的那顶草帽就会一直被人看到。
犹所长已经死了七个月。去年冬季的一天,他走到田野里打野兔,开始有很多孩子跟在他的黑色长统猎枪下面。他把他们全赶回去,一个人走出很远。虽然冬季里野兔的皮毛换成了跟土地差不多的颜色,但是相比之下要猎获它们比在其他季节还要容易一些,因为浅浅的处在休眠期的麦苗不足以遮蔽它们的躯体,况且众所周知,犹所长的枪法在小镇和周围的村庄里是首屈一指的。
长得油黑的小小,就是那些被赶回去的男孩子中间的一个。他身上的那件棉衣是他爷爷的。他的跟他的头发一样黑的小手和胳膊深藏在袖筒里,为了捡起地上的东西,必须两只手配合起来才能做得到。他在孩子们中间跌跌撞撞。但是猛然间,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冬季的天空仿佛在发抖。孩子们立刻停止了吵闹和走路,转身向着犹所长消失的方向看。他们只看到展平的麦田,没有犹所长的影子和他的长统猎枪——许多孩子都渴望伸手摸一摸它呢。孩子们眼前出现一只狂奔出地平线的兔子,霰弹射来,兔子在枪声犹响的地平线上高高翻了几个跟斗,再起不来了。孩子们觉得犹所长打死兔子的情景就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耳畔只响起他的枪声,把耳鼓震得好响。这有什么用!大家一起叹了气,忽然一个孩子叫道:
“你害怕呢,小小!枪又不是打你在身上。”
小小的眼球白得像死人骨头,令人止不住出惊。在他的内心有一片空地,犹所长猎兔的枪声还在那里回响着,如同下雨。而在大家又掉过方向朝小镇赶去的时候,小小自己都觉得脸红。是呀,那个孩子并没有说错。犹所长的枪就像打中了他,打在他的裹着爷爷的大棉衣的小身体上。他爷爷把他的又黑又亮的身体叫作泥鳅呢。爷爷经常用粗硬的大手www.58yuanyou.com抚摸他的身体,口里说着“泥鳅泥鳅,滑滑溜溜”,他就紧偎着爷爷,沉醉在那一片慈爱之中,如同钻进了夏天被阳光晒得热气腾腾的泥塘里面。
还没走进小镇,小小就听见了从爷爷箍桶铺子里传来的做工的声音。他兴奋了起来,跑到孩子们的前面,似乎远行归来,十分热切地希望早一刻见到爷爷。……路边的门口,摆着规格不一的漂亮的木桶和铁桶,还有一只被雨水淋得发绿的木桶悬挂在铺子跟前的木杆上。小小熟悉铺子里的一切。木杆上的那只木桶似乎从他一出生就已在那里悬挂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桶缘的铁箍已经生出了黑色的铁锈,但是木桶仍然没有裂出一道小缝。它仍然那样坚固。小小相信爷爷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箍桶匠,他为小镇感到自豪。
小小远远地看到自己的家了。瓦棚里蹲在长凳上的那个人正用小锤子敲打着一只木桶,他的头没有抬起来,但是小小知道那就是爷爷。
瓦棚的顶上刮过一阵风,发出的声音肯定能够传到爷爷的耳朵里。爷爷年纪很大了但一点不聋。不过小小总是对他大声说话,嗓门高得甚至能把从天上飞过的鸟儿吓一大跳。这样做两人都很高兴,说着说着还会哈哈大笑。天气如果潮湿而寒冷,爷爷在笑的时候可能止不住咳嗽,小小看着他脸上苍老的皮肤被咳嗽牵动着索索发抖,就替他难受。但是爷儿俩在一起不能不快活啊。
他家的房顶上长着很多草,到了这样寒冷的冬天已经干枯了。它们在瓦缝间瑟瑟摇动,似乎很难抵住寒风的袭击,不过冬天过去,春天一来,燕子飞回小镇,风也暖和了,它们又会发绿,长出新的鲜亮的绿叶,点缀小小和箍桶匠的家。
小小放慢了脚步,因为他发现在他家的桶铺附近有一个女人徘徊着。他断定她在等待他们走过去。她是镇上长得最好看的女人,人们叫她花。花的漂亮神气让男孩子们欢欣鼓舞,他们向她走过去了。小小躲在大家的后面,又忽然从他们中间离开,钻进爷爷正工作着的瓦棚里。
爷爷放下锤子,开始检查他的活计。他发觉孙子走了进来,但他没有马上跟他说话,因为他喜欢孙子突然向他大叫,那样他就会愉快地吃一惊。他想往常就是这样。
很对,往常是这样。慈祥的老人的注意力并不在手中的圆柱形的木桶上面,孙子嘹亮的呼叫声已经在他的欢喜的灵魂里响起来。在那片园地里,有一朵怒放的鲜花,还有一只大彩蝶在花朵上盘桓飞舞。
但是那样的声音并没有如他预料的那样响起,那鲜花和五彩缤纷的蝴蝶一刻一刻地模糊着,浅浅地溶入一片青白里面。他只好向孙子掉过头来。
小小正躲在他身边的木料堆后面向棚外凝神注视着。孩子的嘴微微张开。
“你来的时候可像只兔子呢!”老头儿大声向他说。
小小好像没有听见,依旧望着棚外不远的花和她周围的男孩子们。
花就要离开了。那些男孩子也一个接一个地散去。
老箍桶匠的目光随着小小一起投向他们。过了一阵,人走光了。风从路上吹过,卷起干燥的尘土,尘土贴着地面跑,发出摩擦的音响,好像手在揉搓着脸,因为在冬天里,那路面也跟着季节老了。
“你说什么呢,爷爷?”小小这才说,从棉衣袖里探出一小截手指撩一下眼皮,他觉得眼睛很累的时候,这样一撩就好了。他看着爷爷净是皱纹的脸,感到自己的目光正被爷爷温和的目光盯着。
“说你是兔子呢。”老头儿爽朗地笑着说。
小小叫起来,走出木料堆。
老头儿和孩子相视而笑了。老头儿用粗粗的手指头碰一碰孩子的黑脸蛋儿,在上面留下白色的道道,又很快地消失到孩子的黑色皮肤里面去。他的手指在不用力的时候也弯曲着,但是它们在使用起来时是异常灵活的。就是这双手,他用来箍了数不清的木桶。老头儿干这活计快一辈子了。他做好的木桶送给小镇上的人们使用,到了集市的日子,还把它们卖给赶集的农民。农民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小镇上有一个箍桶的老头儿。这老头儿做出的铁皮水桶也照样好,青年的农民喜爱买他做的白铁皮水桶。
“你总在不停地干活,”小小对老头儿说,“你会累坏的。”
老头儿对孩子的话不以为然。唉,老头儿干了一辈子活,整日蹲在工具前面,脊背一点不弯,他挺硬朗的。他苍老的眼睛像太阳一样,永远快活,充满热情。老头儿甚至不会想到自己还会衰老下去,以至于死掉,因为他是跟他的幼小可爱的孙子生活在一起,他也变得年轻了。小小生下来的第二天就没了母亲,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红通通的肉团呀,皮肤像羊羔一样软。他也是老头儿亲手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原因是这孩子想冲进这个世界的念头来得太突然了,别人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他就急急忙忙了。老头儿和那虚弱的产妇以为他不会活下来的,结果产妇过早谢世了,而孩子却欢欢喜喜地留了下来,长得一天比一天壮实。老头儿跟小小相依为命地生活了好几年,他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少年、青春。老头儿心里满是力量。
“这是谁家的活计?”孩子指着老头儿身边的水桶说。他从地上发现了一截断开的铁箍。
老头儿告诉他是伯明家的。伯明昨天晚上把盛了水的木桶放在院子里,结了一大坨子坚冰,把桶给撑破了。这可不能怨老头儿没把桶做好。伯明烧化了冰之后就把桶送来,老头儿用了半天时间才把它修好。但是老头儿不保证如果伯明那小子再不接受教训的话木桶又会怎么样,那么老头儿也就只好放下脸来说他几句了。想必伯明会接受的。“你去让他来取桶吧。”老头儿说。
小小盯着木桶看了一会儿,他在心里估计着木桶的重量。他说,“我去送到他家里吧。他在橡胶厂烧火炉呢,火通红通红,刺人眼,人都不敢总那样瞪着眼看,烟囱里的烟能飘很远。”
老头儿果真在空气里闻到了刺鼻的烟味和臭橡胶气。
“你能行吗?”他用目光打量一打量木桶和自信的小小,那木头家伙向来对什么也不关心,看它的样子吧,好像在生气,生什么气呢?埋怨别人用它来盛水,并且把它的肚皮给撑破了,不过,那种恶劣事儿并不是常有的啊。那种事儿也只有伯明能干得出来,这个小伙子,他身上处处是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总是把事情搞坏。他有一次把橡胶给熬焦了。
“算了吧,小小,”老头儿道,“那桶都快比你高了,你要是能给镇上的人办点大家称道的事,还必须再活过你这一点点的年纪,——比我小一半,就行。”
小小已经准备提桶了。他对爷爷小看他而感到很生气。
“伯明下了班会把桶捎走。”尽管老头儿这样说着,小小也已把木桶提得离开了地面,桶吊子像一只鸭子在低声叫。他不理会爷爷怎么说,因为这事情是他自己想干的。他向棚外走去。
老头儿脸上的皱纹和眉头舒展到最大的限度。他的孙子会把这件事做成功的。
小小走出去了,趄趄趔趔的像只会走路的桶。
“早一点回来,孩子!”老头儿大声叮咛道。他通过孩子的头部看到刚才花站立过的地方。如果现在花还站在那里的话,他就要跟她打招呼了。老头儿看到花总要想到一些事——那都是些年轻时候的好事。他想到了跟他生活过多年的妻子,她也是跟花一样漂亮的女人。她是他用彩轿子从村庄里抬来的。他们有过许多幸福的日子。有一件事老头儿不能够告诉给镇子上的任何一个人,他感到花长得有点像他年轻时候的妻子,——甚至可以说她很像他年轻时候的妻子。他怕犹所长知道这件事以后会发怒。
老头儿的思绪又走进过往的快乐的年代里。他忽然想,再想这些事有什么用!花毕竟不是他的妻子,而且,他的确老了,老得在梦里总是只能眼看着别人奔跑,即使见到当年的妻子,他也不能再那样亲热了,两个人好像不认识似的,相互盯着看,盯着盯着,就流泪。泪水下来,伸手摸摸,不湿。而且两个人连话也不想说,只听着嘡嘡、嘡嘡的什么在响。他觉得身体也好像不在一块,把器官连在一起的那些线都断了,他在逐渐地变轻,变轻,从那种顶天立地的大树,变成秋后飘零的黄叶,又从黄叶变成一点气,化为一个影子,在星光中倏地消逝。
花刚才站着的地方不远就是镇上的台球室。老头儿从瓦棚宽敞的门口,可以看见台球室里绿色的平坦的桌面和桌上圆溜溜的台球。有人在里面聚精会神地打台球。他们形成一种规矩,玩的和看的都不乱说话。老头儿如果留心听,还可以听见台球轻轻的碰击声和台球手的叹息。
他不由得摇了摇头。他把目光从台球室的桌面上收回来,放在孩子刚才隐藏的地方。木料堆里有清洁的优质的桐木。
小小在花尚未离开的时候表现很怪。老头儿想到的就是这个。
天黑下来了,老头儿丢开活计。镇上有些老头儿来找箍桶匠说话。他们的声音街上的人也能听得见。老头儿在一起,总讲年轻时候的事。他们在一块抽烟。今天他们都高兴,还在一块喝酒。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的,他们不去台球室看青年人打台球。在他们看来,那是顶没意思的。
小小坐在老头儿们中间。他细心地听他们讲话,但从不乱插嘴,因为如果他说错了话,别人就会拿他开玩笑,让他的面子过不去。有一个爱寻开心的老头儿还故意模仿着他的嗓音,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难为情得都想从他们中间逃掉。不过,他很喜欢从他们善良的目光中看出爷爷正受着大家的尊重。房子里烟味儿呛人,酒气也很像细小的蛇,游行在迷蒙的空气中,让没喝惯酒的小孩子鼻孔里痒痒,不时打呵欠。
他终于感到脑袋沉甸甸的了,里面有一盏忽明忽灭的小灯笼在来回地跳跃。在老头儿们的声音中间他就要睡着了,他把头靠在爷爷的胳膊上,一动不动。
老头儿们的嗓门压低了,一起把目光投向他。他爷爷对大家望了一眼,就低声说:
“他就要长大成人了,我要看着他长大,帮我干活,我还要送他上学。”
老头儿们点点头:“你好福气。这是个仁义孩子,从小看大。他会成为好学生。”
“他把桶送到伯明门上。”箍桶匠自豪地说,苍老的眼睛里闪出动人的慈祥的目光。他轻轻摇动了一下孩子藏在肥厚的棉衣里的细小的胳膊,看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开始做梦了。”老头儿说。
老头儿调整了一下坐着的姿势,然后把孩子抱起来,口中拂拂的酒气喷在孩子脸上,孩子梦见自己摇摇晃晃地走进芳香的烂漫的花丛里。老头儿把睡着的孩子放在了床上,盖上棉被。火盆已经把被子烘得热乎乎的,老头儿伸进手去试了一下,几乎烫人。
大家继续喝酒,继续聊天,声音全部不自觉地低下去。又过了很长时间,老头儿们都觉得自己的话东一句西一句,根本凑不到一个问题上去。酒喝得起作用了。
老头儿离开箍桶匠家的时候,台球室里的灯还亮着,还有许多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在打台球。外面寒冷的空气迎面扑来,老头儿们感到脚下高高低低,站不稳就相互扶着,渐渐走散了。箍桶匠返回房子里,他就要搂着自己亲爱的小泥鳅休息了。他觉得很累,必须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还有活干。
孩子醒来之后就面带着惺忪睡意坐在床上,把两条光腿伸出温暖的被窝。
“木桶在格登格登走,里面装满了玉米和苹果。”他喃喃地说,“它像长了三条腿。”
“你说什么哪,小小?”老头儿正把木片和卷起的刨花投进火炉里去。
“那是梦里的事情。”
“最好现在不要说梦,”老头儿解释说,“现在是清晨哩。”
“爷爷,在你做的所有的桶里面,还没有一个会走,是不是?”
“是那样。”老头儿说,“要那样做必须懂仙术,我就要成神仙了。”
“妖怪也做得到吗?”小小感到爷爷的话很有趣味。
“妖怪嘛,当然。不过,我想,那样就不会有人来买我们的桶了。”
“为什么?你一直就担心桶卖不出去吗?”
火炉里一块木材叭的一声,爆裂了。一缕白灰飘扬出来,这还真有点奇怪。老头儿对着炉门嘀咕了一句。
“我有点担心。”他说的是实话。虽然他制桶的手艺优秀,但是近年来买他的桶的人却明显地少了,很多人情愿到商店里去买有颜色的塑料桶。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说不定他真可改行了。他还想说什么,但是他停住了,在火焰的哔剥声中侧耳辩听着从外面传来的声音。
“有人吵吵呢,爷爷。”小小开始在被子里穿他的棉裤。他急着走到街上去看出了什么事。
老头儿关好炉门,跟跳下床来的孩子一起匆匆跑到外面。物体上灰白的寒霜还没有完全融尽。太阳光也不显得温暖,它们的热量好像被空中的云气吸收净了。老头儿和孩子看到有一大群人高声叫嚷着跟在一辆胶轮车后面,还有一些人蓬头垢面地向车子追赶。站在台球室窗前的一个人发现了老头儿,向他呼喊着什么。老头儿一时间没闹清怎么回事,但是孩子已经飞离了他,加入到追赶车子的人们中间去。后来,孩子忽然又落在了人们的后面,徘徊不前。
老头儿从远去的人群中看到车上的两条沾满泥巴的腿。他想赶上他们,但是他跟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喂,所长怎么了?”一个刚走出家门的男人对他大声叫喊,“他们走得怪快的!”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人就从他身旁窜过去,差不多把他给撞倒。他看清了那人的黑靴子,坚硬的路面被那人踩得咚咚响。他让自己站稳了,发现这个急冲冲的人就是伯明。老头儿刚想喊住他,他却站住脚步,身子向前倾去,又摇摇地直起来。
伯明发现了留在路边的小小,便对他笑了笑,然后走到他跟前。
伯明从孩子的眼里觉察出了深重的恐惶,他好像沉陷入噩梦里,被恐惧吓呆了。伯明弯腰把他从地上举起来,像捡起一件什么东西,接着,他把孩子放在他结实有力的肩头,向前赶去了。
老头儿的腿脚可不如年青人灵便,但他不会服输的,正要坚持追赶的时候,忽然觉得从天上的云里降下一团暖意融融的灿烂的光辉,一刹间全部被包围在里面,连呼吸都很困难。老头儿双腿乏软,气喘吁吁。脸上如同有一片火在蔓延。
花便乘着那团光辉在不远处出现了。
老头儿掉过头来走。他根本不用抬头看,但他觉得越走离花越近。他忘记了身在小镇,脚下那条路要多长有多长。花在不停地闪射着光辉,不断地明亮。老头儿也以为自己全身透明,步伐有力,但是一定神,却发现已经走到自己的店铺前了。瓦棚前木杆上的那只桶像一只硕大的熟透的瓜,青灰色的瓦间的干草湿漉漉的,因为草上的霜已经完全融化了。老头儿脸上的热气逐渐一缕一缕地散去,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他默不作声地走进瓦棚,坐到活计跟前,丝纹不动,但他的眉宇间还带着花的芬芳和光辉。他流露不尽的幸福和喜悦。他眼睛里什么物体也没有,只有一团变幻无定的红光。
过了一会儿,老头儿从门口去看街道。他低声对自己说,“别人有了灾难,我不应该高兴才对。”他几乎悔恨起自己的自私来,那样得意忘形的心理真肮脏。老头儿的脸色开始变得很严肃,最终近于悲哀了。
“哪一个人把花叫出来的?”他想,“其实也真应该先把这事告诉给花。犹所长在镇上没有亲人。”
老头儿开始回忆看到犹所长在车上的情景。犹所长的腿都僵直了,那也许是天冻的,也许死了有很长时间了。他脚上净是泥巴,还丢了一只靴子,可见他还在地上挣扎过一阵。
“我还以为他昨天就赶回来了呢,原来死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不错的人。他对老年人还是那样和气,还给人们让烟抽。”老头儿想,他还没有动手干活。忽然他站起来,想起封闭的炉火。
还好,炉火快熄了,没把锅里的饭烧焦。
老头儿又走到那些散发着好闻的气味的木料堆前。他望着敞开的门凝神思索着。但是没过上两天,也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可怕的男人闯进了老头儿的视线。在他还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时候,他听到瓦棚上的瓦片在滑动,好像有一只大猫在上面爬。那只高悬的木桶第一次在他的耳边像鼓一样,通通地响了几下。老头儿惊恐甫定。
小小在里面房间的床上低声呼唤他。他这才镇静下来,拐身走过去,但是一条腿忽然脱了力,险些撞倒在木料堆上。
孩子病了。伯明那天把他送到家里来他就有点异常,现在可怜的孩子疲顿无力,眼皮紫黑,闪着光亮。他不能把眼睛全睁开,只能做到让爷爷一个人走进他的眸子里。他连动都不想动,说话时脑袋在打颤,嘴唇上起了一层干燥的白皮,好像缺水。
老头儿心都快碎了。他强忍住眼泪,对孩子说:
“我再去请大夫,另一个要好得多。”
孩子虚弱地把目光投向老头儿。他微微笑了,但没有说出话。
“把大夫给的药吃了就会好,孩子,别急,一心躺着。”
孩子的肩膀在发抖,老头儿看见了,知道他想把手从被窝里伸出去。老头儿就从被子底下捉住了孩子发烫的手,孩子的肩膀不再抖了。他的嘴想吐出一个字,但只有气流在那儿打了一个涡,又消失了。
“想喝水吗,孩子?你肯定渴了。”老头儿重重地摇了一下孩子的手说。
“不是,”他口里产生声音了,模糊不清的,但是老头儿明白他的每一个字的意思。“你别怕,爷爷,”他说,“我明天就可以起床了,你千万别怕……我明天就能帮你干活,给你递钉。”
老头儿真想让自己的泪流出眼眶,可是,当眼皮一打开,竟然没有一滴眼泪。他对孩子咧开嘴笑了,口里最前面的两颗牙齿好像被风雨剥蚀的石柱子。
“刚才我听见什么在响。”孩子说。
“什么响……”老头儿吞吞吐吐地,“什么响也没有!你耳朵听错了。”
“不会错,爷爷。我还能听见地底下有水响,咕噜咕噜,蛤蟆在土里吹气,噗噗。”
“就这。”老头儿说。
“还有外面木桶响,像鼓,嘭嘭嘭。”
“真有‘嘭嘭嘭’,是有个坏家伙在敲着它玩儿。”
“我一直听着身边的动静。还有你的脚板响,踏——吃,吃。我喜欢听这些个呐。”孩子说。
老头儿猛然明白了。
“来!让我们听听收音机吧。收音机里会有人吹喇叭。”老头儿说着,走到墙下的桌前,掀开一片蓝布,露出下面的木匣子收音机,再用手指小心一拧,带着杂音的播音声传出来,听着好像从筛子里掉沙子。老头儿再要把声音调成喇叭叫,背后已走进来一个人。他的手伸在那里停住不动了。他转过身来,发现来人是花。
花神气清爽宁静,白色的皮肤一点看不出被户外的寒风吹过,好像她一直就是在这房顶下面的。
老头儿在自己流逝的青春时代里逗留了一瞬,马上醒悟过来。他问候了花一句。
花是来看望生病的孩子的。她把微胖的身体俯向孩子,孩子在花的美丽的目光中快活地笑了,乳白的牙齿像一粒粒晶莹的钻石一样。
花跟孩子说话。孩子像躺在阳光下的粼粼清波之上。他没有开口,他努力将半开的眼睛里的光集中起来,注视着花说话时的嘴。他的耳朵也没有让那从花口中吐出的一个音节逃走。他看到了碧绿的春水和跳动在水面上的光彩,听到水波相互撞击的声音和燕子的呢喃。
花向老头儿问了孩子的病情。她专门用猪油为孩子炒了嫩黄的鸡蛋,怪不得老头儿早就闻到那么浓的香气。
孩子一心想着花能够在他身边一直待下去,他就真正是一个幸福的孩子了。
老头儿不愿别人都来给孩子操心,他没把孩子的病说得像他认为的那样严重。而且他现在忽然觉得必须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亲骨肉,而是别人的痛苦。
“他怎么就死了,”老头儿诚恳地不无惋惜地说。他还在希望从花的眉间发现一丝哀伤。
“他死了。”
花的语气出人意料地冷淡。
“他是个好人。”老头儿说,“一个人的好处总比坏处多。”
花沉默着。
“枪膛自个儿炸的,怎么回事呢?世事无常呐,这样的事也会发生。”
花垂下眼皮。在眼皮的皱纹里有一道湿润的青痕。她又把眼皮抬起来,目光注视着眼睛一刻也没有从她美丽的躯体上离开的小小。
老头儿猛觉得一阵晕眩。他伸手按住自己的额头。青年时代又离他很近了,他一伸手就能摸得到。他想花一定不知道他很像他年轻时候的妻子。他感到一种迫切的愿望。
老头儿把手从额上拿下来。他就要亲口告诉花这件事了。但是他激动得说话都感到困难。句子已经到了嘴边,他预先领受到了倾吐这句话的快感。
“我又看到了犹所长。”
就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说出口的竟然是这个。
花转过脸来看他,似乎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今天早上,就是刚才,犹所长从我家门前走过去,不紧不慢。”老头儿接着说。
花惊慌失色地站起来,盯着老头儿激动的苍老的脸。她已经气喘吁吁的了。
“一点不假,我保证就是他。我差不多想跟他说话了。”老头儿回忆着。“他很快走过去。我听到棚上瓦响,木桶像鼓,嘭嘭。”
花脸上的惊惧消失了,沉静又出现在那里。
“我也许真老啦,眼花了。你可以不信。”老头儿说。
“木桶又响啦!”
床上的孩子叫道。花和老头儿一起听,听见了外面的人声和雄鸡的啼鸣。阳光从窗子纸上透进来。
“是这样。”花慢慢开口。那一份从容真难得。“我也看见了。”
“我们没有说犹所长的坏话,是不是?“老头儿说。
“是。”
“我们向来是不说别人坏话的。”
“他眼珠子崩出来了。”花的脸上露出笑意。
“真可怜!”
老头儿对自己的态度感到很满意。但是孩子的病却一直不见好转,老头儿甚至怀疑大夫对他隐瞒了一部分事实。他认为大夫对他说了谎,只是想安慰他这个不幸的老头子,编出好话来给他听。老头儿相信大夫对病人是会尽到最大的努力的,可是大夫隐隐约约地暗示他孩子没有必要进医院了。大夫只是按时来给孩子诊断,那也只是强把孩子的这条命多留在世间一个半个时辰吧。难道就没有指望了吗?
这时候犹所长的丧事还没有结束,老头儿也顾不得想到这个了。他也不知道镇上的人是否还在关心着这个死去的人。他只顾自己伤心,一粒饭也吃不下去。
镇上的人陆续来看望他和孩子。从前的那个充满快活的笑语声的店铺现在变得格外寂静。人们走进来都好像怕惊动了什么,小声讲话,宽慰老头儿痛苦的心,劝他进食。
可是那孩子呢?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连听人讲话的力气都没有,鼻息微微,闭着眼,又黑又瘦,他没有能够像他预想的那样很快走下床来,帮爷爷干活,给镇上的人们做做好事。他也好像把爷爷给忘了,把整个小镇也给忘了。这个世界——地底泉水咕噜响,地面上狗乱窜,天上风吹来吹去的世界给全部忘了。他沉睡在一个微微颠簸着的宁静的地方,在那里黑暗弥漫着。那些可怕的黑色的气流几乎把他给吞噬了。
人们也已经相信对于这孩子已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了。大家在想,这孩子一旦完了,那老头儿会一下子被击垮的。人们离开老头儿之后就忧心忡忡,必须想个办法使老头儿避免承受那即将www.58yuanyou.com降临的痛苦。大家都该伸出温暖的手,来补偿老头儿生活中失去的东西。
人们也明白,假如大家一味地欺骗老头儿,将孩子不会好转的真相隐瞒下去,那他的不幸就会变成突如其来的,就会一下子把老头儿带进绝望的深渊。镇子里的人凑在伯明就里一商量,决定将那种必定发生的危险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他,以缓解不幸给他的打击。
这几天镇子笼罩在一种沉寂的气氛之中。台球室里没有人再打台球。镇电影院里也不再放电影。这好像跟悼念死人有关。大家心事重重,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在老头儿的房子里,有人坐在他的木桶上,也有人坐在别的地方。这些人说了一会孩子的病,脸上就露出为难的神色。他们里面有老头儿的同龄人,都是老头儿要好的知心朋友,他们一个比一个善良。他们望着老头儿脸上痛苦的神情,都替他难过。他们这时候都又觉得如果告诉老头儿孩子没指望了,就好像不是死亡把孩子从老头儿手中夺去,而是他们亲手夺去的。谁也不忍心这么干。大家偷偷地交换着目光,甚至还在暗自埋怨。
伯明闯进来了。这么重大的事大家根本没想到让他插手,不是因为他没资格,而是因为他是个粗心的人。他进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几点白雪。外面下雪了。他抖着肩,让雪从衣服上落下去,大家心里真为他着急。
大家心里说,这回事情非得让他搞糟不可。
伯明走到老头儿近旁,望着昏睡着的孩子。他又拐过头来,朝大家面带急色的脸看一看。大家都在暗示他小心,可他一点不知觉。他只是想,老大爷挺住了。他以为大家已经按照在他家商量的那样做了。
“小小没有醒过吧。”他对老头儿说。
“没有。”
老头儿脸上又现出沉重的悲哀。
伯明是那么同情这个善良的老头儿。他想,老大爷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对老头儿肃然起敬。
“你要想得开,老大爷。”他说。
在场的每个人都有点骇然。
“谁说不是?”老头儿说。
有人在拉伯明的衣角。这真是个迟钝的人,他一点不理会,好像那不是他的衣角而是木头的。他想,看来老头儿已经承受住了那种打击。
“我们正在替你担心呢,老大爷。”他说着,扭头去看大家。这一下他忽然明白了,止不住一哆嗦。
老头儿抬起头来望着伯明年轻的脸沉思了一会儿。他也猛然醒悟了。
“我是不会像你们想的那样!”他有些激动,“我虽然年纪老大了,七十五啦,可我没有病,我还能活上七年八年。我什么活都能干,家里还有许多做桶的木头。我要把活干完。孩子呢?他能活下去,我会比他先死。我要是比我先走了,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还要活下去,七年八年不算多吧。”
大家都低下头。房子里很静,听得到大家思想的声音。老头儿却显得很兴奋。在他苍老而坚定的面容上甚至还有些动人的笑意,那是能够生活的由衷的喜悦。
等大家走光了,老头儿又悲伤起来。他是那么爱他的孙子呀!他想也许大家说得对,孩子快完了。他不愿意孩子这样离开他。
窗外可能还下着雪,因为窗子上有些灰影子一掠一掠的。老头儿走到炉火前,把火生旺。火烧红的过程中,老头儿伸出手去烤,他的手有点凉。
手也热了,火也烧红了。老头儿把烧着的木块拨到火盆里,放在孩子的脚旁,罩上烘篮。他要使孩子过得舒舒服服,只能做到这样了。接着,他伸出烤热的慈爱的手握住孩子的脚,它很快就被火盆烤热乎了。虽然老头儿手掌粗糙异常,但仍能感到孩子的皮肤光滑。
“孩子身体有点僵了。”老头儿止不住哀伤地想,“他不会再是那种活蹦乱跳的样子了。”
老头儿揉搓了一阵孩子的脚丫,这一会儿它变得柔软了一些。这使他意外地惊喜。他是不是能把孩子的身体重新变成一只滑溜溜的泥鳅呢?老头儿开始在被子下面揉搓孩子的小腿、肚子、胸脯和孩子的手臂。果然,孩子的全身再不像刚才那样吓人了。他有点像泥鳅的样子了。
也许是火盆里的火起了作用,孩子的身体上蔓延着热气。老头儿不再动他。“让他安静一些吧。”他想。
老头儿活动了一大阵子,有点疲乏了。他就坐在床上歇息一会儿。一闭眼,就觉得床在摇晃,觉得在半空中有一柱蜡烛在点着,将光照在他的孩子身上。接着,那床向后飘移,实质上他感到自己正向前缓缓地踱,但是一直没有踱出屋子。在屋子里的昏黄烛光里面,黑色的活泼的小泥鳅跳得满地都是,木桶上也有小泥鳅在翻跟斗。他觉得热闹极了,满怀信心地观看,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把这情景给吓没了。但是跳泥鳅越发乱闹了,竟朝他的脸上窜。他虽然爱让它们这样跟他耍,但终究受不住了,就去躲。他好像听见跳泥鳅儿在笑,细细地听,果真耳畔有声音。
他睁开眼。灯泡还在房顶下亮着。窗子上已没有灰影子。
老头儿知道自己睡了一个觉,做了一个美梦。梦中的情境真真切切,犹在目前。老头儿咕呶一句。他想起好像听见什么声音,便立刻去看望孩子。
孩子的状况依旧。老头儿心酸地把脸凑过去,贴在孩子的黑脸蛋儿上。他哭了,心里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搅。
在泪眼模糊里,老头儿发现孩子的嘴唇微微张动了一下。他的心一收缩,揉揉眼,再去细看孩子。他能够听见孩子的口里有一点声音。老头儿紧张得大口喘气,他好像觉得自己成了聋子。
生命的气流在孩子的皮肤下面慢慢游动。他脸上的气色的确比刚才好多了,不再发出令人失望的灰白的冷光。老头儿的欣喜使他一动也不敢动。他双眼紧盯着孩子,视线好像看到孩子体内的骨骼和泛波的血液。他觉得孩子体内逐渐明亮起来。
老头儿想,孩子一定在呼唤他。但是现在孩子还没有力气感觉到爷爷。他静候了片刻,孩子的状况持续好转起来,虽然速度依旧很慢。老头儿的信心更坚定了,也许他从未对孩子丧失信心。
老头儿在孩子枕下又垫了一些东西,使他的头颅跟身体相平,呼吸也能够更通畅一些。
“S,S,S……”
孩子的//www.58yuanyou.com喉咙里产生了这样的模糊的音节。老头儿激动得眼皮直跳。
“是桑树。”他低声对孩子说。
老头儿离开孩子,从炉上端来一碗水,乘着灯火放入一些红糖,又用搪匙搅着,接着就喂孩子水喝。孩子呷了一口,老头儿的心里像下了一场春雨。
孩子喝了几匙糖水,又睡着了。
老头儿颓然坐在床下的木头上,一手扶着床沿。他几乎瘫软下去。他眼里一点光也没有。他想,这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苍天,我真要老了,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干一辈子活就是要把力气用完。”他这样想着,垂下眼皮。“也许我马上就要死了,就是这个样子,死就是这样。”老头儿的手从床沿上滑落,他身子一斜,靠在了墙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那些皱纹如同流干了水的田野里的沟渠。他好像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里蜷缩着的就是人生活在世界上的让人记忆的最后一点标志,而且这点标志也就要很快化水、气和土。
但是,他猛然又挣扎着追回到这个世界中的这个房子中来。老头儿强使力气睁开眼皮。他想,死就是做梦,就是睡觉,而且是一睡不醒。他还不能这样去死。“我还没有干完事情啊,我还有很多活计。”他想着,“我想问题都觉得用力,但是一想起来还不是觉得太使劲的。”老头儿掉头看看床上的孩子,那就是他生的喜悦和硕果。他认为孩子离长大成人还远着哪。
老头儿用手掌搓了搓疲惫的双眼。然后他打量了一下他生活着的房子。火炉里的火熄灭了,但还有温热从那里散播出来。它旁边的那些木桶刚才被很多人坐过。外面瓦棚上可能积压了很多雪,被压得低声响。
“镇子里的人都在替我担心,”老头儿思量着,“怕我抗不住。可是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活着的,我还有的是劲儿。现在呢,我的孙子,我的命根根,小小,也马上就要好起来了。他是被那天的事吓坏的,不过,他的身体像我一样,不会那样容易就完了。瞧我的手,满是劲儿!”
老头儿挺了挺腰,坐直了。“这场雪肯定下得好大。”他从窗户里看到覆着白雪的房屋的影子,树木被积雪压得在夜里吱哇叫唤,有些树枝也会断掉。
老头儿忽然想起镇子里的一个人来。
“大家都在关心我们爷儿俩,我也要关心关心别人。”他想,接着就想站起来。孩子气色又好了许多,睡得很平稳,很舒畅,呼吸很均匀。“我的孩子也要好了,我就更应该想到别人。”
老头儿站起来,心里还带着愧意。他几乎没有亲眼看到犹所长。他要去犹所长家。但是现在是夜里什么时候,他可拿不准。他犹豫了一会儿,心想不能再推迟到明天,就又给孩子整了整被子,走出去了。
大地一片洁白,但夜空却显得漆黑无比。镇子里阒无人迹,老头儿顺着被雪盖着的路来到犹所长家里。
犹所长的妻子和儿子们都不在这个镇子上住。老头儿一看犹所长房子里有暗暗的灯光就想犹所长的家属还没有睡。他们可能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老头儿应该去安慰他们。他一想到这个,就觉得有力量,一下就推开了犹所长的房门。但是那房门好像预先就打开了似的。
老头儿立刻闻到了香喷喷的煮野兔肉的味儿。他的肚子里几乎咕噜咕噜叫了。
他想到他这么冒失地到来,可能使犹所长的亲人受了惊。他马上感到很沉重的阴森的目光压迫在他的头上。他因为内心藏着哀悼的情绪,眼睛根本抬不起来,便在房间的中央看到那只蹲在炉火上的铁锅。锅里焖着兔肉,嘟嘟地向外吐着白汽。
犹所长的三个儿子正在守夜。他们全像他们的父亲一样高大,像石头一样结实。
老头儿一阵心慌意乱,嗫嚅着抬头去看他们。他发觉他们非常可怕,虽然他们并没有将视线对着他——他们几乎没有正眼看他,但老头儿觉出他们的目光又险又冷,跟从阴司的裂隙里挤出来的一样。老头儿还没有看清犹所长的尸体停放在哪里,就听见墙后面一个房间里有人问是什么人过来了。那是犹所长的妻子。
其中一个儿子说:
“一个老头子!”
老头儿开始害怕了。他盘算着这些人对他的到来没有友好的态度。
房子里飘满了兔子肉香。一个儿子把锅盖掀开了,往里瞅了瞅,房子里更香了。他们把老头儿围在中间。
老头儿惊慌失措地打量着他们,他的眼睛忽然惊住了。他从他们之间看到了犹所长的灵床。犹所长身上连尸布都没盖,还是那天的老样子,但是身子已经挺直了。老头儿惊奇的是他发现了犹所长淌出来的两颗鲜血淋漓的眼珠子。老头儿浑身打颤,那眼珠子在他视线里突突直跳。
犹所长的儿子一走动,身子就挡住了床上的犹所长,老头儿不解地恐惶地看着跟他对面的这个人。
“哥,”老头儿旁边的那个人对别人说,“动手吧!”
这中间的老大——就是那个逼视着老头儿的人还没有马上说话,看样子他的兄弟都在等他的眼色。过了片刻,他开口对老头儿说道:
“你经不起我们动手!我们比狼还狠,等着瞧吧,老头子!”
他的兄弟表示赞同。他又说:
“你是来找苦头吃的,老头子。你要聪明点,就向我们说实话,镇上的人怎么害了我爹?那个女人是谁?你们总要败露的,老家伙,公安局的人也饶不了你们。等着瞧吧!该你说了,老头子!”
但是老头儿在他们凶恶的目光里不知说什么好。他好像听见有谁在哭。
“给他灌热兔汤!”站在老头儿左边的一个儿子用手掌把老头儿的脑袋向背后狠狠地压了压。
锅盖上的笛子还在响。兔肉香更浓了。
老头儿心想,他们不会那样做。他们对犹所长的死持有怀疑态度,痛苦得快原由网要发疯了。老头儿决心再忍着点,他们过一会儿就能恢复常态。
有人猛推了他一把,他的身子就像被扭歪了。他看看揪着他胸口的老大的脸,那眼里的光像阴暗的刻毒的火一样,几乎要把他全身烤焦。老头儿这才想起挣扎,因为他被这有力的强壮的人提着正向焖兔肉的锅走近。他的身体一阵阵抽搐,但就是出不了声。
“这老头子还好像是硬骨头哩!”
“让他喝热兔汤吧!”
老头儿已经发觉锅盖上笛子的响声就在耳旁。他都快给弄倒在沸腾的锅上了。他想抬起手把揪住他的人推开,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他嘴里喘息着,直望着这个人。他心里想,完了。他还听见一个女人站在不远处,阴森森地得意地笑。
但是,这老大猛然松手了。老头儿的身体开始向兔肉锅落下来,不过,从体腔内骤然产生的电一样的力量使他的双脚稳稳地站住了。
老头儿看见了闯进来的伯明。
那几个人都拐过身去,不声不响地背对着他。那个小儿子又把锅盖拿开,用一根筷子小心地戳着兔肉。一团白汽含着诱人的香味升上屋顶,好像变形的妖魔一样。那个女人站在犹所长的灵床一边,阴沉地盯着什么。她是什么时候走出来的,老头儿一点不知道。
“我们走吧。”老头儿听见伯明在招呼他。
他们离开了犹所长的家。老头儿这时候才知道时间已过了半夜。大雪覆盖着小镇,雪上柔和地发射着刚刚开始照耀的星光。老头儿跟随着他的镇子里最勇敢的年青人,心里渐渐安静下来。伯明听他讲了发生在犹所长家里的事之后,就说: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凶的一家人。”
老头儿格吱格吱地踏着地上的雪,望着伯明坚实的肩膀,说:
“我们谁的坏话也不要说!”
快走近老头儿的家里时,伯明就停下来,老头儿在星光里自个儿走进家门,他才向自己家走去。他想,这真是一个好老头儿,但是幸亏他怕老头儿出事,又起来找这老大爷,不然,那可就惨了。
老头儿首先听到从屋里传出的奇怪的响声。他的通过户外时被冻凉的脸也感受到屋里的暖气,好像火炉生起来了。
在床下的地上蹲着一个孩子。他身上围着半条被。
老头儿惊呆了。他看见孩子正把粮食颗粒从黄玉米穗子上剥下来,又送到口里去嚼,嘣嘣地响。孩子看了老头儿一眼,张开了口,里面还有没嚼碎的玉米粒。他好像顾不得跟爷爷说话,就继续咀动起来。他肚子里非常地饿,已经饥不择食了。
老头儿走过去,阻止他再去吃这种又生又硬的东西。他这才发现,家里剩下来的那些熟食都被孩子吃光了,孩子经过了一场恶梦,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只是饿。
在老头儿离开家的时候,孩子又往火炉里添了一些干透的木柴片,现在它们在冬夜里燃烧得正旺呢。
老头儿抱住孩子就像抱着他余生的希望,他不会再失去他了——而且他向来没有失望过,这是真的。
在这个冬天里,犹所长的尸骨跟他的亲属离开了小镇,回归故土。那个晚上,金乡县城殡仪馆来了车,把他接走了。镇政府另派了一辆车载着犹所长的全部家当。他家里人坚持夜间离开小镇,对此人们一口答应。
冬天过去得很快。春季好像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一样,一下子就来到人们面前。人们欢欣地走进这个明亮的灿烂的季节里去。老箍桶匠瓦棚上,草泛绿了。第一只燕子低低地从房屋上掠过,所有的人都向它打开了大门。这是吉祥的兆头。镇子里商店前的招贴画都换成了新的,电影院的海报也是同样。伯明的橡胶厂把赢利捐给了镇政府做众人的福利基金,每天都有很多人把废塑料和旧轮胎什么的拉到他的工厂里去。人们只想沉浸在大地和天空的新气象之中。
女人花从容不迫地在街上出现时人们都不免向她问候。她对每一个人都温和,但又谨慎,从不与人说笑。人们愿意看见她,视线总是被她牢牢地吸引过去,仿佛她是春天的光辉,需要她照亮人们的心和双目。
花是菏泽地区粮食学校培养出来的人,犹所长在世时她可以不参加工作,到了现在,她仍然能够只待在房子里,没人到过她的房子。她拥有一个很漂亮的独院,里面还有照壁。人们都想去看看。
但是渐渐的,花对镇子里的人们的态度都冷淡下来。老箍桶匠也不再想跟人们说她很像他当年的妻子了。老头儿抓紧时间一心做他的工作。他的孙子身体比任何时候都要健壮。老头儿想,花仍然是镇子里最美的女人。
花也不像曾经疼爱过那个小孩子。有时花走在街上,小小远远地跟着她。他希望她能发现他,那样他心里敢情多么幸福!他爱着花。他不会忘记那一年的夜里他被花带到了她的家里他,——那几乎是很早时候的事。但是他最后还是逃掉了。他爷爷在这一夜没有见他回家,而在另一天里也没见他回来。老头儿差不多急疯了,镇子里的很多人都帮他寻找,找了两天也没见孙子的影子。那几天有人说镇子里出了怪事,他们在夜里看见有只像小孩那样大的蝙蝠倒挂在桑树上,快吓死人了。
那天上午老箍桶匠可没心事干活。犹所长肩挎着猎枪从家里慢慢走出来,抬着头看天上的飞鸟。他的样子真像一位伟人。不过一刻钟他就打了十几只麻雀,丢在他的挎包里。他碰到了伯明,就跟伯明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转过身又举起了猎枪。
伯明发现他的枪口对准了远处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桑树。
“那里有一群麻雀。”犹所长说。
他开了枪。
伯明呼叫一声向那里奔去。
一团绿桑叶从树上落下,但是一个孩子却穿过桑叶,像蛋一样,落在了纷扬的桑叶前头。那就是失踪三天的小小。他在桑树上躲了那么长时间。他没有受伤,但不管别人怎么问他为什么爬上桑树,就是闭口不语他在花那儿见到的事。
现在孩子好像遭到了亲人的遗弃一样痛苦,他泪眼汪汪,但他没有丢掉花会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一笑的幻想。他像他的爷爷一样倔强。而且,他仍在相信家门前木杆上的那个木桶在响。他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镇子里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遗忘。他们觉得七个月是够长的了。夏天了,天气又热VZdeNDkTL,阳光把路面都晒裂了,他们想,前面那个人不就是已故的镇粮食所所长么?他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跟时间一样绵长的记忆里了,就好像种子找到了一片深厚的沃土。
但是,人们所期望的终究会来到。那一个星期,大家都觉得出奇地轻松。他们没有在街上看到那个男人。
周末,人们想起女人花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大家一起涌向她的院子,发现她已经走了。人们远望着她的敞开的院门,各自想着那样一个美丽的女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花。但是,她好像离得人们那么遥远,如在纯净的天外。
老箍桶匠不停地做着他的活计。他的孙子让他细听木桶的响声,他果真听了一会儿,想说没听到又怕孩子再来缠,就说:
“听到啦!”
孩子从他身旁走开,来到木桶下面。有一株盛开着蓝色花朵的牵牛花,缘着木秆婆娑多姿地爬上去,又从杆顶和木桶上垂下头来继续生长。木桶里寄居了一窝麻雀,这时候它们飞出来,把牵牛碧绿的叶子撞得乱晃了一阵。空气在桶口产生共鸣。那些长在叶片底下的躲开阳光的小花儿,还没来得及合拢。孩子想,它们在里面吹着喇叭。

本期编辑:刘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