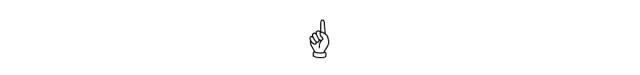张小福的河
一
巧英是一家国营敬老院的面点师,说是面点师,其实啥活都干,基本成了养老院厨房的万事通。
她是经过社会招聘进入这个敬老院厨房的,当时签合同时候,就说明只负责面点方面的工作,不管别的事。可是进了厨房后,就不这样了,几乎啥活都干。为什么呢?这原由很多。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敬老院的人事不断变动,在巧英的记忆中,敬老院的人员不断增加,但自从厨房两个人调到办公室和护理岗位后,她们厨房就从来没满员过。敬老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厨房就左止右拙,人员就不够用,岗位就乱了,厨房的所有人都变成万金油多面手,时间长了,巧英几乎忘了自己是面点师。她生来脾气就随和,于是就毫无怨言的当起了万金油。
这天到了开饭的时候,人特别的多,巧英就在窗口打饭,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打饭从来不看打饭人的脸,只低头看碗,菜盆和递过碗的手,几年下来,她熟悉每一双手每一个碗,比拥有这只碗的脸还熟悉。
她有条不紊的将递过来的碗装满,她熟知每个碗对食物多少软硬酸甜的要求,所以自信的挥舞着勺子,满足每个碗不同的要求。
她正干的酣畅淋漓,勺子就忽然发生了迟钝,因为,递过来的碗让她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于是,她便抬起了头,果然,窗口另一边是一个陌生的脸和一道陌生的目光。
她虽然听说敬老院要来新人但没想到来的这样快,所以有点惊讶。这个陌生的面孔后面,还有几张陌生的脸。
这是一个微胖,年龄大概六十多的男人,脸上干净的看不到一根胡子茬,但也看不到刮的痕迹,这是天生的,仅有的几根眉毛自由的奔放者,秃顶,小眼塌鼻,但衣服却穿的格外干净规矩,浑身透着一种不协调的怪异。
巧英接过了碗,但抡勺的手有点迟疑,她再抬头看那老男人,那人却根本没有留意她, 只是自顾打量着厨房四周的环境。
巧英很不自信的给这个碗里添满菜,放了两个馒头,老男人收回目光,看了一下碗,伸出五个指头。“嗯?”巧英问。“五个馒头,两个不够?”那老男人说。
巧英就又给碗里放了三个馒头,老男人满意的笑了一下,端着碗走了。
接下来,巧英又接过几个陌生的碗,照例打满,放上五个馒头,她习惯的知道,初进敬老院的老人饭量大的出奇。过一段饭量才会慢慢减下来,时间长了,几乎都是只能吃两个馒头。可是她心里还是感到一种不自信,甚至有点失落。
巧英就是在这种恍惚中完成了这次开饭。
第二天,巧英在敬老院院子里的小公园又见到这个老头。
巧英下班后,和厨房里唯一的女性同伴叶子一块到院子公园转转换换心情,于是,就在这个小公园里见到这个老头。
已经是阴历三月天了,风吹过来已经没有令人发抖的阴寒,而是带着隐隐的暖意,带着春的温馨。离清明还有一段时间,小公园的青草已经迫不急待的探出了头。带来一片毛绒绒的嫩绿,几树迎春花,绽放出阳光一样的炫目的金黄。樱桃树长出层层叠叠粉红色花朵,美丽极了。
那老头就一个人孤单单的坐在这个花园长长的凉椅上,手边放着一个小塑料袋,时不时的从塑料袋中抓出瓜子,有一搭没一搭的磕着。
看见她们来,老头不自然的笑着站起来,将瓜子袋递到她们面前说:“吃瓜子,吃瓜子。”
叶子向来随便,抓了一把,一屁股坐到凉椅上磕了起来。巧英有点犹豫,老头又将瓜子袋递到巧英面前说:“吃点吧。”
巧英象征性的抓了几颗,老头手抖了一下,又坚定的将袋子递到巧英面前:“吃瓜子。”口气比刚才坚决的多了。巧英又抓了一点,老头就随手将瓜子袋扔到凉椅上,叶子手里的瓜子已经吃完,又抓了一把,老头才有了笑模样。
“才来啊?那个村子的?”叶子问
没听见老头回答,巧英下意识的看了一眼老头。
老头的脸上依然挂着笑,但整个人神情很茫然,目光好似正极力的向远方看去,仿佛在仔细聆听在远方的另一个人说话,对叶子的问话毫无反应。仿佛突然之间。叶子和巧英就不存在了似的,这让巧英特别不舒服,也感觉到一种怪异。
“哎!叶子问你呢,你是那个村的?”巧英问。
老头收回了目光,看了巧英一眼,倔强的眼神里有一种孤傲。他告诉叶子和巧英,他来自偏远的乡镇里的一个偏远的山村。
“巧英,你去过吗?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叶子磕着瓜子,大咧咧的说。
“我也没去过,只是听说哪里是咱们县风景最好,植被覆盖最高的地方!”巧英说
“风景最好啊?那天你带我们看看,你们那风景真的好吗?有狼吗?那里的人很穷吧?”
叶子来了兴致,瓜子也不磕了,喋喋不休的问起来。
对叶子的问话,老头很不高兴,但还是介绍起他们村子。他说:他家里特别好,他有许多鸡他有许多地,他说他的地每年种着粗大结实的玉米能卖好多钱。他夸他的菜,上了鸡粪的辣椒如何辣如何香,上了猪粪的茄子怎么怎么的美味,上了油渣的萝卜如何肥大香甜。他完全忘记叶子和巧英的存在,好像自己给自己说,接着就说起了村干部。连说带骂,说自己怎么怎么的不想来,村长书记住村干部说这里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非要他来。他的鸡不知怎样了,干部有没有偷得吃了。我们走的时候说好了,他要给我卖个好价钱,这个哈怂,肯定偷吃我的鸡菜,看我回去不咒他。他越说越气,好像口里骂的那个村长是他的远方侄儿。
叶子和巧英看他认真愤怒的样子很滑稽,就笑了起来。
老头这才从幻想中回到现实说:“我叫张小福,我有钱,会做饭,一年收入有一万多,吃穿都有,我没有老,不要人照顾。”说着眼光又茫然的盯着远方,又忘了她们。
“你吹牛,哪有那么好,肯定你吹牛?”叶子说:“你一天怕只吃一顿饭吧!”
张小福脸突然就红了,一句话也不说低下了头。
这时叶子跳了起来嚷道:“忘了忘了,快走快走,我孩子这会儿怕快饿扁了。”说着头也不回的就向大门口走去。
巧英还想跟张小福说什么,看张小福没有理她的意思,也就跟着叶子的身后走了。“叶子,你这疯婆子,等等我!”巧英边追边说。
巧英和叶子并肩走向回家的路,叶子还在不住的唠叨:“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们在农村过的啥日子,你听他吹牛,到这还不是白捡了个金饽饽。你看他牛的,‘我不要照顾!’谁爱照顾你,国家疯了,白白照顾他们,还不落好。钱多的烧的。”
“看把你能的,没有他们,你到哪挣钱?我看是便宜了你。瞧你,就像个女省长,叶省长,明天给我女儿安排个县长,最起码给个养老院长,行不行啊!大省长!”巧英打趣道
“死去吧,还养老院院长,厕所所长都没有,要有那本事我儿子也有工作了。”两人说说闹闹各自回家。
二
第二天,巧英休息,家里的事忙的一塌糊涂,来到单位就显得厌倦无力。
叶子就凑过来了:“老鹰,病了?我来吧,你歇歇?“
“没有,就是没有精神,好困。”巧英说
“那我给你说个笑话,说什么呢?”叶子想了想,:“哎!老鹰,还真有个笑话,是关于你的。”
“瞎扯吧你!还有我的笑话,看你坏样子,又编排我啥了?”
“不是我编的,还真的和你有关,你记得张小福,就那个秃头没有眉毛的?”
“你积点口德,什么秃头没有毛,是土豆吧,还张小福李小祸的。”巧英有点想不起来,就放机关枪似的说。
“真不骗你,就是前天在花园中给你瓜子的老头,他说他是你亲戚。”叶子说
“又胡扯,我和他有啥亲戚?”巧英想起来了。
“真的没亲戚?不可能吧?昨天你没来,张小福把我叫到他那,说和我有亲戚,我当时跟你现在一样,后来才弄明白,他把我当做你了,认错人了。”于是叶子就一边麻利干着活一边快嘴快舌的唠叨起来。
昨天,叶子开完饭后准备回家,刚出厨房,就被等在院子的张小福叫住。要她和他一起到他的宿舍,说是有很重要的事和她说。叶子也好奇,就随他到了他的宿舍。
“咱们是亲戚!”到了宿舍,张小福一边张罗着招呼叶子,一边肯定的说。“论辈分,你得把我叫哥。”
叶子毫无准备,一下子就懵了。只听张小福继续说“北塬吴家尧科吴**是你三爸,我是他侄儿,把他老伴叫姑。是老一辈的亲戚,你可不把我叫哥叫啥。”
叶子这才听明白,她知道张肯定闹错了,她在北原就没有亲戚,更不认识吴**,不过她倒是听巧英说过她在北原有亲戚,肯定是张小福把她当做巧英,也没点破,想再多听点线索。
“山里没有啥好东西,就是一些鸡蛋核桃,鸡蛋是我养的鸡下的,核桃是我地畔的,有点格格,很香,不是啥好东西,你们城里人稀罕,再说,也难吃到这些,我来的时候,我那哈怂侄子,就是我村的村长,说你在这,我就带了点。”
看张小福认真了,叶子也不好意思不说破就坚决推辞:“你弄错了,不是,我不是。”
“咋,看你哥穷,一个人。怕赖住你,放心,哥不是那号人。”张小福真生气了。
“我真的不是,我姓叶叫叶子,你听听,姓都对不上。”叶子着急了。
“你真叫叶子?看这事弄得,这哈怂狗蛋,又骗我,看我回去咋收拾他。”张小福很失望,气哼哼的骂起他侄儿。
叶子觉得张小福有些可怜,就说:“可能闹错了,你找的是巧英,她北原上有亲戚,她也姓*”
“真的,你别哄我。”张小福说。
“明天她上班,你问她吧。”
“老鹰,你不会怪我出卖你吧,不知道咋回事,我就觉得张小福可怜,这老汉不错,明知道认错了,还硬把核桃给我,不拿都不行。”
巧英想了想说:“听我妈说过,一个老亲,可能就是吧。”
“老鹰,咋不说话呢,张小福可能一会找你,你躲躲吧!”
“怪你个大头鬼,这又不是啥不得了的坏事,躲你个鬼,躲哪去?我才不像你那样小气。为一把核桃,就把姐们卖了。”
果然,打饭时张小福就小声对巧英说:“下班你到我哪里去一下,有话说。”说完还左右看看,好像害怕别人听见。巧英就笑着点头。张小福的房间在三楼,敬老院有两座公寓楼。一座在公园后面,那是新盖的。住着社会供养老人,也是单位各部门的办公室,那座楼安静舒适一些。五保户这座楼紧靠orOAoL街道,是双面楼,一面靠厨房,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厨房后面的居民区。靠街道的房间嘈杂烦乱,打开窗户街道上的车声人声就会扑进房间。张小福就住在靠街道的一个房间里。这间房有两个老人一起住,那个老人出去了,张小福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他的床上不是单位统一配置的床单,是一条绿色的碎花单人床单。那床单好像没有洗净的样子,床单中间有些灰色的印痕,和房间洁白的墙面,翠绿色的窗帘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巧英看着床单就有些分神,心里想这些人一辈子把日子过得孤独寂寞,所有的细节都要自己打理,也是悲哀。
张小福说:“我把你三爸叫姑父。姑姑家女儿嫁到我们邻村,她比你大十几岁,你记不记得?”
巧英从小在县城长大。老家的亲戚大多不太来往,吴家其实和她们家已经是出了五服的亲戚,因为在一个村子住着就称呼个几爸几姑的。有一年回老家见过几个比她大的表姐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可是她也不点破、就说:“那个大姐现在怎么样了,我以前回去走亲戚见过她,很黑很瘦,个子高高的。前几年来我们家,还给我爸妈拿过咱们老家的豆豉。”
张小福就高兴地笑了,他拍着大腿说:“是啊!是啊!她现在更加瘦了,一儿一女孩子都大了,他们两口子可有苦了,种了十几亩烤烟,每年收入七八万。可有本事哩。”
于是巧英就附和着笑,就跟着他夸那个表姐能行。夸完了表姐张小福走到床前半蹲下来从床侧的抽屉里拿出来一小袋土鸡蛋,这时候巧英才发现张小福的褪有毛病,一瘸一拐的。蹲不下去只好一条腿半跪下来才能拉开抽屉。巧英心里有些替他难过。
他紧紧抓住床沿用了好大的力气才站了起来。他说:“这是自己养的土鸡下的,拿回去给娃娃们吃。”巧英就推辞说:“不要,娃娃们不要,你自己吃,我们家啥也不缺。”
张小福就沉下脸说:“咋?嫌弃我。害怕我以后给你添麻烦。”
巧英赶紧说:“哥,真的不是,我是说你一个人身体也不好,弄点东西不容易。”他一把从巧英胳膊上拿下皮包,打开拉链把鸡蛋放了进去。嘴里说:“既然认我这个哥就听话,拿上。”巧英看推辞不了,就接过皮包,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说:“哥,我第一次来也没有给你买什么,这一百元钱你拿上,想买什么就给自己买一点。以前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亲戚。现在知道了,就不能空手来。”
张小福看着巧英手里的钱,眼圈就有些红了,他嘴里推辞了一下。巧英硬把钱塞进他口袋里,背起皮包拉开门走了。张小福看着巧英走出门去,眼里有了泪。
三
这是张小福来到敬老院的第一个夜晚,对面床上那个肮脏邋遢的老男人已经睡着了。窗外隔一会儿就有汽车尖叫着经过,车灯把屋里照得忽明忽暗。还有街道上不知谁和谁吵架,骂着难听的脏话。对面那个男人在打呼噜,还不停地磨牙,嘴里说着梦话,叽里咕噜听不清说什么。
张小福烦躁地在床上翻来翻去,心里骂着自己的侄儿张庆,他知道那是一个白眼狼,恨不得他早早死掉好霸占他那几亩田地,还有他的那一群鸡。鸡比人有良心,比人忠诚啊!他的眼前又出现永远难以忘怀的那一幕。
他几乎记不起母亲长什么样,他稍大一些才知道,母亲是跟一个来村子里做石活的陕北人跑了。父亲根本就没有去找她,母亲跑路那年他只有两岁。只记得父亲每天都在喝酒,喝醉了酒就打他。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又不知道到哪里喝酒去了。破窑洞的土炕冷硬似铁,只有五岁的他饿的发抖。爬到锅台上揭开冰冷的大锅。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空的锅底发出黑色的亮光。炕头上煤油灯闪闪烁烁,就像风一吹就会熄灭。他又费力地爬下锅台,在大案板上终于找到半个干硬的玉米面馒头,他高兴起来,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块在嘴里嚼着。
那是一个五岁孩子第一次一个人在破窑洞里过夜,风不停地敲打门板,寒风从窗户的破洞里灌了进来,发出尖利的吼声,就像随时都会把小屋刮塌。他吓的全身发抖,他害怕风变成怪物突然伸出手把他抓住,然后张开嘴咬他。他大声哭,哭声被风的怒吼吞没了,他哭了很久最后竟然睡着了,醒来时窗外已经有了亮光,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他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再醒来时,天已经大亮,阳光透过破了的窗格照进来,大炕上他裹着父亲的被子穿着破烂的棉衣一个人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回,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开始害怕起来,这时候突然有几个人闯进门来,门里灌进大量的冷气,好像这些人都是直接从冰雪里钻出来的。门被他们撞的发出巨响,就像马上就要散架了。父亲被七手八脚放在炕上,他这时候才看见父亲全身僵硬,双目紧闭,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腿上全是湿的,好像在雪地里爬了好久。
那几个人大声对他说话,粗声粗气地好像害怕他听不见,他们说:“你爸已经死了,是喝醉了酒在回家的路上掉进沟里,在雪地里冻了一夜,冻死了。”
那时候他听到别人这么说,茫然地看着这些人舞弄父亲,他们从院子的雪堆里抱来干草铺在地上,从炕上把父亲挪到干草上。然后拿来一块破布盖住父亲青灰色的脸。他呆呆看着父亲僵硬笨拙的样子,突然觉得他异常陌生。他进入脑子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再也没人打他了。直到父亲被埋进土坑里,他才突然明白从此后父亲再也不会给他吃喝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了。他害怕,他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他多么希望父亲醒过来再打他骂他。这才嚎啕大哭,直哭到天昏地暗,然后昏了过去。等他醒过orOAoL来已经躺在大伯家炕上,村里几个婶子在他周围议论,一个说:“孩子真惜慌,没爸没妈了。”
一个说:“命不好,看孩子瘦的。”
大妈说:“唉,今后就要在我家里,让我们养活,我们家有五个娃,又加一个拿啥给吃啊!”
一个胖女人说:“没得办法,总不能让他饿死,你就将就着。慢慢等他长大。”
“唉!”黑瘦的大妈又说:“就怕我辛辛苦苦把他管上,最后还不落好,村里人还说我对他不好。”
“不会的,不会的,谁说那种没良心的话让她养这个娃娃。”这些女人抢着说。
四
王杨玲气鼓鼓地下了公交车,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女说说笑笑从她身边经过,一个女孩踩在她脚上,几个人一声不吭地就要离开,女孩就像没有感觉到踩到了人。她大叫一声:“等一下。”
几张年轻的脸转了过来,她说:“踩了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还是学生,你们老师怎么教你们的?”
一个男生转脸轻蔑地看着她,发出一声嬉笑。踩她的女生黑着脸说:“对不起,大婶,我们可以走了吗?”她看清了几个孩子眼里的不耐和漠然。他们不等她回答转身逃跑一样走进几步远的中学。
“这些孩子!”她说:“什么素质。”气鼓鼓地走进医院,这个新来的张小福刚来几天就住院了。真烦人啊!医院是她最讨厌的地方,楼道上一股永远也消散不了的消毒水刺鼻的味道,还有打扫不彻底的卫生间的尿骚味儿,病房里病人身上散发出来意义复杂的怪味。张小福躺在白色的被子下,看她进来连个招呼也不打,她把从敬老院食堂拿来的饭菜摊开来送到病床跟前的床头柜上,张小福坐起来开始吃饭,这人饭量很大,她拿来的三个馒头一碗菜一会儿就全部消灭干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卫生纸抹净嘴巴上的饭渣。顺手把纸扔在地上。另一张床上的一个胖老头说:“怎么随地扔啊!”
王杨玲对那个老人说:“农村人什么也不懂,卫生习惯就是这样。”
边说边拿起门边的扫把扫起来。他看见张小福拿眼睛瞪她。她就说:“以后不能随地乱扔,要扔到垃圾筒里。”张小福说:“我是病人,你来就是伺候我的,我不扔你闲坐着也没事干。”
王杨玲气的脸色胀红,那个临床的老人多嘴多舌地说:“你是雇来的护工啊!”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王杨玲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就说:“才不是呢!我是敬老院的护理,他就是一个没人管的五保户,你以为他是谁?”那人看张小福一眼说:“哦!五保户啊!”口气里满是轻蔑。
张小福转过脸,又躺了下来,不再看这两个人。心脏又开始疼痛,他双手紧紧压着心脏部位。他听到王杨玲对那个婆婆妈妈的男人说:“自己是肺心病,一旦感冒就会犯病。很麻烦的。”张小福真想用手堵住王杨玲那张臭嘴:“缺德鬼,不说话不行吗?非要揭别人的短啊!”他想:“老子五保户怎么了,吃你们orOAoL的了,还是挖你们祖坟了?你们这么看不起老子?”
王杨玲看着医生给张小福扎上了吊针,这会儿功夫那个多嘴的男人和他矮胖的女儿也问完了敬老院的情况。问的全是些无知的问题,王杨玲耐着性子一一解答,他们开始唏嘘,一个说:“看病一分钱不花,到了共产主义了。吃也白吃住也白住,还有这么好的事啊!现在国家真是对这些人太好了。”王杨玲说:“就这,我们院里的老人还不满意,还嫌照顾的不够,一个个牛逼轰轰以为自己了不起,每个人都应该把他们当成皇帝。”那个老人就说:“比儿女都好,那些人真不知天高地厚,现在这个政策真好,要放到以前这些人老了就受死了,没有钱看病没有钱吃饭,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有些人死了好久都臭了村里人才发现。”
张小福忍无可忍,突然大声恶声恶气地说:“那你怎么不杀了儿女,早早的不要结婚或者杀了你老婆。你也可以享这个福了。”
那个老人就生气地说:“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这是人说的话吗?你怎么是这种不识好歹的人。”王杨玲就赶紧说:“叔别和他一般见识,这些人都是不识好歹的,怎么能说清。”
那个多嘴多舌的老人气鼓鼓地转过身,头对着门口,女儿看了一眼吊瓶说:“爸,医生说让你不要生气,你就自己找气受,你和那种人计较什么?”
男人就不再说话,张小福却怨毒地看着王杨玲,在心里把她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一遍。王杨玲看着吊瓶里盐水还很多就走出病房来到过道里。
王杨玲讨厌医院,每次来到医院她的心就疼痛不已,那是她永远不愿意回味的痛彻心扉的惨痛经历。
那是秋天的黄昏,公路在山坡上呈s型层层缠绕,就像螺丝被拉长变形而不断重复的回环,路两边的山崖上点缀着绿色的大树和各色野花,有些树的叶子已经变成红色或黄色的,从塬上下来的摩托车在崎岖的山路行驶着,摩托车手是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头上没带头盔,眼角和脸上的皱纹,以及黧黑色的皮肤都告诉人们他是一个长期户外活动的人。风猛烈地刮过他的耳边,他的耳朵有些轻微的疼痛。就像走之前听到的那个电话,妻子王杨玲的哭声仍然在耳际回响,母亲和妻子永远水火不容。强势的母亲事事都要她说了算,妻子却是一个事事较真的女人,敏感多疑斤斤计较。他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这个塬上的乡镇上班,离家有五十多公里。结婚后一直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四十多了提拔已经没有希望,吃苦受累却仍然是一个普通镇干部,妻子没有工作,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所剩无几,还要时不时贴补父母一些。他知道自己的妻女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不妥,一大家子人吃住在一起,家里的米面油是父亲在买,可是菜却一直是妻子在买,其实谁都知道每个月的菜钱比米面油更费钱。母亲总是嫌弃妻子没有工作,生的又是女儿。可是他们这么多年没有积蓄,买不起房子,无法搬出父母的小院。两个女人鸡毛蒜皮天天弄,为了节省路费,他买了这个摩托车。妻子说过这里路不好,容易出事,不让他买。可是每次回家都要等车,不光花钱多,也让他烦不胜烦。对于缺钱的人来说节省一点算一点吧。
“我们几时能够搬出去住啊!我受够了,我吃个饭她都嫌我吃的多,每次一吃饭就嘴倔脸掉,她难道不知道东西都是我买的,还嫌我光吃不赚钱。天啊!我都不想活了。”王杨玲絮絮叨叨,千篇一律的话又一次在耳边响起,摩托车手烦躁地摇摇头,就像想甩掉无边的烦恼。
突然摩托车撞上了一块路边的大石头,他喊了一声:“该死!”双手拼命想抓住脱手的摩托车把,这时候摩托车就像一头野兽般猛地飞了起来,他被带动着飞过摩托车然后像陀螺一样,快速地向山崖下滚去,摩托车飞过他的头顶在山坡上不停地撞击,车身和车轮很快分奔离折,就像孩子们撒落的积木,各种零件滚落在山坡上。可怜的摩托车手,不断翻滚,脸在山坡上的灌木和泥土上不断摩擦,一会儿就血肉模糊,最后他重重地跌落在沟底的灌木丛中。就像一个布偶,四肢就像被风刮断的树枝一样悬挂在身体上,身体最后就像被扯断的纸人一样滚落沟底。
第二天王杨玲在医院看见丈夫的时候,大叫一声晕了过去,那残忍血腥的场面击碎了她的心,从此后噩梦就像毒蛇一样缠绕在她的身上,她的世界从此坍塌了。
五
一个黑漆漆的窑洞,窑洞里的大炕上坐着一大家人,大伯坐在首位,穿着破破烂烂的五个孩子围坐在黄褐色的木头炕桌前吃饭,孩子们挤在一起几乎插不进去任何一个人。张小福站在桌前挤不进去,大伯说:“张红!给小福让一个地方。”一个十多岁的瘦女孩站了起来,满脸不高兴地拿着碗离开桌子到大锅前灶火角落吃饭去了。张小福看着女孩离去的方向觉得好像自己抢了人家位置,桌上摆着一大碗咸菜,一人一碗稀薄的玉米粥,还放着几个玉米馍馍。张小福看着那几个馍馍,一动也不动,嘴里吞咽着口水。另外几个孩子在桌上飞快地一人拿了一个,还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用筷子一下插了两个举到嘴前,然后对着张小福挤眉弄眼地笑,大妈的脸冰冷坚硬,就像要从皮肉里掉出冰渣。大伯对那个孩子说:“学军把你的给小福一个,现在咱们家多了一个人,大家要让着他一点。”那个叫学军的男孩故意大叫一声:“哎呀!”一口却咬掉两个馍馍各一个角,嘴里含满东西不知道说些什么,别的孩子就大笑。大伯也嘴角淡淡地咧了一下,好像是笑了一下。从放馍馍的柳条框里拿了一个递给张小福。他一边看大妈冰冷的脸一边咀嚼着馍馍,那些孩子已经吃第二个了,他吃完手里的,发现柳条框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他的肚子仍然很饿,大伯问他:“吃饱了吗?”他点点头,把一碗稀粥倒进肚子里。
又一天,六七岁的瘦弱男孩在大土灶前努力地吹火,他的脸憋成酱紫色,鼓起腮帮子一下一下吹着,一些灶灰四散飞了出来,落在他的头上衣服上。那时候大妈还在地里没有回来。他想在大妈回来前烧着火,最好把水烧开,大伯有喝茶的习惯,他想灌满家里那两把保温瓶。其中一把红漆皮的还是他家的,爸爸死后家里的东西都搬到大妈家了,那个破窑洞也锁住了门。想到这里,他又一次哭了,他想让爸爸再打他,狠狠的打,只要爸爸还活着他就不会天天被大妈家的孩子们打骂欺负。他又想起晚上几个孩子都不让他挨着他们,几个姐姐骂他身上有臭味,哥哥就一脚把他踢下炕去,屁股摔的生疼。他爬起来缩在大炕的另一头,那里没有铺褥子,破烂的席子已经变成黑色。有许多地方已经露出土炕黄黑色的泥土,他努力抽出自己的被褥,胡乱铺在上面。几个孩子偷偷笑,一个说:“小心席糜子扎屁股,扎烂了流红血。”几个孩子大声笑了。他骂了一句:“一群哈怂。”被子就被几个孩子倒扣下来捂着他,一顿拳打脚踢。他发不出声音。几个孩子终于放开了他。最大的十多岁的女孩说:“以后你听话,我们叫你干啥就干啥。不许骂人,不许告状,否则下次还要打。”这时候大妈听到叫喊在窑门口说:“不要胡弄,都小声点,小心你爸过来打。”几个孩子就不再说话,大妈一走他们就哈哈大笑。
火还是着不起来。他拿了锅台前的火柴,点着一些干篙草,火‘呼’的一声吼叫着着了,好多火扑了出来,他只听嘶啦一声额前的头发眉毛全被烧掉了,他用手一摸手上一些干硬的黑色灰烬。篙草很快着完了,变成一堆红色的灰烬,几根黑色的树干仍然没有烧着。他从灶火前站起来又到院子里找来许多干柴火,抓了篙草又添在灰烬上,夹在大柴之间,他又鼓起腮帮子吹起来。
这时候大妈回来了,她扔下锄头大步走了进来。看见张小福在吹火就说:“去去去,走开让我来。”张小福站在边上,只见大妈把灰扒拉出来一堆。嘴里说:“火要空心才能着,看你把我火柴糟蹋了多少,救火的攘柴又糟蹋了多少?哎呀,以后不要你救火,走开走开!”张小福赶紧慢慢地走了。这时候大妈已经麻利得升起了火,就向他喊:“去,再抱些柴。”他跑到院子里的柴火垛跟前抱柴,柴火垛很高,可是他太矮,柴火垛比他还高出一节,在他面前就像竖起一座小山,根本够不着上面。于是就狠劲在中间抽,刚刚抽出几根,哗啦一声,柴火垛就发出巨响,他赶紧跑开,粗细不一的木柴四散坍塌。
大妈扑出来抓住他,眼睛血红,她骂道:“天啊,丧门星!滚一边去,啥也不要你干了!干啥都要工钱。”这时候他看见大妈张大的嘴里,稀疏的牙齿焦黄,嘴里喷出一股强烈的臭味。他的胳膊被捏的生疼,他知道大妈是准备打他的,却忍住了。大伯听到响声也跑了出来,每天中午大伯一回来先在炕上躺着睡一会,这时候对他吼道:“滚,能滚多远滚多远,害人鬼。”
他从院子里跑出去,在中午的太阳下面瞎逛,逛了许久,这天中午他不打算吃饭了。他知道自己闯了祸,于是就来到村子外面。一片又一片田野,尽头是连绵无边的大山,母亲在哪里啊!他信步顺着大路走出村子,那时候已经放工,人们都回去做饭或者吃饭去了,路上没有一个人。一个瘦弱低矮的孩子在乡间小路上独行。他那时候一心想要找到自己的妈妈。
六
王杨玲已经受够了,张小福住院的七天里她天天起早贪黑地送饭陪他吊针,但是她发现这人根本不感激她,看见他就一副受苦受难受了委屈的样子,好像她怠慢了他似的。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五保户,却摆出一副大干部大款的样子,好像她是他雇佣的仆人。对她指手画脚,爱答不理。怎么这么像她的公婆呢?为什么她总是遇到这种不是人的东西啊!
丈夫死后她有一段几乎不想活了,公婆整天苦着脸。一想到丈夫也许是听了她的电话才会那么晚回家出了那么惨烈车祸,她就心如刀绞。她强打精神还必须给公婆做饭,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有一次她在厨房忙活听到婆婆对公公说:“我说她是个丧门星你不信,现在倒好一个儿子没生,现在又克死了俊杰,你看看她那高颧骨,她当年一进门我就看她不行,不是好命女人,你们父子就不信,我可怜的儿子啊!我现在就希望她出去,走远远的,我真不想看到她。”停了一会儿公公的声音响起他说:“唉!要怪只能怪命,她现在啥啥没有,你让她到那里去?怎么生活。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在敬老院当院长,我给说说,让她有个工作也能养活她和她女子。也不要天天在家里惹你生气。”婆婆叹了一口气说:“最好有了工作就不要回来,省得我看见她堵得慌。”
这一天,她唯一的同学雪雁来看她,两个人一见面,雪雁就说:“杨玲啊!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眼睛红肿,无神,绝望,无精打采。我看你这样下去就彻底毁了。”雪雁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女子,说出的话就像做文章一样字斟句酌。
王杨玲说:“我觉得活着实在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可是我们小玲怎么办?她已经大一了,谁管她啊!她没有了爸爸再失去妈妈怎么受得了?”
雪雁说:“杨玲,你现在是没有精神寄托,你不要天天憋在家里,应该出去认识人,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其实人吧,谁活得那么舒心?你看着活得好的人,说不定内心天天都是车祸现场,你看见痛苦的人也许内心却充实快乐,人只要内心有寄托,世间的一切都能够看开,一切都是扯淡,活着才是王道,不要为一个人而活,一切都是命。你不要总是在老两口面前晃来晃去,心情永远不会好。怎么样?我今天带你去个地方让你转变一下思路,也权当散心。”
两人第一次来到教会,当王杨玲听到大家含泪唱的赞美诗,当第一次听到牧师讲道,她觉得心灵一下子得到了净化,她跪在牧师面前,她忏悔自己的罪孽,她哭着说:“是我克死了俊杰,我对不起他,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公婆做的一切都是对我的惩罚。”
当她不久后被特招到敬老院上班的时候,几乎每夜她都会忏悔说:“感谢神给了我工作,感谢神给了我食物,感谢神给了我一切。我如今有了工作能够养活自己都是因为信神的缘故。信神让我改变了厄运。每天夜里的失眠开始减轻,噩梦也不再夜夜纠缠她了。”
尽管她信了教,还是处处碰壁,不会与人交往,虽然她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努力,处处讨好别人,从来不说脏话。诚实守信,心地善良。可是她还是无法融入这个单位里。
敬老院的门是那种电子门,从保安公司顾的门卫。那天是那个五十多岁,喜欢和女人胡谝乱抡的胖男人值班。那男人长得高大威猛,可是却长着一双细长猥琐的眼睛,这种女人一样的眼睛几乎天天含着笑可是在笑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流里流气,这眼睛一看见漂亮女人就亮光四原由网射,喜欢和各种女人开无聊的玩笑,王杨玲想不通这种人怎么能够守单位门户,听说这人以前是村官就有农村流氓的那种明目张胆的痞气。奇怪的是自从他来到敬老院,所有的员工反而喜欢聚集在门房里,说笑胡谝,每天热闹非凡。
门房当年在敬老院既是员工们上班每天签到的地方,又是每个老人请假条的收集地,每一个老人请假都会在这里有记录,过一段护理必须来这里整理请假条,写每天事件记录。这天她去整理请假条,又是这男人值班。那天门房没有别的人,这人无聊地看电视,看见她来就笑着打招呼,说:“他妈的!越看电视越生气。”王杨玲就奇怪地说:“生什么气?”
男人就说:“电视上全是漂亮女人,一个比一个骚,就没有一个是咱的。”
王杨玲就说:“无聊。”
男人就坏笑着走近一步看着她说:“啥无聊?人就活这个无聊劲嘛!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离不开男人,这就是阴阳平衡。我就不信,你一个人夜里不想男人?又不是小姑娘,装啥装?”
说着,眼光猥琐地在她身上转来转去,最后在她胸前停了下来,他的目光似一双手,已经开始胡乱抚摸了。王杨玲脸红耳耻地后退一大步,恨不能对准他的眼睛来一拳,让他那色迷迷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东西。可是她还是忍住了,转身大步离开,男人就在她身后哈哈笑。就像喉咙里塞了一根鸡毛,嘎嘎粗鲁狂野的嬉笑让王杨玲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
她气呼呼地边走边在牙缝里骂出一句:“流氓!”这句话男人根本没有听见。
这天夜里,许久不做的噩梦又来了,半夜她梦见丈夫推开门走了进来,坐在床头说:“你终于搬出来了,这回我爸妈就不会给你气受了。”说着丈夫就爬上来,挨着她躺下来,她在梦里抚摸着丈夫的脸说:“你不要离开我,我和小玲都离不开你,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你。”于是她手上用劲把丈夫拉进怀里,她急切地张开嘴寻找丈夫的唇,丈夫的吻粗鲁急切,胡乱地落在她的脖颈乳房上,一种久违的渴望从心底冒出来,身体就像冒起一个个小火苗,然后变成熊熊大火。她紧紧抱住丈夫,就像龟裂的土地需要甘霖,需要滋润一样迫切。可是突然之间,丈夫的嘴唇不见了,嘴的位置变成血肉模糊的一个大洞,血咕咕地往出喷,那一双温厚的眼睛也变成两个小洞一起喷着血,鼻子不见了,哪里变成了花椰菜一样的一团红色的破皮烂肉。“啊!”她尖叫一声惊醒了,被子湿透了,全身水淋淋的,她猛地坐起来,卷缩成一团悲切的哭了。
“为什么?”她敲打着自己的头问:“老天为什么这么欺负我?为什么要杀了丈夫?为什么杀了她的幸福?这一生老天对她如此吝啬,事事不如意,一个又一个恶人,唯一爱她的那个人也毫不留情的被夺走,为什么老天爷如此待她?”这一夜注定是不眠的,她恨恨的想,这么多天她已经接受了,自从信神以后,她已经能够压抑自己心底的欲望,她觉得那是对丈夫亵渎。她甚至鄙视自己,只有这样她才觉得配得上丈夫地下的魂魄。这一夜都是因那个门卫而起,她恨那个恶心的男人,她决定下一次绝不客气。
又一天她刚刚回到敬老院,电动门开了,她走到门口突然一辆车也向门口飞速开来。那男人抓住她的衣摆把她拉进门房里,她猛地推开他骂道:“干啥?干啥?耍啥流氓?是人不是人都想欺负我!”
那时候门房床上坐着两个护理,办公椅上坐着厨房的一个年轻厨师。王杨玲想不通这些女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和这个色鬼胡说八道,她们咯咯乱笑,笑得花枝乱颤,让她觉得说不出的恶心。这人就加倍地对这些女人说着无聊的笑话,这些人嘻嘻哈哈常常热闹无比。
王杨玲站在门口一阵乱骂,护理站起来先是劝她,她流氓欺负的一出口,那两个护理满脸尴尬地站起来走了,厨师是个年轻英俊的男人。他嘻嘻哈哈一笑,一副看热闹的样子一下子刺痛了她,她就骂:“这个单位都是些啥货,有没有素质?”
厨师就不高兴了,站起来说:“姨,你看你这话说的,一个字,绝。一棍子就打翻了一群人,厉害!”
门卫脸红耳赤的说:“你知不知道好歹?刚刚我看那个车差一点碰到你,拉了你一下,就招来这样一堆话。我怎么就流氓你了?说说笑笑而已,有啥认真的,都几十岁的人了。”
王杨玲气急败坏她说:“这还用说吗?你就是一个见了女人就走不动的货,你说你不是流氓是什么?”厨师听到这话就坏笑着挤眉弄眼地走了,门卫脸色由红变黑说:“王杨玲我告诉你,我就是流氓也看不上你,你看看你自己,要人才没人才,要脸蛋没脸蛋。一张驴脸成天掉的老长。我眼睛瞎了才会看上你。”
王杨玲被一下子气的七窍生烟,恨不得一耳光煽过去,但是她忍住了,她哭着跑了,她边跑边咬牙切齿地骂:“混蛋,流氓。”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
这门卫也不是好鸟,几乎见一个说一个,这件事全单位很快就传遍了,连领导也知道了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女人以后还是少招惹。”
张小福这天终于出院了,王杨玲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这天巧英就问王杨玲张小福看病的情况。那时候刚刚开完饭,两个人在二号餐厅窗口站着。王杨玲大声说:“那人是肺心病,一个感冒就可能要命,要特别注意。”然后又说:“这人不是东西,根本不知道感激,别人对他再好都以为应该,我天天给送饭看盐水连一句好也没落下,人家还说,我是应该的,以为他是谁的大爷?”那时候张小福就在二号餐厅坐着吃饭,每一个字他都听得一清二楚。
巧英说:“别和他们一般见识,这都是一些可怜人,人家要是啥都好,怎么会到这里要我们照顾?你们基督教不是说了吗?别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基督说的仁爱就是这样,爱护每一个可怜人。”
王杨玲就说:“巧英我说不过你,可是我知道,对魔鬼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而且我也是可怜人,怎么没有一个人同情我?像我这样的人还欺负,真的就不得好死。就是十恶不赦,应该下地狱。”
巧英看着王杨玲气呼呼离开,心里就莫名地憋了一把火没处发泄。这时叶子叫她吃饭,她坐在饭桌前,就对叶子说了刚才的话。厨师就说:“你生她的气干嘛?告诉你,王杨玲就是一个神经病,那人不是一般人。”然后就指指自己的头说:“这儿有问题。”叶子也说:“你可能不知道现在护理几乎没有人搭理她。她一开口就骂别人欺负她,好好一句话就招来一句欺负。你说都在一个单位上班谁欺负谁有意思吗?而且人人都认为她可怜,可是你不能因为可怜就要求所有人都让着你,要所有人都忍受你的臭脾气。谁又不是你父母,凭什么?只是那人工作很认真,卫生也是全单位最好的,很勤快,要不是这样领导都有可能不要她了,据说许多人都在领导面前说她坏话。”巧英只好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七
张小福那天其实没有并没有走多远,大太阳晒的人睁不开眼睛,他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长期的饥饿让他没有力气,他不记得自从父亲死后他什么时候吃饱过。几乎每顿饭他都不敢吃饱。
这条路被雨水冲刷的坑坑洼洼,有些地方还有冲出的小水沟,横亘在土路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褐色的蛇在爬行。路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他走了大概二里多路就返回去了,他知道他不会找到妈妈,妈妈早已不要他了,他哭了很久,最后自己又回到大妈家。那时大妈家一家人坐在炕上吃饭,他们说说笑笑的,他一进门。所有人都闭了口,冷冷地看着他。他们才是一家人,而他不过是一个外人!那是他第二次感觉到的痛。比起父亲死去那天的浑浑噩噩,这种感觉更加痛苦。
大伯把他抱上炕。表姐说:“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没处去吧!看你再逞能?”大伯吼了一声:“给我悄逼了,不说话谁能卖了你”大妈看了大伯一眼,淡淡地说:“给孩子发啥火?”说完就离开饭桌,洗碗去了。桌上别的孩子已经吃完,是玉米面片,上面飘着一些绿色葱花。大伯把桌上的一碗端给他说:“吃吧,吃吧。”
他端起碗大口吃起来,就是那时候他对食物的依恋变得更加迫切 ,吃饱饭就成为他那时唯一的奢望。他发现在他能够吃饱的日子里,他饭量很大。
等他十多岁时他也和大妈家的孩子一样进了学校,每天放学他第一个拿起猪草镂去地里拾猪草,中午的大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玉米地里闷热干燥,玉米叶就像剑矢一样神出鬼没地刮蹭着他的脸,玉米地里的苦菜很高,但是很不好找,有时一片地一颗也没有,有的地方却很多,拾猪草的孩子很多,有些地方被别的孩子拾完了。他第一次揭开刚刚挂上玉米粒的棒子,那是一个个珍珠一样的乳白色颗粒,他踮起脚尖咬了一颗,嘴里是甜丝丝黏糊糊的液体,有一股玉米的清香。他偷偷搬下来,一层层剥开包皮放到嘴里咀嚼,真香啊!一连吃了四个,他觉得肚子已经饱了。这才拾满了猪草回家。
那天他回到家里,大妈家窑门紧闭,到了吃饭时间了。他推开门看到大妈慌乱地把什么东西往身后藏,几个孩子嘴里不断咀嚼着什么,最小的小军手里拿着一个白面烧饼。那时候白面平时很少吃到,他一下子气急了,几个孩子天天欺负他,什么活都支使他干,稍有不顺就打他。什么坏事都懒他身上,大妈每次都会偏袒自己孩子,把所有过错都尽量推到他身上,对他越来越冷漠。看见他们开小灶他再也忍受不了就委屈地哭了。他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要回到自己家住去,他喊到:“你们不把我当人,我做牛做马天天干活,天天吃不饱!你们背着我吃好的,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村里月月还给我补助粮食!我也没有白吃你们的。”大妈看他哭的厉害就说:“小福啊!我给你留了,不是你刚才没回来吗?”
大姐姐那时已经是十七八的大姑娘了却说:“张小福你有没有良心?要不是我们家你早饿死了,我们自己吃点怎么了?这是我们家!我们想咋样咋样关你屁事,不给你吃怎么了?”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地骂起来,那几个姐姐一个比一个牙尖嘴利她们抢着说:“妈,你就别理他,你天天给他吃喝,还给他做鞋做衣凭啥咱们还不对了?养个狗还会看门,养头猪还能吃肉。养他还养下罪了。”
张小福就大声说:“我自己会做饭,会洗衣服,我回自己家,我自己过。不要你们养,我自己养自己。”
大妈就冷笑说:“看来我是喂了个白眼狼啊!现在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就要走了啊!要走你就走!你大伯今天去镇上了,晚上回来你给他说,你爱走不走我可不管。”
张小福这时已经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被褥,全部放在架子车谁,拉着就往自己家去了。院子里已经是杂草丛生,黄蒿长的比他还高,窑顶上也是荆棘野草覆盖。他拿了一把铁镢开始疯狂地挖着杂草,院子很大,他挖了很久仍然只挖了一小遛,连路都没有挖开。他已经挖不动了,全身没有力气,他仍然倔强地挖着。
也不知道挖了多久,他饿的头昏眼花,这时候大伯佝偻着身子进来了,大伯进门就吼道:“小福你给我死回去,你能的还当你娃能上天。”说着就一把夺下了他的铁镢。他想夺过来但是一下子摔倒了。大伯扶起他说:“娃呀!你还小一个人还不行。我知道这几年大伯家娃娃多,你跟着我受了罪,你现在跟我回去,我请人找队干部把这窑洞修好,过几年你想住就搬过来,现在不能住啊!
张小福哭了说:“大伯啊!我知道只有你对我好,我不想让你作难。我一个人住不难为你。”
大伯一把抓住他,老鹰提小鸡一样把他拉回去。那时候桌上放着一大盆白面饼子,大伯威严地说:“吃饭。”大妈和姐姐们一碗碗端上了玉米稀饭,一大盆土豆炒腊肉。简直就像过节日。
那是他几年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大伯在饭桌上说,以后都给我对小福客气一点,再让我看见你们几个偷着打他,操心你们的皮。
几个孩子一边拼命往嘴里塞饼子,一边点头。后来的两年间他不再上学,大妈家的大女儿也已出嫁,他开始在队上干活挣公分,回到大妈家什么也不干,没有人理他,他也不理人。看见饭他像有仇一样狠狠吃,他不再怕大妈的眼光,成了好吃懒做,没脸没皮的人。大妈看他的眼光就像看见了一只苍蝇,仇恨和厌恶充满眼底。可是大妈却背过脸不再去看他,恶狠狠地隐忍了下来,只当他不存在。他那时候才发现要不被欺负只有自己恶,人常说的没错,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虽然他知道一家人早已恨不得他早早滚蛋。这时他反而不着急,直到有一天大伯叫来几个人开始收拾他的窑洞,他们铲光了院里的草,窑顶上的草和荆棘也收拾利索,最后用压场的碌碡来回压了许多遍,又铺了一层毛草加了厚厚一层土又压了多遍。大家说这回就不会漏雨了。
他自己开始收拾窑里,窑洞里一股霉味,由于多年没人居住窑洞里老鼠洞,小虫许多,灰尘也很厚,炕上就扫了几荸荠尘土,炕中间已经坍塌了,大家七手八脚拆了它,又重新盘了一个大土炕。
他的家就这样收拾好了,他刚刚十五岁就一个人独立生活了。其实他知道大妈家后来几乎把他当成害货,送走了他全家人几乎松了一口气。那么多人给他收拾家的时候,都把他当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坏蛋了,村子里人人都认为大妈大伯是好人。
那时队上照顾他一些粮食,他自己就开始过日子了。谁也想不到第二年他却因为一场病变成了拐子。有一天早晨醒来他突然觉得头疼欲裂,口干舌燥。他想爬起来倒些水喝,可是一下子晕了过去 。那时候他年龄小村里人根本不指望他上工,就是来也派最轻的活,有时他不来也给他记工分。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照顾他,常常干脆就不去上工。那天他晕了过去一连几天昏迷不醒,人们还以为他又偷懒了,直到第三天才有几个人来看他,一进门就发现他发高烧,头就像火炭。他被送进医院。那一次高烧引起了肺心病,如果再迟一点命就没有了。他的腿也肿胀无力,被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从此他就一瘸一拐了。腿的疼痛一直跟随了他半生,也会随着年龄老去更加疼痛难忍,一致到死去才会停止折磨。
八
只要有新人来,卫生就会变得难以打扫,这几天王杨玲已经是第N次打扫卫生间了,公共卫生间便池里臭气熏天,不知道谁弄得,竟然满池的褐黄色粪便。这些人竟然不冲厕所,明明有水却拉了抬屁股就走人,真叫一个恶心。四个小间几乎全是这样,气死了。她一个个冲洗干净,连早上吃的饭也吐了。她气呼呼地跑回护理室拿来钥匙,一下子把男女卫生间各锁了三个,每个只留一个小间。其实每个老人的房间里都有小卫生间,可是这些老人却不在自己房间大便,也不会冲洗。更不习惯坐马桶,王杨玲认为这纯粹是欺负人,故意找茬。“如果让我抓住狗日的,我非收拾他不可。”她在心里嘀咕。
这一天夜里她去上卫生间,因为护理室没有卫生间。都是在大卫生间解决个人问题,这一天正好是她锁门的第一天。她推开门,里面居然有人,竟然是穿一身蓝衣服的张小福!她又羞又恼,赶紧关上门。
她大声在外面喊:“你咋回事啊?你不知道这是女卫生间吗?在里面还不关门。”
老头在里面四平八稳地说:“你不让上厕所,锁了门要憋死我啊!我不上这上哪,厕所是你家里的不准上?”王杨玲等了好久张小福仍然慢吞吞地在里面。王杨玲就说:“你们一天到晚连卫生间也不冲,你房间里不是有马桶吗?”
张小福又说:“不会用,坐下拉不出来。”
“你真是一个老流氓”王杨玲气愤地说,“女厕所是你随便进的?你恶不恶心?”
张小福冷笑一声说:“我就进了,你把我求咬了,我就拉一泡,咋流氓你了。”
王杨玲一听张小福粗鲁的脏话就气急乱骂起来。
王杨玲正骂的起劲,张小福拉开门猛地冲出来,王杨玲刚好站在门口,他就怒气冲冲地说:“好狗不挡路,滚一边去!”
王杨玲一愣神间,他已经挤过去,一瘸一拐地回房间去了。王杨玲没有听到水响,她进去一看,一股无名火腾的一声窜了起来。张小福居然没有冲厕所!便池里黄褐色的粪便发出热腾腾的臭气,直冲人的鼻孔。
王杨玲愤怒地边向楼道边走边吼:“自己冲了。”可是楼道里已经不见张小福人影,她愤怒的吼声就像打在气球上的拳头,气球轻飘飘地飞走了,拳头却打在墙上碰疼了自己。张小福的房子离公共卫生间只有几步的距离,她疯了一样追了进去。
张小福已经躺在床上,看见王杨玲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不紧不慢地拉开被子把自己裹起来
这种冒视直接就把王杨玲内心的恼怒燃烧到失去理智,她一字一顿地说:“你—给—我—把—厕—所—冲—干—净!听到了没有???”
张小福看着王杨玲憋成紫红色的大四方脸冷笑,他觉得自己自从来到这里对这个女人憋了一肚子恶气,这会儿一下子找到了出口。他讨厌她那种说话的口气;讨厌她看不起人的样子;讨厌她处处表现的她自己就像救世主的样子。好像她不是来赚钱而是可怜这些人一样。他觉得来这里这段时间他已经被这个恶婆娘伤的不轻,就像她每天拿着一把利箭,时不时射他一箭。却没有人看见他的伤口和鲜血。这女人看他的眼神像极了大妈的冷漠和蔑视,却还没有大妈的隐忍。大妈是轻易不说恶毒的话的,虽然更加讨厌他。
他冷冷地说:“我就不冲,你能把我咋样?你是啥东西?你不过就是一个伺候我们的人,和过去的丫鬟老妈子一样。你当你是谁?你当自己是老子的救命恩人吗?我应该感谢您啊!冲厕所就是你的活,你赚钱就应该干。叫老子冲,干啥你闲着赚钱啊!”
王杨玲瞪大眼睛,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恶狠狠的说:“你说你是啥东西?要不是国家可怜你,你死了都没人埋。你一辈子混下个孤家寡人,你看看你在这里谁和你能处的来?就连你房子的老人也不和你说话。你有意思吗?活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说那些话?我是伺候大家的,不是伺候你一个人的,你算个屁?”
张小福听了这些话,刚刚下去的火气又升了起来,他‘呸’地一声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说:“老子死了还有国家埋,你呢,谁埋你,看你那克夫样子,老子看见都讨厌。你克死了你男人还想克死敬老院所有的老人是吧?”
这些话就像一支支缀着毒汁的剑,每一剑都准确无误都射进王杨玲的软肋。她感觉自己身体里冒出“滋滋”烧灼的声音,五脏六腑都剧烈疼痛。
她尖叫一声哭了,她撕心裂肺地叫道:“天啊!救苦救难的主原由网啊!惩罚这个魔鬼吧!”
这时候楼道里传来杂踏的脚步声,许多老人涌了出来,把王杨玲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地问:“怎么了?”有些耳背的老人不停问前面的人。王杨玲一边哭一边述说,几个老人就抢着说:“不要和那种人一般见识,他就不是个人。”一个勤快的老人主动去冲洗干净了卫生间。一群老人簇拥着王杨玲来到护理室,大家群情激愤,共同声讨张小福的种种劣迹,有的说:“他偷听别人说话。”有的说:“他从来不理人,臭脾气犟钣金。”有的说:“他一说话就打击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最后得出共同结论,不再理他,权当他不是个人。
一个老人又说:“王护理是个多心善的人啊!拿自己的钱给我买东西,还这么欺负人家。”老人说:“每次他有病都是王护理陪他,买吃的喝的,比儿女都好,真是好女子!”老人一开头,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王杨玲的好来,似乎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这时候王杨玲的一口恶气才稍稍得到释放。她说:“我的心老天神明都可以看见,我对你们咋样大家能知道我很高兴,就是我累死,只要大家理解,我也会高兴死的。”
最后大家同仇敌忾,把共同的敌人张小福恨的牙根痒痒,恨不能剔除出去而后快。
这件事过后,隔一段男卫生间地上就会有一堆粪便,而且这些粪便被人用马桶刷涂抹的满地都是,这几乎把王杨玲气死,三楼的几个老人都告诉王杨玲这是张小福干的。王杨玲坚信除了他不会有第二个人,于是安排了几个老人轮流看守,只要抓住人就会送到领导那里。
就在大家群情激愤打算抓住他,收拾他,让他名誉扫地,想法子惩罚他时。这件事突然不再发生了,这些老人准备的一场战争就这样嘎然而止。就像一场电影没有到高潮就结束了,让大家意犹未尽。究竟是不是他,没有人知道答案。
作者:喻巧凤,富县社会福利中心工人,喜欢写作,曾在《今日陕西人》上发表过报告文学,在延安日报发表散文若干篇。在县刊网刊都有作品发表,富县作协会员。